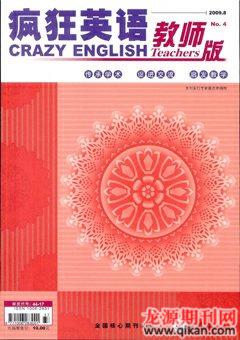轭式搭配语用解读与翻译
司继涛
摘 要:轭式搭配是一种将仅适用于甲项事物的词语顺势搭配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乙项事物上的英语修辞格。这种搭配法在语法上属于“非法”,但在语用上却是“合法”的。文章从语用学视角分析轭式搭配的结构特征——变异性、间接性、关联性及其语义推理,并探讨其汉译策略。
关键词:轭式搭配;语用特征;认知参照;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9)08-0127-4
Abstract: Zeugma, an English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n epithet only applying to one thing is directly employed to other irrelevant things. Such collocations are asyntatic, but pragmatically tenable.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reveals zeugmas characteristics—variability, indirectness, relevance and its semantic cognition, and probes into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zeugma,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referenc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1. 引言
轭式搭配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语言现象和变异搭配英语修辞法,一直是我国外语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修辞现象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修辞和语法方面。文章拟从语用学视角入手,分析这一修辞格的结构特征及其语义认知推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汉译策略。
2. 定义和用法
2.1 轭式搭配的定义
轭式搭配“zeugma”一词源于希腊词语“zeugnynai”,意为“yoke”(Pearsall, 1998),即汉语的“轭”。 这一修辞格的主要特点为“拉郎配”,即以一关键词(即轭词)生硬地将两个或更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捆绑”起来使用,造成语义表层结构晦涩难懂,但却获得一种新颖、奇妙的修辞效果。这就好比用一副轭把几头牲口硬套在一起拉车一般,看似硬套却又能协调行进,看似牵强却又能产生强大的聚合力。《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一书给这一修辞格下的定义为:“一种在一个句子中用一个词同时支配两个或更多词的修辞法,通常在语法上或逻辑上只有一种用法是合适的”(Drabble, 2000: 1128)。例如:
(1) I used to organize my fathers tools, my mothers kitchen utensils, my sisters boyfriends.
这一例句的谓语动词“organize”同时支配三个不属同类的名词,其中与“tools”、“utensils”构成合理规范的搭配,与“boyfriends”搭配则不合文法,但通过巧妙借助“organize”与前面构成的正常搭配,顺势套用,反而使非规范的搭配在特定的语境中暂时地在语法和逻辑上获得成立与通过,收到引人入胜的修辞效果。
轭式搭配的“以一制众”结构属于搭配上的缺省,“是基于表达上的省略”(Hilladay等, 1976: 214),体现了修辞语言的“经济原则”。由于缺省,使得轭词同时支配多个不同语义范畴的词,造成了局部搭配的错位、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偏离。而正是这种“错位”和“偏离”突破了常规语言的固有模式,使表达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幽默风趣。
2.2 轭式搭配的用法
从语言结构形式看,轭式搭配通常有以下几种用法:
2.2.1 同一动词支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
(2) And all the people saw the thundering and the lightening and the noise of the trumpet, and the mountain smoking...
众人看到雷鸣、闪电,看到喇叭声和山上的烟雾……(例句中的谓语动词“saw”同时支配“thundering”、“lightening”、“noise”、“smoking”四个名词,其中与“thundering”和“noise”搭配不符合常理。)
2.2.2 同一介词单位与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搭配
(3) Well see to it that the blouses appeal to the eye as well as to the purse.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罩衫吸引人们的眼球,吸引人们的钱包。(例句中“appeal to”同时支配“eye”和“purse”,其中与“purse”搭配不合文法。)
2.2.3 同一形容词支配两个或更多的名词
(4) They went to the graveyard with weeping eyes and hearts.
他们去参加葬礼,心和眼都在流泪。(例句中形容词“weeping”同时与两个名词“eyes”和“hearts”连用,其中与“heart”连用不符合常理。)
2.2.4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语共用一谓语
(5) Glass, china and reputation are easily cracked and never well mended.
玻璃、瓷器和荣誉,三者皆易损坏,而不能复原。(例句主语“glass”、“china”、“reputation”共享谓语“cracked and mended”,但“reputation”使用这一谓语却不符合逻辑。)
3. 语用特征及语义认知
3.1 变异性
轭式修辞格的语义搭配有悖常理却又合乎逻辑地存在着,表现了一种“无理而妙”的修辞现象。人类的语言不仅具有稳定性和规约性,而且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语言变异性”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指的是语言形式脱离语言常规的可能性。Verschueren在其著作《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诠释了其语用学观的语言变异性。他认为,“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说话人根据交际意图及多种语境因素从可供的不同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1999: 52)在交际中,话语类型和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可以使语言的意义产生无限的变化,在语境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的作用下,语言的使用或选择就灵活多样,使意义的生成成为一个动态过程。
作为一种语义搭配有违常规的修辞格,轭式搭配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变异现象,是为了服务一定的交际意图和适应某个特定语境而生成存在的。因此,轭式搭配可以看作是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顺应交际意图、交际语境及语言结构在语用上作出选择的一种表达形式。
3.2 间接性
Searle指出,人们实施言语行为最简单的情况是——说话人说出一句话,确切地表达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字面意义和说话意图相吻合,也就是句子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或称为直接言语行为。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往往会“通过实施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1975: 61),或是“通过一种次要的施事行为来间接地实现一种主要的施事行为”(1979: 34)。因此,次要的施事行为是字面的,而主要的施事行为则是蕴藏在字面意义之下的“言外之力”,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要理解这样的话语,听话者必须联系具体的交际语境,依据说话双方共有知识,透过话语的字面意思推断出说话人的真实意图。
轭式搭配表面上违反语言常规搭配,违反了Grice提出的交际“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但从其结构形式和功能之间关系看,两者体现着某种间接的关系,其字面意义下蕴藏着另一层更深的“言外之力”(转引自Levinson, 1983: 101)。在例(1)中,作者正是借助轭式搭配的间接性巧妙而又含蓄地表达了其“效率专家”的意图。首先,作者故意构建错位搭配营造视觉落差和幽默效果,从另一角度“不显山露水”地表达其意图。尽管“organize”与“boyfriend”搭配不合逻辑,但读者通过借助前面的自然搭配,联想推导出这一搭配的意义,进而明白作者的深层意图,即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的优秀品质。其次,作者借助轭式的搭配缺省,节省笔墨,精炼言语,暗示其语言表达的“高效率”。读者在分析句子结构和理解句子语义的基础上,可以体会出作者这又一“言外之力”。
3.3 关联性及其语义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认知的实现在于它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关联。也就是说,言语交际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心理,即通过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来认知事物。因此,言语交际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何自然等,1998:92-107)。根据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Sperber等, 1986 & 1995: 260)。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通过明示行为向听话人展示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而推理就是寻找关联。关联指的就是说话人的话语在听话人的语境假设中可以产生语境效果。推理涉及到两类信息的结合和运算,即由话语信号建立的新假设和在此之前已被处理的旧假设或语境假设,新、旧信息互相联系在一起就成了关联信息。听话人根据关联原则、旧信息和新信息的相互联系,从新旧信息所提供的前提,借助推理而获得说话人的话语意图。
轭式搭配的结构涉及到常规搭配与非常规搭配构成新语境产生新义的问题。其中常规搭配可看作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信息或说话者提供的认知环境,而变异的搭配则被看作新信息,当两者被“轭”在一起时,就产生了关联。从认知语义角度来说,Talmy认为,“记忆中已有的项目构成基础,提供分析范畴,作为评估、描述和分析新认知项目的参照点。”(2000: 329)常规搭配正是这样的“已知项目”,为变异搭配提供认知参照,使受话者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联想推理,获知话语意义。例如:
(6) At noon, Mrs. Turpin would get out of bed and humor, put on Kimono, airs and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
这一例句中包含有两个轭式搭配。动词短语“get out of”分别与“bed”和“humor”搭配。其中,“get out of bed(起床)”是合乎逻辑的搭配,“get out of humor”是不合常理的错配,借助“get out of bed”这一“认知假设”及常规短语“out of humor(情绪不佳)”,读者可推导出“get out of humor”的意思为“心情不好”。动词短语“put on”同时与三个名词“kimono”、“airs”、“water”搭配。其中前两个是规范的搭配,“put on kimono”意为穿上和服,“put on airs”意为装腔作势、摆出做派;“put on water”则为非常规搭配,逻辑上讲不通,字面含义晦涩。读者可根据语境“起床”、“穿衣服”、“boil for coffee”,联系生活常识,推导出“put on water”的隐含意义为“put the pot(containing water)on the stove”。因此,整句话的意思为:特宾夫人总是中午时分起床,起床后心绪不佳,穿上和服,摆出做派,放上水壶烧水泡咖啡。
综上所言,轭式搭配实则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对言语形式作出的一种语用选择。其结构形式利用了事物或概念间相近、相关的原理,借助其自身搭建的认知参照,受话者进行合乎逻辑的比拟、联想、推导,寻求话语的最佳关联,最终获知话语含义并体会出其中的“言外之力”。英语异叙法(syllepsis)的结构形式和修辞特点与轭式搭配极其相似,国内外一些学者和辞书将两者视为同一辞格。但事实上,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轭式搭配的构建是借助其具体的认知语境,即自然搭配构成的认知参照,构成变异搭配认知化、合法化的先决条件;而异叙法则是利用英语一词多义的特点,在同一句子中用一个多义词分别搭配两个或两个以上词语构成不同层面意义的修辞法,所形成的都为自然搭配。例如:
(7) The newly elected member for Central Leeds took his oath and his seat.
那位新当选的里兹中心区的委员宣誓就职。
此句中“take”和“oath”、“seat”这两个名词所形成搭配的都是自然搭配,只不过“take”以不同的意义分别与这个词搭配而已,“take ones oath”意为“宣誓”,“take ones seat”意为“任职”。
4. 翻译策略
汉语的粘连与轭式搭配都是将适用于甲项事物的词语顺势粘连到乙项事物上来的修辞手法。例如,汉语习语“人穷志不穷”,“志”本来是不会“穷”的,但“甲乙两项说话连说时,趁便就用甲项说话时所可适用的词来表现乙项观念”,于是“穷”也就被粘连到“志”上了。因此,从修辞实质来分析,两者是完全相同(胡曙中,2008: 209)。但是,由于英、汉文化和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两者并非完全对等,很多情况下并不一一对应。因此,轭式搭配的汉译就不能简单地直接移植或套用汉语的粘连结构。语境是轭式搭配赖以“生存”的空间。因此,翻译时首先要注意分析其具体的语境,准确把握各个搭配的内在关联和深层结构的含义;其次,处理译文时既要保证原文信息的有效传达,又要应尽可能体现原文的修辞特点,“使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Nida, 1964: 159)。具体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4.1 直译法
汉语中的粘连与轭式搭配有不少相似或相近的表达,翻译时为了更好地保留原文的风格,再现原文的修辞特点,只要符合汉语表达规范,均宜采用直译法。例如:
(8) While Gatsby has built up his wealth and position from nothing, the Buchanans represent “old money”.
盖茨比是靠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的,而布坎南夫妇却是那类靠吃“老祖宗饭”的人。
(9) They went to the graveyard with weeping eyes and hearts.
他们去参加葬礼,心和眼都在流泪。
(10) Some pitying hand may find it there, when I and my sorrow are dust.
将来会有慈悲的手在那找到它的吧,那时我和我的忧愁都已化为尘烟。
4.2 按汉语的搭配习惯分译
由于英、汉词语搭配及语义联想机制存在着诸多差异,在不少情况下,轭式搭配中的各个搭配若直译,会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或出现译文表达不通顺的情况。这时,应根据原文的具体语境,按照汉语的词语搭配习惯,分译各个搭配。例如:
(11) She was dressed in a maids cap, a pinafore and in a bright smile.
她头戴女仆帽,腰系围裙,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例句中的谓语was dressed in,分译为“(头)戴”,“(腰)系”和“(脸上)露出”)
(12) Her beauty and her bank-account faded.
她的美貌凋谢了,银行的存款也少了(例句中的谓语动词“faded”分译为“凋谢”和“(减)少”)
4.3 转换法
当轭式搭配是由一动词+介词的结构(有时为单一动词)和两个宾语组成时,翻译时要将其中一个搭配译作状语,另一个译作谓语。例如:
(13) Mrs. Smith got out of bed and humor.
史密斯夫人郁郁寡欢地起了床。(例句中“got out of bed”在译文中被译成了谓语,而“(got out of)humor”则被译作状语)
(14) The general lost the town and his head.
那位将军因为失了城池而被斩首。(例句中的“lost the town”在译文中成了原因状语,而“(lost)his head”则成了谓语)
4.4 引申意译法
某些轭式搭配包涵有较深刻的寓意,难以直接从字面意义翻译,在这种情况下,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将整个句子或句子某个部分意义引申,并按照汉语行文习惯意译整句。例如:
(15) Love and cough cannot be hid.
爱情像咳嗽, 藏也藏不住。
(16) She was aroused from her seat and her reflections by somebodys approach.
她感到有人走近,便即刻站了起来,人也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5. 结语
作为一种变异搭配的修辞格,轭式搭配尽管其搭配在语法上行不通,但在语用上却是成立的,它所表现出来的语用特征(变异性、间接性和关联性)及其语义认知推理的实现皆有赖于其结构的特定语境。Peecei(1999: 73-75)指出,生活中的语言充满了歧义和省略,怎样消除歧义、怎样补充被省略了的信息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具体的语境和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因此,在翻译轭式搭配这类超常规修辞格时,应注意分析其具体的语境,找出其语言表层结构中事物或概念之间的隐含关联,由表及里,深入其语言深层结构,推导出其语用涵义,并通过译入语的恰当形式表现出来,使译文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贴切、自然地接近原文风貌。
参考文献
Drabble, M.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28.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6: 214.
Levinson, S. C. Pragmatic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 J. Bill, 1964: 159.
Peccei, J. S. Pragmatics[M]. Routledge Press, 1999: 73-75.
Seale, J. Indirect speech act. In Cole, P.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61.
Sea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 1995: 260.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32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99: 52.
何自然、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 现代外语,1998(3):92-107.
胡曙中. 英语修辞跨文化研究[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