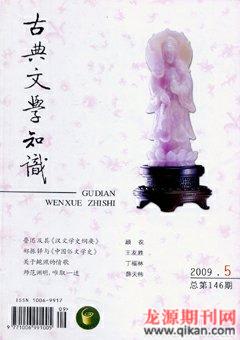明湖边美人绝调
车振华
有人说,杜甫、老舍、《老残游记》是济南的三张名片,让国人甚至世界知道了济南。这话不错。一代诗圣杜子美“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诗句断言了济南的人杰地灵,文学大师老舍“上帝把春的艺术赐给了西湖,把夏的艺术赐给了瑞士,把秋天的和冬天的全赐给了济南”的文句彰显了济南的物华天宝,而《老残游记》则是两者兼而有之。它既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风景描绘,又有对济南世俗生活的展现,给我们留下了“白妞说书”的最详细和富有诗意的记录。
“白妞”是鼓书艺人王小玉的艺名,她是廪丘(今属山东郓城)人,约生于同治六年(1867)。刘鹗之子刘大绅在《关于〈老残游记〉》中说:“黑妞、白妞,确有其人,所写捧角情形,亦为当时实况。”刘鹗的仆人李贵晚年也回忆说:“二太爷(刘鹗)在书中所说在济南明湖居听白妞和黑妞说书,是确有其事,也确有其人。姐姐叫白妞儿,妹妹叫黑妞儿。”济南是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和明代著名戏曲家李开先的家乡,自清末至民国,各种曲艺形式都集聚济南,为济南赢得了“曲山艺海”的美誉。这其中,王小玉的说书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亮点。但是,与大多数前辈艺人一样,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王小玉一直被尘封在历史的寂寞角落里。本文借助零星的史料记载和《老残游记》的诗意描述,力图走近这位曾在大明湖畔掀起观众热情的著名艺人,走进她精湛的说书艺术世界。
一、 从“犁铧”到“梨花”
王小玉的说书,准确的称呼应该叫说鼓书、唱大鼓。这一行在江湖上被称为“柳海轰”,“柳”是唱,“海轰”指大鼓。古代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作为这个行当的庇护者,需要一直供奉,并定期祭祀。教育界供奉孔夫子,竹木泥瓦匠供奉鲁班,裁缝业供奉轩辕氏(黄帝),酿酒业供奉杜康,商业供奉财神(赵公明)。大鼓这一行供奉的是东周的第三位王——周庄王。据大鼓界的人士说,周庄王在上古曾经击鼓化民,而他们唱大鼓也是要劝人民、正风俗,所以就把周庄王作为唱大鼓的祖师爷。大鼓艺人在后台都设有“周庄王之神位”,演员在上台前要先向牌位作揖,以示敬意。
王小玉当时唱的是大鼓中的一个小门类——“梨花大鼓”,用刘鹗的话说,这种曲艺形式是“山东乡下的土调”。明末清初,鲁西北的农民在辛苦的农业劳作结束后,用两片破损的犁铧片相击作为伴奏,唱一些简单的地方歌谣,以放松身心。到了乾隆年间,这种简单的用犁铧片相击而歌的纯朴艺术形式脱离了农人自娱自乐的阶段,变得复杂起来,铁片变成了铜板,加入了矮脚扁鼓,后来又变成高架鼓,成为左手执铜板,右手击鼓,三弦伴奏的说唱艺术,取名为“犁铧大鼓”,后来又雅称为“梨花大鼓”,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山东大鼓”。
与其他大鼓不同,梨花大鼓艺人不尊周庄王,而是尊大舜为祖师爷。这恐怕是与最初唱梨花大鼓所用的工具——犁铧——有关。犁铧是农民用来耕地的重要工具,而梨花大鼓的发源地山东在早于周庄王的上古也有一位曾经在此耕地的大人物——大舜。《墨子•尚贤中》记载:“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相传舜在历山(今济南千佛山)从事农业和水利等工作,因为德行高尚,就被尧选为接班人。这不能不让早期的梨花大鼓艺人产生联想,于是名声比周庄王大、经历又与梨花大鼓艺人有几分相合的大舜就成了梨花大鼓的祖师爷。
“梨花大鼓”并不是王小玉首创,它最初只在农村乡间演出,后来由农村而城镇,由城镇而城市,成为市民喜欢的一种曲艺。在同治年间,济南就有人开始唱大鼓了,师史氏(孙点)《历下志游》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郭大妮者,不传其姓名,说者谓为武定人,善鼓词。鼓词者,设场于茶案,一瞽者调弦,歌者执铁板,点小皮鼓,唱七字曲,从而和者三四人,老幼男妇不等。长短高下,自有节奏,仿佛都中之大鼓书、津门之莲花落者。先是历城无鼓词,大妮之鸨不知何许人,始创此曲,买雏伎三,大妮其一也。奏艺于章夏,仅敷日食。辛未秋来会垣,择西关隙地,支彩棚,设红氍毹,大妮率两妹登场演说。肌肤光艳,媚态横生。身无罗绮,荆钗布裙,精洁无纤尘。横波甚清,莲钩其细,曲则抑扬顿挫,奕奕有神,绚烂之余,变以平淡,觉耳目为之一清。凡座上客,罔不称赏。门前车马渐胜于前,缠头之资,积之巨万。丙子正月上元后五日,邑之千佛山开市会,大妮就其中设雅座,遍招所与欢者来,度曲永日,极尽所长。立而观者几天无余地,识与不识,鲜不欣欣然称大快。未一月,则已嫁去,两妹亦相率脱。一曲清歌,遂如广陵散矣。
在郭大妮脱离乐籍而嫁为人妇之后,有一位寄居济南章丘的临清人黄大妮,想继承郭大妮的事业,于是就在西关当年郭大妮演唱的地方也摆下台子,演唱当年的遗曲。虽然她也有着郭大妮一样漂亮的相貌,唱功也还不算差,但毕竟时过境迁,流行歌曲一拨拨地更新,旧曲被视之为弃履,所以除了一些念旧的老人外,黄大妮唱的旧曲不但没有她前辈所享受的追捧,甚至还被人嘲笑为不合时宜。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黄大妮的表妹王小玉登场了。
二、 “红妆柳敬亭”的歌声
梨花大鼓只唱不说,相对于靠评说为主的平话和评书,它对表演者的天赋要求更高,因为曼妙的歌喉是很难后天练就的。而王小玉就具备这种天赋。受家庭的熏陶,她十二三岁时就已经熟悉大鼓书的演唱技艺。她还很注意学习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腔,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她一听也就会唱”,她很有歌唱的天赋,“仗着她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她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老残游记》)。用《老残游记》的说法,她“是天生的怪物”。
王小玉还是个心性颇高的艺人,有鉴于表姊黄大妮的失败,她不满于已有腔调之平淡无奇,于是她做了一番创新,广取皮、黄、梆子腔等唱腔以及昆曲、小曲之长,创造出了山东大鼓“南口犁铧(梨花)调”新唱腔。《老残游记》引用了两位听众的谈话,虽然有些夸张,倒也可以拿来做个说明:“她(黑妞)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她的好处人学得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你想,这几年来,好玩耍的谁不学她们的调儿呢?就是窑子里的姑娘,也人人都学,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处,从没有一个人能及她十分里的一分的。”
十六岁时,王小玉跟随父亲到临清的街市上献艺。师史氏《历下志游》云:“黄之姨妹王小玉者,亦工此,随其父奏艺于临清市肆。梦梅花生客过临清,于将行前之一日,偕三五友人假坐逆旅,招之来度曲数阕,亦颇悦耳。王年十六,眉目姣好,低头隅坐,楚楚可怜。歌至兴酣,则又神采夺人,不少羞涩。吟红主人甚眷恋之,侧坐无言,有斗酒听鹂之感,诵昔人‘便牵魂梦从今日,再睹婵娟是几时之句,为惆怅者久之,亦可谓深于情者矣!”“便牵魂梦从今日,再睹婵娟是几时”这两句诗是宋代李昉赠襄阳妓所作,小玉不在乐籍,把这两句诗用在她身上似乎不妥,但她的神采和技艺实在是让人着迷和留恋。既然连袁枚都评价李昉这首诗写得“一往情深,言由衷发”(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我们也就不必责怪这位不知名的多情文人轻佻了。
十八九岁时,王小玉携妹妹黑妞来济南卖艺,献技于大明湖畔的明湖居和趵突泉边的四面亭。尤其是明湖居,它处在鹊华桥南,百花洲西侧,此处距巡抚衙门、提督学院很近,地理位置优越。它本身又是一个能容纳一百多张桌子的大戏园子,是唱大鼓书的风水宝地。因为有前几年演艺生涯的磨炼,王小玉的说书技艺较之临清卖艺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可以产生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用《老残游记》的说法就是“一纸招贴,举国若狂”。挑担子的挑夫说:“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吧。”店铺里的伙计说:“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当年那位美女秦罗敷出门采桑,惹得使君抓耳挠腮,使得“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王小玉说书的魅力,也可以与之相媲美了。
王小玉的说书,受到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欢迎。来听王小玉说书的,有挑夫伙计,有本地读书人,也有那些身着便衣、带着随从、坐着轿子的官员。王小玉甚至还给很多人带来了财路和就业机会——在等待她登场的一段时间,“光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
因为高超的说书技艺,王小玉在济南得到了一个“红妆柳敬亭”的美名。柳敬亭是中国古代说书界最有名的艺人,但他相貌不佳——面色黄黑,满脸疮疤、小疙瘩,被时人戏称为“柳麻子”。以柳敬亭来比王小玉,这既说明王小玉的技艺之高超,又说明此时的王小玉打动听众已经完全不靠娇羞和色相,而全靠曼妙的歌喉。
王小玉演唱的大鼓书好到什么地步呢?当时客居济南、有“明湖第一词流过客”之称的湖南诗人王以敏,也就是《老残游记》中那位听了小玉的说书赞叹不已的梦湘先生,曾针对小玉的说书专门写过一首诗:“变调何人采竹枝,居然谈笑千金值。君不见王家有女淡丰妆,玉娘小字香春风。明眸含睇水新剪,登场按拍天无功。……鱼龙曼衍鸾凤清,珠顺喉啭调新莺。坠如空庭杂花落,抗如百丈游丛行。凄如寒泉咽哀壑,寂如幽梦萦旗旌……”
王以敏将小玉的歌喉比作鱼龙、鸾凤、新莺、寒泉、幽梦,可见她的演唱是极富艺术性的。但用了这么多的比喻来作形容,反而显得太过空洞了些,倒不如刘鹗借王以敏之口对小玉演唱的效果所作的评价:“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她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她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
“三月不知肉味”,语出《论语•述而》,是孔子在齐地听到韶乐之后的一种类似高峰体验的感受,而相传韶乐的创始人正是山东大鼓的祖师爷大舜。刘鹗在这里拈出这句名言来形容王小玉的歌声,除了这句名言家喻户晓的缘故之外,恐怕还有一层溯源的意思吧!
三、 才子名角一相逢
最妙的当然是刘鹗本人散文诗般的描绘。他在明湖居的一次平常的做客,才子与名角的一次简单相逢,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中国曲艺史上的一段佳话。我们今天能把王小玉从文化的边缘发掘出来,使她避免事随人亡的命运,不能不对刘鹗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决口,一时间官府束手无策。第二年,刘鹗到河南投效河督吴大徵,利用自己的治河知识,参加了抗灾抢险,他“短衣匹马”,与工人一起劳作。刘鹗敢于大胆负责,同僚有所顾忌、不敢做的事,刘鹗都敢做,很快他就声誉鹊起。等到黄河合龙之后,吴大徵论功行赏,要把刘鹗之功报与朝廷,刘鹗却把功劳让给了哥哥刘梦熊,自己专心负责测绘河南、山东和直隶(今河北省)的三省黄河河图。
光绪十七年(1891),刘鹗受山东巡抚张曜(《老残游记》中的庄宫保)之聘,任黄河下游提调。这一段经历,被刘鹗写进了《老残游记》。第一回中,老残用从大禹传下来的方法给黄瑞和(黄河)治愈了浑身溃烂(黄河泛滥)的怪病,便是他来山东治河的隐喻。但遗憾的是,他的山东治河之行却是无功而返的。当时,关于黄河治理分为两种观点,刘鹗主张实行东汉王景“攻沙去淤”的办法,而候补道台施补华(即《老残游记》中的史钧甫)却主张实行西汉贾让“不与河争地”的办法。对贾让纸上谈兵的治河之法,刘鹗是坚决反对的,他借老残的口说:“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但是,张曜最终听从了施补华的意见,废弃了黄河民埝,退守大堤,造成黄河在山东章丘、齐河和长清三次决口,使得济南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一条哭声,五百多里路长。”
在济南,刘鹗先是只身住在历城县衙,后来接来家眷居住在小布政司街,不久又移居县西巷内的英武街,距著名的大明湖、珍珠泉、王府池子和曲水亭一带很近,这就为他去明湖居听王小玉说书提供了便利。
介绍完刘鹗与济南的这段渊源,我们再来看他对王小玉唱鼓书的描写是如何之奇、如何之妙。这是两段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文,在所有描写音乐的文字中,恐怕也只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能够与之较一高下: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她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王小玉传递给听众的是声音,是入于听众之耳的,但是刘鹗却用通感的手法把这种听觉转化为视觉,并以泰山、黄山和东洋烟火来作比喻,让读者产生出无穷的联想。的确,也只有像刘鹗这样有着超常音乐感受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欣赏者,才能传达出王小玉歌声的美妙。
有人说,小玉当时唱的是梨花大鼓的名段《黑驴段》,这话并不可信。因为,王小玉唱完那支曲子,又让黑妞唱了一段,自己重新出场时唱的那支才是《黑驴段》。虽然也全是快板,越唱越快,但是从刘鹗“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逊一筹了”的评价来看,前一段并非是《黑驴段》,而是另外一支同《黑驴段》一样有着“赶腔夺板”快节奏的段子,可惜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支了。
以王小玉在济南的票房影响力,她的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观的。据李贵回忆,王小玉“置良田数顷,还自备双套辕大车”。这在当时可是够阔气的了。但是她的妹妹黑妞却是红颜薄命,早早去世了。据1916年出版的凫道人《旧学庵笔记》记载,清末大臣端方为其《明湖秋泛图》题词,有“黑妞已死白妞嫁,肠断扬州杜牧之”之语,可知黑妞早亡,而王小玉与她的前辈郭大妮一样,在嫁为人妇后离开了大鼓舞台。对喜爱她的听众来说,真正是“再睹婵娟是几时”了。
据王以敏的外孙女钱鼎芬著文回忆,她儿时曾经见过王小玉与黑妞的合影。在她的印象中,那是两个青年女子,上衣的衣袖挺肥大,衣袖上还有很宽的镶边(见《“明湖第一词流过客”——王梦湘》,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四期)。《老残游记》也描写黑妞“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白妞的“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可见,她们姐妹是经常穿这种镶边的衣服的。王小玉之后最著名的梨花大鼓艺人谢大玉(其父谢其荣,又名“神手谢老化”,曾经担任小玉姊妹的伴奏),曾保存有一张王小玉的照片。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参观新改建的明湖居剧场时,表示要将照片贡献出来,悬挂在剧场内,可惜她不久就去世了,照片也不知所终。师史氏描绘小玉的外表只用了“眉目姣好”四个字,《老残游记》也说小玉“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可见,王小玉应该是貌不惊人,但是,作为梨花大鼓由农村走向城市并开启这种曲艺形式繁荣局面的重要艺人,平凡的相貌又何妨她成为梨花大鼓和济南人文风情的形象代言人呢?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