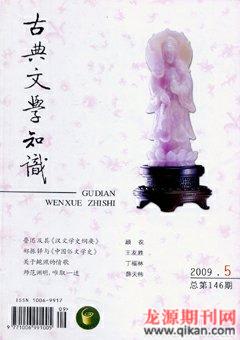李商隐《无题二首》解
董希平
在李商隐数十首偏重感觉印象而含义很难坐实的无题诗中,本文主要讨论的应该是文笔比较细密、具体的两首——当然它们同样令人产生难以把捉、无从下手解读的慨叹: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其一)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其二)
细玩诗意,这两首虽二实一,在内容的描写、交代上相互补充,实际上叙述的是同一情事。只不过第一首分场景写男女交往中的思念、相遇与期待,粗线条地描画出所咏主题,第二首则宛若第一首的注脚,极写女子的痴情与身世遭际之感。如果说第一首是宏观描述,那么第二首就应该是近距离的局部特写。两诗在情脉上前后呼应,圆融为一,完美地再现了诗人与无名女子的情事与情愫。
一、 疏解
限于篇幅及写作重点,本文拟先详解第二首,然后对第一首予以大略解说与疏解。
先看第二首。“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首联交代出时间、场景及主人公,亦为后文的叙述张本。重帏深深,暗示这是富贵荣华、常人难至之居;堂名莫愁,又指出主人公的女性身份——除了本诗之外,“莫愁”一词在李商隐诗中凡五见,为:
卢家文杏好,试近莫愁飞。(《越燕二首》其一)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二首》其二)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
客自胜潘岳,侬今定莫愁。(《灯》)
若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有愁时。(《莫愁》)
“莫愁”本为古乐府中所歌咏之美丽女子,据载有二:
一为石城莫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西曲歌》之《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该诗前小序云:“《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忘愁声,因有此歌。”
一为洛阳莫愁。《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所载之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此时及后来人们就常以莫愁来指代美丽、富贵、无忧无虑的女子,如《玉台新咏•续玉台新咏》中梁陈之际的周弘正《咏新婚》:“莫愁年十五,来聘子都家。婿颜如美玉,妇色胜桃花。带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暂却轻纨扇,倾城判不赊。”这里就是借莫愁来比喻、赞美一位美丽的新婚女子。
李商隐诗中的莫愁,也同样指代美丽而幸福无忧的女子。联系前边所引李商隐诗五处涉及莫愁的地方,我们也不难想象出这首《无题》诗中莫愁堂主人的美丽与富有。然而,这位女子的精神生活却显然并不幸福,“卧后清宵”显示其寂寞与孤独,而“细细长”三字则清晰地表现出这种针刺般的痛苦对于心灵的噬蚀,以及处于此种痛苦折磨之下,时间缓缓滑过心头的漫长感觉。
“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颔联和颈联承接上文,全面诠释主人公复杂而难以名状的内心世界,是全诗的核心。颔联所用是两个事典,神女典出宋玉《高唐赋》,谓楚襄王游高唐,遇巫山神女,谓王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而远在李商隐之前,神女在诗歌中就已经成为容貌美丽,生活幸福得近乎仙人的女子的代名词,在宫体诗流行的南北朝,诗歌中的“神女”,更是多为此义:
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未眠解著同心结,欲醉那堪连理杯。(梁•江总《杂曲三首》之三)
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梁•简文帝萧纲《咏美人看画诗》)
合欢芳树连理枝,荆王神女乍相随。谁家妖艳荡轻舟,含娇转眄骋风流。(北齐•辛德源《咏东飞伯劳歌》)
翻检《玉台新咏》、《乐府诗集》乃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涉及“神女”的作品就更多了,神女含义与上述诸诗中之神女相类,于此不难推测义山心目中神女之如花美貌和如仙如梦之生活及追求。但对这无限的梦想憧憬,作者却以“元是梦”三字作结,冷酷而无情,于强烈的反差中透出莫大的哀痛与幻灭——“神女”的追求思念甚至包括她自己的美貌从开始就注定只能是大梦一场!
小姑典出古乐府。《乐府诗集•吴声歌曲四》之《神弦歌》有《清溪小姑曲》:“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其小序题解云:
《续齐谐记》曰:会稽赵文韶,宋元嘉中为东扶侍,廨在青溪甲桥。秋夜步月,怅然思归,乃倚门唱《乌飞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许,诣门曰:“女郎闻歌声,有悦人者。逐月游戏,故遣相问。”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暂过。须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许,容色绝妙。谓文韶曰:“闻君善歌,能为作一曲否?”文韶即为歌“草生盘石下”,声甚清美。女郎顾青衣,取箜篌和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脱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晓幕。伺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连宴寝。将旦别去,以金簪遗文韶。文绍亦赠以银碗及瑠璃匕。明日,于青溪庙中得之,乃知得所见青溪神女也。按干宝《搜神记》曰:“广陵蒋子文,尝为秣陵尉,因击贼,伤而死。吴孙权时封中都侯,立庙钟山。”《异苑》曰:“青溪小姑,蒋侯第三妹也。”如果说“神女”一句尚是伤悼心愿虚幻似梦的话,那么小姑一句则以清溪小姑与赵文韶虽有遇合却终因仙凡之隔而终归虚妄为底蕴,暗示出才貌如仙的女主人公一样承受着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异给自己与恋人带来的莫大痛苦。“本无郎”中一个“本”字,揭示诗中女子虽用情至深,但却似乎与所思念对象竟只有匆匆一晤,这可以与第一首中“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相参看,有惊鸿一瞥之缘而无把手言欢之份,虽有而实无。“本无郎”三字看似违情,而实合理,正是痛极之语。
颈联则由缥缈凄婉的氤氲转至柔弱清丽的物境中,颇显自怜之意。上句中,风波与菱枝,一强一弱,对比鲜明,而诗人的倾向也尽显无遗。在李商隐诗中,“风波”始终是恶劣情绪的制造者和诱因:
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鸳鸯》)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泪》)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春日寄怀》)
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无题》)
本诗也不例外,菱枝这一诗中物象,为李商隐首创(李商隐以前的诗人均未用过),深具柔弱馨香的美质。菱枝本弱,又置于强横无常之风波中,则其凄楚之状可以想见,“不信”谓明知而故意如此,愈显风波之暴,菱枝之惨,而女主人公内心的深哀,遂得以委婉而淋漓表露:外既有强阻,内复无强援。颈联下句中,桂叶喻女主人公自己,盖桂叶喻美人之传统,久已有之,如唐玄宗的江妃《谢赐珍珠》如此:“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李贺《河内诗三首》之《湖中曲》亦然:“长眉越沙采兰若,桂叶水葓春漠漠。”清露当喻外援,盖在湿润天气之下,桂树之香气愈加浓烈,所以诗人有此联系。然“谁教”二字,谓本可如此而竟不如此。则芬芳内蕴之桂叶本可借助月露滋润而尽情飘香,然月露行有余力却冷漠无情,桂叶遂不免凄苦之厄。李商隐另一首《深宫》:“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上句与该联上句同,下句则与该联下句相反,二者手法与构思绝似,可以参看。
尾联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如女主人公尽诉心事后的一声长叹,充溢着斩截无悔的意味,却又余音袅袅,意味无穷。“直道相思了无益”,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认为“直”为假定之词,“凡文笔作开合之势者,往往用‘直字以垫起,与‘饶字相似,特饶字缓而直字劲耳”。该句意思为:“就算这种刻骨铭心的相思于事无补,就算春梦成空。”——李商隐诗中每有这种慨叹: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宿骆氏亭寄怀崔雍┐拶颉)┆
白日相思可奈何,严城清夜断经过。(《赠歌妓二首》其二)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
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燕台四首》之《秋》)
“未妨惆怅是清狂”——“未妨”,即不妨之意,为唐人习用语,如白居易《和答诗十首》之《和思归乐》:“谁谓谴谪去,未妨游赏行。”石仲元《阳朔道中》:“文网牵人宁底急,未妨得意看山来。”均为此类。“清狂”,《汉书•昌邑王传》:“清狂不惠。”注云:“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如今白痴也。”“清狂”在唐诗中多为放逸不羁之意,如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一:“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李咸用《公无渡河》:“有叟有叟何清狂,行搔短发提壶浆。”然此处当如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所解:“清狂为不慧或白痴之意。”而该句之意则为“即使相思无益,亦不妨终抱痴情耳”。汉乐府有《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该诗尾联两句情感之浓烈虽不及《上邪》,其劲直与精致实有过之。
再看第一首。
首联写女主人公于夜深人静之际,用凤尾香罗缝制碧文圆顶罗帐的情景。深深的夜色,轻柔的香罗,衬托出女主人公娴稚的气质。“罗帐”一物在古诗中一直是作为相思男女的背景陪衬出现的,如《玉台新咏•续玉台新咏》陈后主诗:“自君之出矣,房空罗帐轻。思君如昼烛,怀心不见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汤惠休《白纻歌三首》其三:“秋风袅袅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乐府诗集•江南弄中》载沈佺期《凤笙曲》:“岂无婵娟子,结念罗帐中。”至晚唐,罗帐已经成为积淀着女性幽怨的物象,缝制罗帐至深夜,这一行为本身己微妙地传达出女主人公的心态。
颔联两句写男女主人公短暂如惊鸿一瞥的相遇:男子驱车匆匆而过,女子则含羞以团扇半掩面庞,露眼偷窥,虽相见而未及通一语,羞怯、甜蜜、遗憾诸般复杂感情,尽在不言中。“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月魄”,月初生或圆而始缺时有体无光之部分。“扇裁月魄”,指裁制的扇,形如圆月。而团扇亦为古代女子常用之物,或可为女子身份之象征,古诗人咏及男女之事,往往用之。如《玉台新咏》卷五载何逊《拟青青河畔草》:“歌筵掩团扇,何时一相见。”班婕妤《怨歌行》:“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车走雷声”指代男子,司马相如《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李商隐诗中常有这种用法,如《无题四首》之二:“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柳》:“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
颈联写匆匆邂逅之后的隔绝与悠长思念。意为自己已经孤独地伴随着逐渐黯淡的灯烛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眼看春事已过,时至初夏,石榴花盛开似火,而所思念的人却杳无音信,石榴花旺盛的生命力更使为情所苦的女主人公生出青春易逝的忧伤。“曾是寂寥金烬暗”,古诗文中的孤独灯烛常常是寂寞的象征,而“金烬暗”又有双关之义,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之叹。“断无消息石榴红”中“石榴红”与上句中的“金烬暗”相对,一边是女子正当盛年妙龄(按石榴在古人眼中又与女子有关,如《全唐诗》卷五载武则天《如意娘》:“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一边是为遥遥无期的相会苦苦等待,个中哀苦,可以想见。
尾联叙女子所思念男子的美好姿态以及渴望与之相会的心情。“斑骓只系垂杨岸”,叙所思念之男子的距离曾经如此之近,但近而不可见,更增悲苦之情。“斑骓”,男子所乘之马。《尔雅•释畜》:“苍白杂毛,骓。”《重修玉篇》:“骓,马苍白杂毛色也。”李商隐诗中,多用斑骓指代意气风发的俊美男子,如:
白道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无题》)
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对雪二首》其二)
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春游》)“何处西南待好风”意谓:什么时候能等到美好的西南风,将自己吹送到爱人身边呢?此句化用曹植《七哀》诗:“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二、 主题
全篇字面意思如上所解,但是正如李商隐的其他无题诗一样,“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这两首诗的主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而言,可分为两派,一为咏男女情事,一为寄托身世之慨。
先看前者。
一、 谓之艳诗之变调:许学夷《诗源辩体》认为“诡僻”:商隐七言律语虽秾丽而中多“诡僻”,如“狂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句,最为诡僻。“……论诗者有理障、事障,予窃谓此为意障耳”。王夫之《唐诗评选》则认为:“(‘重帏深下莫愁堂一首)艳诗别调。”
二、 认为是怀人之作。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以为首章“咏所思之人,可思而不可见也”,次章,“此义山自言其作诗之旨也”。
三、 记录情事之作。苏雪林、陈贻焮先生曾先后联缀李商隐写情诸诗,演绎出义山恋爱事迹,其中无题诗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再看后者,这是明清以来很流行的解说,均以为是借闺情感慨身世:
一、 或以为自伤平生,像徐德泓《李义山诗疏》:“二首皆慨不遇而托喻于闺情也。”胡以梅《唐诗贯珠》:“(首章)是遇合不谐。”“次章,此以莫愁比所思之人也。”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也以为:“李青莲‘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二语,可作此二诗注脚。前诗言不求人知也,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故假借女子以为词。”
二、 或具体指明感慨内容。如陆昆曾《李义山诗解》:“按本传:‘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二诗疑为绹发。因不便明言,而托为男女之词,此风骚遗意也。”而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说得更详细:“(义山)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也。”近人汪辟疆亦持此说:“此大中五年义山应柳仲郢辟,将赴东川,决意令狐之诗也。”
黄侃的解读,大约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代表性结论了:“义山诸无题,以此二首为最得风人之旨,察其词,纯托之于守礼而不佻之处子,与杜陵所谓空谷佳人,殆均不愧幽贞,而解者多以为有思而不得之词,失之甚矣!”
概言之,义山《无题》诸诗,本就歧义丛生,主题晦涩难明。其16首直接以“无题”命名的诗作中,可编年者只有3首(至于只取作品首句字词为题,看似有题而实则无题的作品就更多了)。而义山以骈文文法作诗,又偏好带有神仙香艳色彩的典故,故给自己诗歌的解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义山自身经历坎坷,多遭情事而又具敏感多愁的诗人气质,有用世之志却不得一开襟怀,更加剧了这种语义的复杂性。实际上,义山诗的这种难解情形,义山在世时就已存在,其《有感》诗云:“非关宋玉有微词,确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所喟叹的也是这种杂解纷纭的状况。
其实,这种以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比兴代言传统,自屈原以来就代代相继、绵绵不绝,尤其是这类兼陶写情怀和男女情事两种色彩于一身的无题诗,其含义本就难以确指。而作者自己创作这类诗歌之时,其平生遭际与感慨,情场之聚散悲欢,家庭之漂泊难安,诸种情感纷至沓来,难以明辨,下笔之际,又岂能一一分清?作者本人已是如此,更何况与作者隔了数层的读者兼后代人?
诗无达诂,前人早有此叹。我们阅读这类诗歌,大可效释子舍筏登岸的读经修行之法,舍其纷繁诗象而阅其混沌诗情,以空灵之情寻求与诗心的契合,藉以达到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可也。所谓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能够获得不形诸文字的理解,也就是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