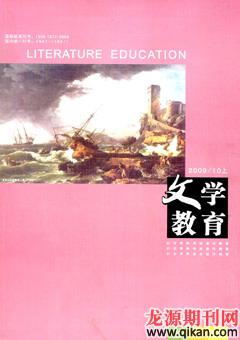从阿涅丝的手势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莫丽娟
一、阿涅丝的诞生
在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作者在一开始就跳出以往叙述者力图制造的真实情境,向读者坦言:“阿涅丝出现于一位六十岁的老太太的一个手势之中。我在游泳池边上看到这位老太太在向她的游泳教师挥手告别,她的相貌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清,可是她那个手势却在我心中唤醒一种不可遏止的、难以理解的怀旧情绪,在这种情绪中产生了这个我把她叫做阿涅丝的人物。”这个叫阿涅丝的女人不是来自生活的原型,而是不为作者所知的一个人。结合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阐述的小说理论,这种反常的小说技巧并不足怪。他一再强调,小说家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先知,而是“存在的探索者”。存在之思被视为小说的终极目的,为了探讨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昆德拉惯于用符号为小说人物编码。在昆德拉看来,把握自我,“就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这种编码艺术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得到实践。在其成名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他将灵与肉视为解析特雷莎的关键词,而将轻与重视为托马斯的生存密码。正是这些关键词支撑起了每个人物的生存状态,标志着每个人物的不同可能性的侧面,支撑起整部小说的大厦。
与其他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在《不朽》中,作者并非通过词汇,而是手势来对人物存在可能性进行编码。阿涅丝的手势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按照叙述顺序分别是与游泳教练、少年的恋人、和她的父亲告别。在与游泳教练的告别中,这个六十岁或六十五岁的太太(这时候还并不能称之为阿涅丝)回头时的手势姿态优雅,充满魅力,这种魅力并不为这一年龄的女人所有,它是处于时间之外的。这种不属于时间的本质在作者头脑中唤起一个叫做阿涅丝的名字的女人。在制造出阿涅丝这个人物之后,作者试图通过另外两次不同时期的手势来探寻她的存在处境。在与少年的恋人的挥手告别中,阿涅丝受到了父亲喜爱的女秘书的影响,这一优美的手势在阿涅丝心里唤醒了一种巨大的模糊的希望,这种希望在她每次向朋友告别时都得到实现,直到她发现妹妹洛拉也开始模仿姐姐的这一优美的手势。阿涅丝发现这一手势并不为她独有,她一直在和千千万万的人共同使用这一手势,于是抛弃了这个手势并开始对所有的手势持怀疑态度(只保留必要的交流手势,点头或摇头等)。在与自己幻想出来的陌生人的对话中,她对自我存在的理解逐渐明晰:不与人类为伍。对于阿涅丝而言,只有一种脱离人类,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的真正办法:那就是与她自己决裂,废弃定义她那个自我,成为自我的叛离者。这个在她身上沉睡的手势某一天在她与病重的父亲告别时复苏。在莫可名状的动力下,她在同一个地点,用跟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女秘书相同的手势向父亲告别。这一告别仪式使得两个相隔遥远的时代相遇,突然她意识到她们也许正是父亲生前所爱的唯一两个女人。阿涅丝理解到。父亲和她一样,通过躲避的方式与世界决裂(这种方式她之前并不理解,但后来领悟到了)。与其说她是在向父亲告别,不如说她是与这个世界告别。
二,手势的复制
手势对于阿涅丝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构成她的生存编码,在文本结构上它衔接了女秘书和洛拉两端,为作者从阿涅丝的生存可能性出发探寻其他个体的可能性提供了途径。与阿涅丝对这个手势的果断抛弃不同,洛拉复制并坚持了这一手势,即使到了小说的末尾,这一手势还在她的身上出现过(也是在游泳池,相信这与它的第一次出现地点的雷同不可能单单以巧合来解释)。洛拉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人类在使用同一手势,或者她并不介意这点,正是对这个手势的默认显示了洛拉和阿涅丝的不同:洛拉更加强调人的类特性。为了展示洛拉不同于阿涅丝的存在面,作者赋予她另一个手势:渴望不朽的手势。在对感情失望至极的时候,洛拉渴望通过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转移感情带来的伤痛时,她一边重复一边将手指指向心窝,随后将两条手臂挥向天空。阿涅丝虽然无法想象这一晦涩的手势到底是指向什么,但是她知道洛拉所指的一定是崇高遥远的事情,决不可能与洛拉之前提到的自杀有任何关系。事实证明洛拉要从事的是不朽的事业,尽管这个不朽不同于贝蒂娜那介入历史的伟大的不朽,但仍然是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微小的不朽,这种不朽超越了此时她所感受的痛苦,让她留在身边人的记忆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挥向天空的时候连洛拉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将要做点什么来超越目前的痛苦。挥手这一手势在这里成了跳出因果链之外的一个插曲,挥手并不是为洛拉头脑中事先所准备好的动作,而是一个非理性的决定。这个手势抓住了洛拉,并决定了她的行动。可以说,洛拉诞生于这一渴望不朽的手势中,它构成了洛拉的生存编码。
阿涅丝生前的丈夫,洛拉后来的丈夫,保罗,并没有目击到洛拉的这一渴望不朽的手势,倒是受洛拉重复的挥手的手势的吸引,于是这一手势在保罗那里得到第三轮复制。这一笨拙的复制揭示了保罗对爱情模糊茫然的认知。在保罗与阿涅丝的女儿布丽吉特那里,为了宣扬年轻一代对绝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求(这种追求成为她征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取悦父亲的有力武器),她将这个手势转变为反抗侵犯人权的手势。作者正是通过作为生存编码的阿涅丝的手势继续探寻,在这个编码的支撑下展开对阿涅丝的叙述,在此过程中,手势随着话题的深入而延展开来,逐渐分裂为几条叙述线路,手势在每一条叙述线路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这种叙述线路更像是道路而非公路,因为“公路总是笔直的,唯一的;道路,从其定义本身而言,就是蜿蜒曲折的,就是一张错综复杂、秘密的网中的~部分。”道路式的叙述引起更加深层的哲学式探讨,继而辐射到其他人物的生存可能性。这个最初出自于女秘书的手势在小说中另外的人物的存在密码中显示着不同的意义,当然,这些密码“不是抽象地研究的,而是在行动中、在处境中渐渐显示出来的。”
三、双重复调
《不朽》中,挥手这一手势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穿越过程,从女秘书到阿涅丝,再过渡到洛拉、保罗以及布里吉特,甚至贝蒂娜等人。作者对不同人物生存状态的探讨并不只如上所述仅仅采用叙述的方式。作者更倾向于在制造手势后借用哲学性的沉思来追问背后的深层含义。作者经常中断叙事插入议论成分,在最大限度上追问人物的生存可能性。作者认为,小说的魅力并非在于叙述之中,而是在行动停止之处。这种再三缓解故事情节的手法在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那里就有了。在《奥德修斯》中,奥德修斯返家报仇过程中身份的暴露这一紧张情节就是由于其伤疤的被发现而悬置,诗人开始插入对他伤疤来历的回顾。在荷马史诗中,情节高潮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史诗的总体风格并非要紧紧扣住读者或听众的心弦。小说《不朽》中,由于作者将存在之思作为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插入部分摒弃了单一的叙述,而采用哲学式的探讨方法。在《不朽》中,围绕着手势这一概念,他引出了众多讨论。在构造阿涅丝的手势时,昆德拉从人口膨胀和固定手势数量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手势主宰人类而非人类主宰手势的结论;布里吉特对于侵犯人权的抗议引出了意愿演变为权利的思考……这种讨论因为形式上与传统小说单一叙事方式背离而招致离题的怀疑。这种怀疑更多是出于形式层面的考虑,但正是这种颇具实验性的探索构成了小说形式上的张力,成为昆德拉小说最大魅力所在。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就对布洛赫在小说艺术上的革新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小说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只要想象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就可以了),这正是因为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与科学知识的倾向……这一点,当然以为着要对小说的形式进行深刻的变革。”
四、结语与疑惑
不论是对人的生存可能性进行编码,还是杂糅小说叙事和哲学沉思为一体,都彰显着昆德拉在小说形式方面实验性探索的可贵努力,其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然而,他的实验性探索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小说文体限度的追问:在各类学科形式逐渐多元化的现状下,究竟小说与其他学科之间还有没有本质上的界限?如果有,究竟是小说中的哪种成分(主题,题材,情节,人物)超越了其他学科特性而使得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如果没有,那么关于不同学科的划分是不是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了?这些问题有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