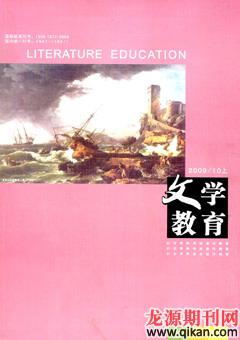浅析塔尔科夫斯基的《镜子》
李泓锦
电影诞生伊始,卢米埃尔兄弟和乔治梅里爱就将电影导入了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之于电影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艺术思潮永远是时代的产物,此后法国诗意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带来了现实主义的繁荣兴盛,而法国超现实主义、德国表现主义亦将表现主义推到了创作的顶峰,但两者的审美原则和创作手法的分歧则日趋明显,纪录片和“纯电影”美学实验更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极致。“新浪潮”和“左岸派”关于“双重现实”理念的提出,为艺术电影带来了全新的思路,调和了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矛盾。此后的电影作者们则不再拘泥于表现形式的局限,“真实”是唯一的原则。创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创造现实的艺术家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线。经由电影手法创造的内在世界应被视为现实,因为它在被记录的那一瞬间已被客观地建立了。这也是塔尔科夫斯基对作品中真实的一贯准则和追求,他电影的代表《镜子》更是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力证之一。
《镜子》的确是一部高度作者化的诗意电影,从形式到内容充满了导演个人与私密的企图,整个叙事中似乎不那么恰当的纯粹个人抒情的语气让人感到不悦,且易产生对导演某种程度上妄自尊大的误解。《镜子》叙述了一个深为痛苦所困的人的故事,因为他感觉无法回报家人所给予他的一切,就觉得自己不够爱他们,这一念头折磨着他并无法释怀。这是一部关于他的思想、他的回忆以及他的梦境的电影,尽管这个人物在电影中完全没有出现,但那些表象的事件、主角的动作、行为模式都受到了影响。从《镜子》中我们发现体现于文学和诗歌中的抒情主角的影像得到回响,他的信仰、他的判断以及他的思考建构出一个图像,甚至可以清楚地界定他的形貌,这个人物无疑就是导演本人。从未出现的角色拥有了表情、鲜明的个性、以及丰满的内心世界。无论那些碎片式的回忆、呓语般的独白、梦境和梦境中的梦境,这些都是表现主义的典型特征。
然而所有的片断经过漫长的时间跨度,在贯穿始终的虔诚气氛中最终统一成严谨缜密的整体,这一切都是通过导演对于艺术感觉的把握在潜意识当中创作完成的。真实的梦境与真实本身融为一体,呓语在耳边回荡如浩然的诗篇,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静静流淌,此时你方能感悟作品的伟大,摄影师尤索夫最后也坦承,虽然很不愿意,但他认为这是塔尔科夫斯基最好的作品。那正是现实主义所追求的真实带来的巨大震撼,《镜子》的目的在于重现那些导演所挚爱与熟识的人们的生活:其活动和矛盾,其动力和冲突。他巨细靡遗地披露他所见所闻的真实——就算并非人人都能接受那样的真实。电影将新闻片、梦境、现实、希望、假设和回忆的镜头穿插出现,成为一种起伏纷扰的境况,用来对照主角所遭逢的无以回避的存在问题。
至此,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归结为一种共通的态度,因为电影无法像文学作品一般使用读者的经验,并考虑在每位读者心里产生一种“美学的同化”。导演必须以最极致的诚恳来陈述自己的经验,这当然不容易办到。在这种情况下导演的经验亦可能是同等重要的全人类的经验,就一个人的心灵经验而言,昨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一百年前人类发生的事可能有完全相同程度的意义。当然,艺术家有时也可能迷路走失;但只要他诚心诚意,即使是他犯下的过错也有其趣味,因为那些过错呈现了他内在生命的现实,呈现了他置身外在世界所履历的漂泊与挣扎。没有人拥有过真正完整的真实,那些可以表现、不可表现的争辩试图扭曲真实。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他们老是说艺术必须反映人生等等。真是胡扯:作家自己创造生命,仿佛生命从未在他面前存在过……”
电影影像的塑造是具体的、有形的且是四度空间的。不过绝不是所有电影画面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影像,常常它们只描述了一些特殊的层面。塔尔科夫斯基一直执著地尝试让人们相信,作为一种艺术的媒介,电影自有其相当于散文的可能性,他证明了电影能够以其连贯性来观察生命,而不致生硬地加以干扰。因为那正是导演所了解和坚信的电影真正诗意本质的所在。关于诗意气氛,塔尔科夫斯基以印象派为例,认为印象派为了霎那而着手刻画霎那,以表达瞬间的意义,那应该是艺术手段而非目的。也许形式过度单纯化可能会有矫揉造作或刻意斧凿之虞,因此塔尔科夫斯基在电影中尽可能地剔除了镜头里所有暖昧和影射的手法——那些被视为“诗意气氛”之标记的元素。而气氛乃是源自中心思想,源自作者自身观念的实现。所有的物品、风景、演员的声调都将随着整体基调而开始产生回响。一切都将互相关联且不可缺失。事事物物逐渐全面相交更迭、互生共鸣,气氛便油然而生。
塔尔科夫斯基的伟大之处,或者说《镜子》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这种以诗意气氛为本质、完全不同于其它艺术形式的、纯粹的电影艺术。《镜子》当中包含了各类的艺术形式,电视、诗歌、照片、纪录片、交响乐、文学书信和油画,然而电影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将所有的这一切融人了电影本身的叙事当中,自然流畅没有任何的生硬抽象,它们都成为表达电影情感的元素,发挥了自己的最大功能并且精确地吻合电影的诗意气氛,隐约中还散发着象征与暗示的意蕴。影片不仅限于童年与母亲的回忆,而且由个人、家庭问题扩展到苏联甚至是本世纪的现代史。观众感觉到巴赫、佩戈莱希,感觉到阿尔谢尼伊的诗歌,感觉到普希金的信函、红军强渡锡瓦什海、西班牙内战,当然也感觉到导演对于童年的复杂回忆以及种种私密的家庭情事。又譬如达芬奇的肖像画《持杜松的年轻女郎》被用于父亲请假回家与儿子短暂晤面那场戏中。我们很难描绘该画最后究竟在我们脑中留下了什么印象,甚至也无法肯定地表示我们到底喜不喜欢那个女人。究竟她是惹人怜爱抑或讨人嫌恶。她既令人着迷又叫人讨厌,她的一切具有一种难以形容之美,同时又显得冷酷、疯狂。这一疯狂并非影射世界的浪漫与诱人,而是超越了善与恶,带着负面色彩的美,它具有一种堕落的元素和美的元素。在《镜子》里这样一幅肖像画将一种超越时间的元素引入了依序发展的瞬间中,同时让女主角与该肖像画并列,强调了她和女演员同样具有既迎且拒的魅力。
《镜子》螺旋形的叙事方式也很独特。在三层螺旋结构中还有几条纵轴线贯穿其中。螺旋结构的第一圈是大螺旋,籍由回忆年轻时母亲美丽的形象为开端,依序连接至主角现在的妻子、年老的母亲与曾经爱恋过的少女等四个形象,展现出主角心中困境与历史处境的关联;第二圈是中螺旋,影片继续以这四个女性形象为基本元素,但顺序有所变化与重复,相对于第一圈螺旋的许多战争纪录片的大叙述,第二圈则逐渐缩小至个人与家庭的问题:第三圈是小螺旋,将扩散开来的螺旋收束成一点,使年老的母亲与年轻的母亲在同一时空中出现,以形成巨大的时间张力。在纵轴线上则是飘浮与着陆(影片中多次出现热气球降落、牛奶滴落和瓶子掉落的镜头)、父亲的诗与时间的永劫循环(情景与遭遇的不断重复,年轻时的母亲和现在的妻子、年轻时的自己和现在的儿子均由同一演员出演)等为线索。几条纵轴线使得影片的螺旋结构不至于扩散,又使故事的发展具有完整的一贯性,并使复杂的影像元素得以流畅地串连起来。
导演艺术的修养之高和艺术电影对精英文化的不懈追求导致了《镜子》某种程度上的晦涩难解,但即便不能从文本上彻底地读懂电影,亦不影响影像本身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任何人都可以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当作一面“镜子”,在其中会看到我们自己,当一部电影的构想被赋予宛如生命般的形式并专注于其感性的功能,那么观众便可能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来联系电影的构想。于是电影就成为了唯一的光明。我们可在漆黑的世界里沉醉于这些精雕细琢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