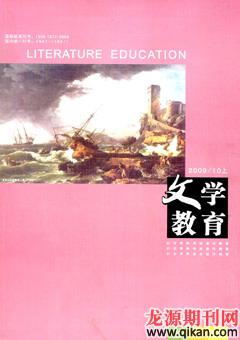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舞舞舞》中的死亡意象
陆 雁
《舞舞舞》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部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其主旨在于揭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虚无。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采用现实与幻想交错的双线结构,并将“死亡”这个严肃且常见的主题贯穿其中,本文便试图从此方面结合作品本身探讨“死亡”在这部后现代作品中的意义。
小说主要写“我”在冥冥之中走进一间陈列了六具白骨的亦真亦幻的死亡之屋里。身边的朋友在接连的日子里相继死去。其中的五具白骨已有了对应之人。度过了一段死亡陪伴的惊魂日子。“我”终于在宾馆女服务员由美吉那里找到了安全感,也有了在安静城市过安静生活的具体计划。可那第六具白骨的意味却始终未点透。“我”依然脱不出死亡之屋。
可以说,整部小说与“死亡”两个字眼是密不可分的。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传统的审美转向审丑。现代电影不再把花前月下的爱情作为唯一的赞颂对象,而让失之交臂、残缺不全的爱充满荧幕;同样,污秽、死亡意象经常性地出现在现代文本中,也显示了文学由审美走向审丑的特征。村上春树身处这一时代,或多或少地受了时代大潮流的影响。就我看来,他笔下的死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死尸的呈现
所谓“死尸的呈现”,是指作者把尸体的污秽形式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村上春树笔下的死亡大多数也有此特点,尤其一以《舞舞舞》为代表。该作品中对“咪眯”死的描写便体现出这类特征。
“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作者进而借警察之口道出咪眯死时的场景:“才二十岁出头。是被人用长筒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脑袋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
村上在这里将死亡过程的想象性体验展示在读者面前,并不是有意愿地去指责杀人者虐杀无辜生命的无聊及其残暴,而是平平淡淡地一一道来,如叙家常。冷静的叙述所对应的是叙述者实施犯罪时的理性和清醒,但理性和清醒中也夹杂着心理的混乱和矛盾。这便揭示出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格分裂”的普遍倾向。这种情况下的死更多地可以理解为是自我意义的放逐,而不单纯是生命本体的消逝。在村上的作品中,“自我”是一个破碎的片段,以前的“完整视域”被打破,“自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也不再是“整一和连贯的自我”,自我的消融反倒成为大势所驱。表现人的卑微感,揭示出人类的当代困境成为其中主流。当自我的力量已无法与世界对抗时,人物便选择了死亡。《舞舞舞》便向读者表现了这样一群人物,他们的自我在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下走向了畸变。村上向我们展示的更是一些被社会巨大压力挤得无处躲藏而“向内转”的一类“精神分裂”的人,人物性格的悖理与人格的分裂特征被彻底地展现出来。正如小说中五反田所说的“哪里有意思?我们生存的意思到底在哪里?”
在他们心中,一切都归于无意义,他们与外部世界是不和谐的,“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与他人‘一道加以体验,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置身于环境中加以体验。”于是只能在孤独中体验自己,他们将自己孤立起来,通过反常的行为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对立冲突的关系,更甚者走向了一种‘自我幽闭的状态。小说中放有六具白骨的房间便是最为幽闭的小说场景,不仅象征了人物在普通日常生活中与社会的隔绝和远离。也象征了人物在心理上、精神上与外在世界的隔阂,更象征了人的孤独感、自我幽闭的倾向。极度幽闭与孤独实质上便是死亡的征兆。小说中,“我”在夏威夷的闹市区看见了喜喜,于是我便一直追寻着她,走进了一排办公楼中的一座,进而走上楼梯,来到了有六具白骨的房间。此时,小说的叙述视角从喧哗的街道移向一座安静的办公楼,又由一座办公楼移向一个房间。随着视角的变化,封闭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给小说表现的死亡平添了几分恐怖的效果。
精神分裂使他们采用极端方式与社会对抗,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随时成为他们的报复对向。在中国,以残雪、余华为代表的一批先锋作家,也很热衷于死尸的展现,在余华的《现实一种》里,一家四个男性都在互相的虐杀,直到最后一个男人被枪毙后还被家人出于报复的动机把尸体捐献给医院做移植和解剖用,当医生各自拿着工具,各取所需,嘻嘻哈哈地解剖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有严重“人格分裂”倾向的人。
二、象征之死
小说中有些死亡的意义并不停留在表面,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人死了”不是仅仅真的为了表现“人死了”,而是意在往深处挖掘,是在说“什么东西死了”。此时的人只是这个“东西”或某种精神的载体罢了。《舞舞舞》中“笛克诺斯”型的死,即象征之死。它是“象征手法的意义放逐”,在文本中,笛克诺斯即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里美好的象征,这位独臂诗人能做出高雅可口的三明治,也为大家煮咖啡,他过着近乎仆人的生活,当我们吃完时,“笛克把空啤酒罐和盘子撤走”;她在屋子里四处捡起她丢下的烟头,似乎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在爱着一个女人。而偏偏他爱的女人不是为周围人做出奉献的那种类型,恰恰相反,她要为调整自身的存在而向周围一点点索取,因为她将这种索取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最后“笛克诺斯死了”,“星期天傍晚他去箱根一条街上买东西,当抱着自选商场的购物袋出门时,被卡车轧死了”。死得安静,死得平凡,死得如草芥。仿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也不想打扰到他人。而他爱的女人并未显示出读者期望的悲伤,她低声说“食品快没有了,他出去买,结果落得这样,所以……”她的弦外之音是指该买的食物没有买回来,家里还缺食物,与痛失爱人的悲痛无关。村上在这里仅仅用一句话便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极度可怕的冷漠。笛克诺斯死的无价值也即是说明他所象征的美好在当代社会中的无价值。所以他的死即是他象征之物的死。那个女人的冷漠,毫不在乎,并以游戏的玩赏看待生命及其死亡的过程,是对“性本恶”的一种助长。
有学者认为,人的心理结构除去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外,还存在了第四维,即“逆某”。所谓“逆某”,“即非我、反我、我的叛逆,是人格构成中的一般反向内驱力。”“自我是确定性,即我是谁;逆某是潜在性,即我不是什么”。这是一种矛盾性的产物,“它经常从自我中脱离出来,与自我形成对立并演变成反自我的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中受到攻击时,他首先采取的措
施就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当这种伤害的力量超出自己能抵抗的范畴时,他体内的“逆某”因素就会起作用,把自己变得不象自己。而是向反方向转化,来表现自己的反抗。但实际上,“没有人愿意成为非我,我们的一切行为其部分目的就是填补遮盖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虚空。”我们非常希望成为自我,但在压力下却不得不反方向行走,“感受到内心非我的狂乱”,觉得自己渺小卑微,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彻底变成另外一个自己,村上笔下也有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即是‘精神的死亡,这样的人物只是精神的一种象征,一个载体。人的死实质想提示的是一种精神的死。这也是后现代小说中最常表现出的“死亡”形式。
三、忠于死亡的死
我讨论的前两种情况中,死者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了生命。而本书中还有一种类型的死,即是忠于死亡的死。五反田的死可以归人这种类型。他死的极其简单,“‘玛莎拉蒂从芝浦海打捞上来是在翌日偏午时分”,此处的“玛莎蒂拉”是五反田的车名。在这里,虽然说五反田在寥寥数语中很快地、宁静地死去。但其实他的死并不是突然的,当他活着时,他的身体里就已经开始积聚死亡的因子,他的身体里包裹着死亡的核,不仅是当他死去时,而且是显然在他还活着时,他已经是在死亡的空间中完成了他的行为,他只是在找寻自己应该死亡的“不确定的时间”而已。也就是说,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死,然后他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他已经准备好随时死亡,但这个死亡时间处于哪一个点上,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读者也不知道,只知道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就应该死了,自然而然地就死了。书中也提到“他一直考虑把‘玛莎蒂拉投入大海,他知道那是自己唯一的出口,而始终将手放在那出口的门把手上等待时机。”他自己命中早已注定他该以这种方法死,“死亡”之神已为他安排好了路;然而事实上他也确实以这种方法死了,按照铺好的路走下去,没有发生意外,没有突然被剥夺什么。是在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后,自愿死的。对于他这种死亡,就是“忠于死亡的死”。
这种死亡形式一定程度地表现了生与死、人间与地狱的混淆、颠倒、错置。因为在他们身上,“生”的时候就已经孕育着“死”。生与死的界线在他们身上显示得很模糊,以致连当事人也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活的还是死的。文本中的“喜喜”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作者未曾告诉我们她到底是生是死,只是说她消失了,而且是借她自己之口道出的,“我并没有死,只是消失而已,消失。转移到另一个世界上,就像转乘到另一列并头行驶的电车上,这也就是所谓消失。懂吗?”而事实是,她会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显现,甚至对我说话。其实,很多现代作品中都会将生与死荒谬颠倒过来。其目的就是想表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死无异、死生纠葛、生即是死甚至是生不如死的观念。”是一种虚无的死亡形式。
而《舞舞舞》的深刻之处便在于,表现虚无的死亡并非它所停留的层面,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让人将自己从这空洞里连根拔起,让“自我”融入这个社会,这部小说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积极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与其它多数后现代小说所透露出来的苦闷失望、焦虑孤独的主题很不同。小说的题目《舞舞舞》便是取自于此,当“我”问羊男我该如何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时,他告诉“我”:“跳舞,不停地跳舞,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跳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逆某”的反抗,即对自身消极因素的反抗。而“战胜‘逆某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对抗与妥协。”如果采用对抗的形式来反抗逆某,就意味着与“雪”同一类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来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即“我蔑视大众”,“我是局外人”,实质上,大部分这种人并非成功地反抗了社会的虚无,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罢了,这种“与众不同”的建构“除了‘自我观看以外,同时也是希望‘被人观看。这类人只是在内心里进行反抗,而缺少实际性的反抗活动,这种与众不同的最终结果却与他们的最初愿望恰好相反,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地抛弃了社会,而是他们被社会抛弃了,退到了社会的边缘。自我依赖于自我,与社会其它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状态,这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口反而离死亡越来越近。而本书中所提倡的反抗方式其实是“妥协”,即克服“逆某”的真正方法就是压制“逆某”,把自己内在的“反抗”分子压抑在一定量变之内,永远不让它发生质变而导致自己为了减轻所受威胁的不安全感而做出离奇的举动。我们要逼着自己与社会“连接上”,对目标持之以恒,“跳得大家心悦诚服”。所以《舞舞舞》中的主人公“我”,虽然生活在锁闭的环境中,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同外界隔绝,当周围的人一个个死亡之时,我仍然……最初的“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被社会流放的人,“既无应干的后,又无想干的事”,而在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历程之后,自己才明白有束缚才有自由,“我”流放自己但不封闭自我,生活隐退但不隔离本性,内在的自我借助于对社会的参与而变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小说中那句“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正是主人公寻找自由的真正途径。
“现代主义小说家‘向内转,发现了一个破碎的自我,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发生断裂,而且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产生严重的干扰”,而在村上的《舞舞舞》中,积极的“自我”才是“自我”的应有之意。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找寻自我的历程中,“历经心理挫折和思想动荡之后,他至少已经理解到生活不仅是‘一个谜语,‘一场猜测,‘掷一下骰子,而且也是人的内心和智力无止境较力的现场,无止境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现场,是一种担当。”死亡是自己主动选择被社会遗弃,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村上春树是日本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他笔下的死亡从一定程度上说有超越普通的意味,与其它的作家有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村上春树在小说中一再重复的话语。他其实是想寻找所有这些死亡的源头。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