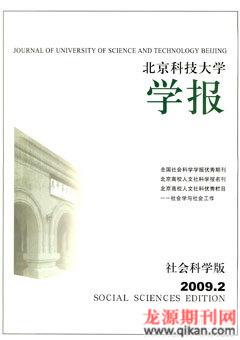妙语的语法根源
李 力
〔摘要〕语法根源是语言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概念。本文首先介绍Taylor[1]提出的语言的范畴化,然后以实证说明妙语类典型分布在不同的语言中,如英语和汉语妙语。分析英汉妙语的差异有助于揭示语法根源的本质特征,如在英语妙语中,在一定情境中要达到幽默会意应选择特定的语法结构、语法路向和语法构式;而在汉语妙语中,由于认知差异,在以上三个方面具有不同的语法根源。我们认为,娱悦产生的真正源泉不仅在于妙语体验者能够消解旧感知和新现实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妙语体验者能够依据其特有的体验来解释该语法根源。
〔关键词〕妙语;体验;语法根源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099-05
一、引言
不同的语言流派对语法根源有不同的解释,但谁也无法回避语法根源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法根源来自对世界的认识,而对世界的认识发端于范畴化。在人们对语法范畴的偏移校正和能产限定过程中,语言产生微妙的变化,妙语由此而生。妙语的语法根源似乎来自那些人们认为有趣、幽默的范畴。当说者认为好笑的范畴与听者也认为滑稽的范畴相吻合时,两者解释妙语时的语法根源应该是一致的。本文利用妙语的三个语法范畴观察其语法根源。这三个语法范畴分别为妙语的能产性、抽象性和对立性。抽象性融于对立性和能产性之中,对立性往往表现为对偏移度的把握。
(一)语法根源与英汉妙语中的语法范畴
1. 语法根源的概念
语法根源源自人类表述这个世界的经验,这个意义上的语法是一种意义潜势。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语法根源也是丰富多元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是通过区分不同事物而认识这个世界的,因而范畴化成为人们体验周围世界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语法的根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法根源的抽象定义是语法范畴化的过程。
2. 英汉妙语中的语法范畴
英语妙语如果用汉语表达,需要考虑两种语言的语法范畴差异,否则,将无法释解妙语的妙处所在。在语言的构式、定向、模式方面,妙语往往反映语言内在的表述习惯。这种表述习惯可能源自英语和汉语各自的语法范畴。妙语在汉语和英语表达上的不同可能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比如,汉语与英语在营造紧张气氛时的初始语法范例就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当潜信息中的妙语出现时,不同的听众在调整思路以理解对方妙语时就多了一个步骤。一方面,听众需要适应初始语法范例与摔包袱过程中语法范例的差别;另一方面,还要解决营造紧张气氛时初始语法范例可能存在的差异。英语与汉语妙语不存在完全一致的语法范畴。语法范畴在跨语言妙语表述中的对立性和能产性可能成为通过妙语探究语法根源形成原因的切入点。
(二)语法范畴的例示
语法范畴的例示主要有三个途径:时态、语法词和词序规约。在对语言范畴化过程的研究中,
Taylor[1](151)发现,过去时有三组意义:过去时间(对历史和小说叙述类文本的拓展)、反事实性和语用舒缓。跨语言显著的相似性足以提示我们,过去时属多义范畴,而妙语也具备多义范畴特征,如一个妙语会有妙语字面义、妙语言外义和妙语调侃义。Taylor[1](243)指出,我们对过去时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加以细化。过去时最早的例证是指刚刚发生的过去。只是到了后来儿童才将其意义扩展至更久远的过去。此外,过去时在儿童的词库中起初并没有应用到所有的动词之中。其早期的使用局限在某一类动词上,如fall、drop、slip、crash、break。这些词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指高度瞬时事件(punctual event),而且,这些事件涉及状态的明显改变,状态通常是越来越糟。可能涉及一个参与者①。只是到了后来,儿童才将过去时态扩展到表示非瞬时事件的动词和表示非视觉心理状态的动词,如see、watch、know等等。似乎过去时态的中心意义不仅仅指说话时的过去。中心意义更为独特,指“瞬时事件最近过去的完成,而且其后果在说话时可以被明显地觉察到。”而对妙语的理解过程也随着听者认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深入细化的过程,即由具体的幽默妙语意义到诗化妙语和哲理妙语过渡的过程。
由过去时态的范畴化演变得出两点结论:1、语法在语义表达上是通过词汇逐步向外拓展的;2、在不断抽象化的拓展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留下一些语法痕迹,如过去时态由某一类动词向另外一类动词的拓展。这些演变特征说明,语言的自然度应该遵循某一范畴向另外一个范畴的跨越过程。我们假设,这种跨越实现得越充分,语法原范畴的张力就越大。因此,在偏移度较高的语篇中,通过对妙语语言形式的观察可以发现语法根源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语言使用在不同情境下的对立性和能产性。
二、妙语中的对立性与能产性
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妙语表达,其语法根源的语篇表象、对立性与能产性也随之不同。通过对汉英时段的比较可以观察到相应语法的对立特征,这一点在妙语语篇表象中体现明显。国内学者[2](19-101)多从语义、语用和认知来对反讽话语中的矛盾进行研究,所依据的多为西方的语用学理论②。这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其研究方法往往过于理性,这有悖于中国式幽默返璞归真的研究[3](3-4)。
我们试图从语法范畴的视角来考察妙语中的对立性与能产性。有关类典型理论前人已有介绍[1](38-68),妙语中体现的反映语法类典型的句法结构,在结构模式上存在类典型效果[1](197-220)。我们从Taylor[1](200-201)对句法结构中形义相对独立关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妙语类典型的脉络。在Taylor[1](200)看来,结构即为意义与形式的配对。形式与意义均可以呈现类典型效果。一个结构可用来表达意义,该意义不同程度地与中心规范相左。同样,填补结构空缺项的项目与正式规格的类典型也有偏移。一个结构的产出性程度需要作为其表征的一部分加以陈述。我们认为,结构的产出性程度即为种种偏移的集合。其类典型允许的偏移方式以及偏移范围越丰富,产出性就越高。由此,我们引申得出,种种语法模式的根源可能是针对类典型的偏移,这也是探索语法根源的一条新路。
首先,从Taylor[1](200)给出的例子看,从纯句法的观点出发,“Is that a fact?”为“是非疑问句”的常规例示。然而,从语义上看,这句话却是相当边缘化的“是非疑问句” 例示。因为该句没有具体指明对极性的要求。该句几乎不能算作是问句,而是说话人吃惊的一种表达,“真的吗?”。从类典型具体指明角度无法完整地预测该表达的意义。与此同时,依据其自身特点,该句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该结构的公式规定特定的词汇项可能出现在结构空缺中。特定的词汇项包括动词需要的时态和名词的数。
Taylor[1](201)进一步指出,该结构应视为高度不能产,因为从中心具体指明的引申是极不可能的。比如,作为说话人吃惊的表达,人们不能说“*Are those facts?”,“*Were these facts?”。同样道理,“How do you do?”也无法扩展成“*How does she do?”或“*How do you all do?”。其它一些公式表达是具有能产性的,但范围限制极其严格。比如,表达感谢的种种手段有“Thanks”, “Thanks very much”, “Thanks a lot”, “Thanks a million”。有人可能为了表达极为热忱的感谢,说“Thanks a billion”。但插入其它数词就不可能了,比如,不能说 “*Thanks a hundred”, “*Thanks a thousand”。此外,Fillmore[11](63-67)用“day in day out”表达例示了另外一类低产出性的结构。在此结构中,允许在空位中插入其它的时间单位。可以推测,这些空位中所添词的指明通常能够感知到有单调性的时间段,如“week in week out”, “month in month out”, “year in year out”。不允许插入过长或过短的时间单位,如“*century in century out”, “*millennium in millennium out”, “*minute in minute out”, “*second in second out”。其原因在于,单调通常不是以分、秒来衡量的,在人类有限的生命期间,我们不可能体会到延续几个世纪乃至千年的单调。在这一方面,该结构体现了形式与语义特征的相对独立。如果某种语言将语法结构中的能产程度作幽默化处理,并且在该语言中予以认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据此追溯到该语言的语法根源。
从对以上例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语法根源与结构能产性限定级别有关。在第一条引申中,我们看到的是语法根源多样性的源头,即针对类典型的偏移。而在第二条引申中,我们看到的是语法根源的区别性特征。语法根源是在自由与受限这对对立统一体中得以呈现的。这样一来,语法根源似乎应为一个围绕类典型模式进行的动态作用过程。由印度-罗马至Chomsky的整个西方语法源于对粘连的原始表征,我们可以将此类语法比作对各个项目的连接。本文则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语法根源,即从偏移-限定能产性这个角度来探索语法根源。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摆脱原初的比喻,而将文本与自我结合起来,即读者或作者在应对情景变化过程中在语言表达上产生的偏移和解释该偏移的种种方式及范围都可作为语法根源的表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妙语中富含“偏移-限定能产性”语篇。
三、汉英妙语中的偏移与限定能产性
正是语言的能产性和非能产性的偏移使我们得以将妙语与语法根源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解读者对妙语作出了多样化的解读,由此作出不同的抽象,并形成相应的对立性特征。而相应语言的语法类典型往往由此而产生。街头标识妙语似乎能够体现相应语言群体的语法类典型特征,以及其中蕴涵着的相应语法的初始痕迹,即语法根源。其理据在于语法类典型差异可导致解释妙语过程的不同,并使妙语偏移与限定能产性成为追溯语法根源的一个手段。
(一)汉语妙语中的偏移与限定能产性
汉语妙语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情境冲突,这些都反映了语法范畴的偏移和限定能产性。以张玉国[12](1)的一段幽默为例:
日前外出旅游,首站由汕头至厦门。途经一加油站,旅客纷纷下车“减轻负担”。公厕设在一花园中,环境清幽宜人。从公厕出来,忽见门前有一指示牌,看后不禁厥倒。只见牌子上方,大书“公厕”二字;下面有一大箭头,并附一行小字:“内有园林式餐厅,欢迎旅游团体和个人前往小酙。”
在此处,尽管“公厕”与“园林式餐厅”在语法上等同,但在语义上却形成了一对对立体。通过抽象的跨范畴理解,牌子上的符号有了妙语的意境。这个妙语意境的产生是通过语法范畴的能产性来表达的,即读者对该语符的拓展。
从中国影视小品角度分析,姗子[13](34-35)认为,中式幽默最关键的地方是其犀利的语言。幽默类典型由关心小人物发展到了对人性和人欲的思考。中国喜剧大部分走的都是借助于方言的软幽默道路,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一种文化、国情、民意以及方言了解基础上的幽默。中国式幽默是与其政治文化观念和取向息息相关的,是这个民族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从上述中式幽默旅途奇观可见,高速公路休息处的指示牌透露出当今中国人人性和人欲的许多成分,在语篇上表达了现代普通中国人的诉求,对财富物质追求的极致可能会产生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但与此同时,也于细微处显现种种语法结构解读上的偏移。方
成[14](88)说“幽默”是出于人的智慧的逗笑。即“滑稽”只是可笑,而“幽默”是艺术,有美感,能令人笑过之后有所回味。看来,汉语妙语还较少涉及语法结构的能产性研究。这种现象说明汉语中还未有人就语法根源进行妙语语篇分析。而妙语作为一种话语活动是需要以语法为依托的。其语法根源在反映人类本性的最重要特征——幽默上得到最确切的体现。因而,中式幽默类典型的语法根源也可以通过如旅游奇观中的幽默事件得到解释。在中式幽默中,幽默者常以个体形式感悟幽默现象,撞击出奇妙情境的交际常发端于符号和幽默者心底的对话。因此,其语法根源常常是由景物及人的单向交流。
(二)英语妙语中的偏移与限定能产性
同样,英语妙语中也有许多令人尴尬的情境冲突,这些也反映其语法范畴的偏移和限定能产性。但在英语妙语中,其偏移的表现形式与听者解释模式的个性化倾向更密切相关,而其限定能产性更倾向于个体体验。Howe[15](252-254)认为,所有笑话都起始于紧张的构建,同时形成初始范式。在笑话的妙语处或令人忍俊不禁的瞬间,观察者体验到范式的转移,根据新信息的突然显现,对事件事实重新诠释[16](452)。其次,Howe[15]将笑话和幽默做了区分:来自紧张消除的笑话可以视为简单的本能反映,类似挠痒痒使人发笑。而幽默则更为复杂,它比简单的紧张的消除包含更多的社会交往内容。最后,Howe[15]介绍了心理解读假设。该假设拓展了幽默的公认理论,涵盖观察者和幽默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笑话起始部分建构紧张气氛时,幽默对象获得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他所感知到的事实。当妙语出现时,幽默对象必须重新调整他的思路,以适应初始范式和新信息突然显现的差异。幽默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即当我们在看到并且明白幽默对象发生改变时所作出的反映。娱乐的真正源泉来自我们的观察,即幽默对象在脑海中解决先前察觉到的情形和现实的冲突。幽默源自我们对有意识的大脑的欣赏,这个有意识的大脑被迫适应新的一套环境。即使是最基本的幽默形式——双关也是如此,没有接收用的锡箔装置,该双关将可能平淡无味,毫无生气。
美国式幽默可以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窥见一斑。马克·吐温曾经说过, “幽默的秘密源泉并不是欢乐而是悲哀。天堂里没有幽默。” [17](411)美国式幽默用意往往在于抒发生活中的无奈、反映人的生存境遇。在美国式幽默日常会话中也反映了美式幽默关注人生的主线,其表现形式涉及语法根源。Davies[18](1361)认为,交际往往发端于连续构建的笑话片段中,尽管是间接的,但通过在对方设计的框架中合作,展示相互的谅解。这种经过改进的互知是相互沟通的重要因素,能否参与这类笑话也因此成为该能力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来说,讲笑话是展示会话参与度的显著标记。因为能够在一起说笑话是双方关系建立并得以维系的重要方式。尽管笑话是语言和交互过程中看似普遍的一种人类现象,但它比大部分交际过程更明显地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18](1362)。从对美国人一则笑话的分析中,Davies[18](1364-1365)描绘了会话笑话在美国亚文化中的情况。故事发生在纽约市,Davies正在第五大街等候公共汽车,周围有一群人,其中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一时间引起了Davies的注意,因为她的穿着很得体,非常适合在早春时分在纽约市内旅行,穿得起码要比Davies强。而此刻,Davies的目光落在远处汽车站的一块牌子上。这是一块标准的长方形金属交通牌,安装在一块标准的标牌立柱上,上面写着“NO PARKING, NO STANDING, NO STOPPING, NO KIDDING”,这几个字由上到下平行排列着。当Davies解读这一“只有在纽约”才有的现象时,他的脸色一定经历了一番变化,由起初的惊异到好奇之色。虽然他本人未曾留意,可是却被旁人注意到了。此刻,Davies的目光转向官方贴出的纸牌上。纸牌是用胶布粘贴在柱子上的,恰好位于那块永久性标牌的下方。纸牌上写道,“NO PARKING ON SATURDAY”。正当Davies出神地体味这两个并置的标牌上令人不解的信息时,他听到一个老妇人操着一口纽约音道,“I wonder what they do on SAturday”,核重音强烈地落在“Saturday”的第一个音节上。Davies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他不得不停下来琢磨对方的问题。当他与矮小的老妇人目光相遇时,可能只是报以会心地一笑,或回上一句,“yeah, thats what Im wondering”,说这句话时调核应该落在“Im”上。很显然,老妇人一直都在注视着Davies。她留意到他在读那些标语牌和他的反应。当她看到Davies一脸困惑,似乎要琢磨出纽约官僚们的真正意图时,她应时地道出了他的心声,且其言语非常准确到位。她说这番话是以两块标牌的共有语篇情境为基础的,伴随有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老妇人对句法进行了巧妙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对标牌的荒谬解读上。即“周六,停车是被禁止的,而站立、停留和开玩笑则是允许的”。在这个句法情境中,重复了“no parking”这一句,还附加了“on Saturday”,她的话以“Saturday”这个词结尾,并且通过落在第一个音节上的调核重音,建立了一个具有鲜明对比差异的强调点。这个语义韵线索激发的对比建构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星期六与一周中的其它日子被区分开来。在星期六之外的这些日子里,站立、停留和开玩笑在此处也理应是被禁止的。此外,将两个否定句“no parking”和“no parking on Saturday”并置在一起,强化了“在星期六停车是被禁止的”这一想法。与此同时,也潜在地取消了对站立、停留和开玩笑的禁止,因为对这些行为的禁止没有得到重复。富有讽刺意味的嗓音,加上冷峻的表达方式,传达给Davies的是纽约人的厌世情绪,而Davies庆幸自己也有同感,并深陷其中。这里,双方都对自己两难的生存境遇表示同情,任凭卡夫卡式的城市官僚们摆布。通过以如此艺术化的方式打断Davies的思路,老妇人实质上是在“窥探Davies的思想”,道出了Davies的所想,展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认知形式的神通。老妇人话语中语用上的微妙之处给Davies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解释:将其视为自己的想法,就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当成自己想法的准确再现;当作一个问题,并对其作答;回避,假装没听到她的话或当做不是对自己说的话。因而,老妇人话语中对句子形式的选择同样是对我们所处社会语境的细致回应。老妇人的话是个陈述句(I wonder what they do on Saturday),实际上是在间接地传达问题。这种约定俗成的间接性提问,使听话者可以选择不作回答,但同时也在听者脑海中建立起对某种回应的期待,这一点与直接问句一致。
尽管语法根源可以通过听者以语用和认知的形式在句法等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但笑话涉及的当事人对笑话的设计和解读在偏移程度和能产限定性方面则存在更多的语法范畴跨越等不确定因素。如果从Davies[18](1366)的回应分析,抱之一笑,或说一声,“yeah, thats what Im wondering”,紧扣发话人的语言特征。Davies使用了同一个动词(wonder),在语言上与前面的话相联。因而,将起始者话语中的主要小句“what they do on Saturday”通过代词“that”和“what”联系在一起。从话语的语用结构来看,Davies通过小句分裂结构,将指称起始部分的先前话语置于“话题”位置,由此暗示此处的共有知识为先前的话语,Davies加入的是一个“评论”(额外的信息)。
四、结论
透过妙语可以观察到许多语法根源的表象,特定的妙语需要相应的语法与之匹配才能产生一定的幽默效果。妙语因处于不同文化背景而可能具有不同的语法根源。幽默的范畴属于消遣娱乐,是文本最原始的形态,因而能够更深入地体现人性。本文承认妙语中个体区分特征,且在原始的形态中,该区分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妙语的能产性特征可以追溯到类典型语法根源形态。原始形态文本差异体现原始形态语法,该语法折射出该种语言使用者的偏移性经验,这种经验又反过来影响使用者妙语的能产性。语法根源在当事人对各自所处妙语环境的调整、处理和反映中得以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选用语法模式时会以原始形态为出发点。探究妙语的语法根源有助于我们观察各个语言社团的人是如何通过不同语法范畴的协商进行有效沟通的。
〔参考文献〕
[1]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9/ 1995/ 2001.
[2]文旭. 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林语堂. 幽默人生[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Grice, H.P. Meaning[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LX(VI): 377-388.
[5]Grice, H.P. Utterers meaning and intentions[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9: 78, 147-177.
[6]Grice, H.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Cole, P. & Morgan, J. L.(eds.) Syntax and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5: 113-128.
[7]Grice, H.P.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Cole, P.(ed.) Syntax and Semantics 9: Pragmatic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113-128.
[8]Grice, H.P. Presupposition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A]. In Cole, P. (ed.)Radical Pragmatic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183-98.
[9]Brown, P. and Levinson, S.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politeness phenomena [A]. In Goody, E.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78: 56-310.
[10]Sperber, D. & Wilson, D. Mutual knowledge and relevance in the theory of comprehension [A]. In Smith, N. V. (ed.)Mutual Knowledge [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2: 61-131.
[11]Fillmore, C.J. Innocence: A second idealization for linguistics [J]. BLS, 1979 (5):63-67.
[12]张玉国. 旅途奇观 [J]. 咬文嚼字,2003(10):1.
[13]姗子. 中式幽默 [J]. 西部广播电视, 2007(5):34-35.
[14]石破. 和谐社会的幽默问题 [J]. 南风窗, 2007(3):88.
[15]Howe, N.E. The origin of humor [J]. Medical Hypotheses, 2002,59 (3): 252-254.
[16]Spencer, H. The physiology of laughter[A].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 Vol II [C]. New York: Appleton, 1910.
[17]Twain, M. A horse tale [OL]. (2007-09-11) [2008-11-30]. http://www.pagebypagebooks.com/Mark_Twain/A_Horses_Tale.
[18]Davies, Evans, Catherine. How English-learners joke with native speakers: a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humor as collaborative discourse across cultur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1361-1385.
(责任编辑: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