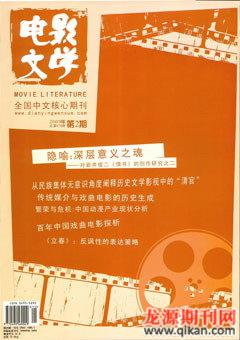缺损的“他者”:徐静蕾电影中的女性
骆 鹏
[摘要]《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徐静蕾拍摄的这两部电影都是女性题材的影片,并且都是以影像的主角存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垄断镜像的传统,但是,尽管徐静蕾是一位女性导演,并且这两部电影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独白来推进情节的发展,但其塑造的并不是真实的、完整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形象仍然是缺损的。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形象,缺损;他者;非独立
在主流影视中,女性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影视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被摄像机背后的男性导演凝视,被剧中的男性角色凝视,被男性观众凝视,在三重凝视之下,女性被改写成男性世界中的欲望符号,依据男性世界的法则来生存。在男权制度下,女性甚至称不上“第二性”,只能以“非男性”的形式存在。在男性主导的影视文化机制内,理想的男人是期待视野的核心,而女人则无关紧要。但女人或多或少必须出现,因为她们的存在印证着男人的强势。
一、陌生女人——镜像主角中的“他者”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他者”一定是来定义女性的。
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从女性主义的立场这样理解“他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长期以来,男性把自己界定为主体,女性便成为他者。女性形象虽然在影片中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却还是接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析与解读。在“他者”言下,女性形象体现在电影中,常常处于沉默无语状态或者根本没有话语的权利。她们躲在男性的背后,阉割了自己的话语。在“他者”的观照下,电影中的一些女主人公总是些聪慧、早熟、敏感的女孩,因为家庭的破碎或者家庭的不和谐,过早体会到了安全感与被爱感的缺失,她们在对父权的颠覆中交织了对父亲的依恋,而在寻找中又掺杂着失落感。女性导演试图以女性的语言建构女性形象,建立起“女性话语”。女性话语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体现“颠覆”与“寻找”的主题。因此,在女性导演的影片中,试图以“自我”的话语去建构女性形象,很多时候却在颠覆中又不自觉地陷入到“他者”的语言——“寻找父亲(传统)”的过程。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以女性主人公的讲述带着作家进入到她的故事之中。幼时缺少父爱的女孩爱上了一位风流倜傥的男作家,女孩甚至是痴迷于作家。在这场疯狂的只有她一个人的爱情中,作家更像是“父亲”的角色,填补了父亲的缺席。而她依然没有逃出对于男性的依赖,始终作为“他者”在寻找着“父亲”。表面上,她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但是她的生活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男性:男作家是她考上北师大的动力,是促成她抗衡世俗舆论,独自抚养私生子的勇气。她的一切行为都指向那个男人。由此不难看出,她在拼命颠覆父权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于它生存下去,她依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当儿子病逝之后,这种依赖再没有一种纽带来维持,于是她也随儿子而去了。从这种意识上来说,在陌生女人身上所反映出的女性形象是缺损的,她被巨大的男性阴影所笼罩。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获得与作家的联系,哪怕作家并不知情,一旦这个联系失去了,她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影片中,陌生女人虽然占有“话语言说”的权利,可是,极端的“话语”的展现反而凸显了对于“自我话语”的自卑,看似属于“女性自我话语”的背后还隐藏着对于“他者”语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徐静蕾塑造的女性形象,在要求“自我”话语同时,她又是以“他者”话语来建构自己的话语。她在逃离一种男性话语的时候,又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男性话语之中,从而始终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
徐静蕾以一种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自身与外在世界的成长经验,这种努力在其作品里,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从强调女性自身经验、想象和欲望出发,在电影创作中创造了一种极端强调个人化的生存感觉和女性的独特品质的语言方式,并以此种姿势重新对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确认和定义,以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徐静蕾将陌生女人的爱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上看,电影似乎通篇渗透了女性意识: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享受我自己的过程。至于得到得不到,至于男性的反应怎么样,跟我个人爱的过程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是这样,既然就是一个女人自我完成的过程,那么这个男人哪怕就是一个石柱好像也可以完成了。由此看出,她虽然有了女性意识表白的欲望,但仍停留在自我展示的阶段,她还没有重塑自我的自觉和勇气。因此,在徐静蕾影片中的陌生女人不过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被女性接受后,又通过女性反映出来,兼带上了中国传统的含蓄色彩与伦理思想烙印而已。显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非理性的自虐式爱情无疑是威胁到当代女性独立的自我价值与自尊的,是不能真实反映现实中的女性形象的,她依然是缺损的“他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女人像教徒一样对她爱的偶像的崇拜,是靠精神力量给自己树立一个“虚构神”,并通过单方面的牺牲和奉献——事实上的自虐——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解脱与升华。然而圣徒即使通过自我牺牲,也永远不会和神平起平坐,女人也同样永远不能通过牺牲和自虐而成为和男性地位相同的物种。相反,这种牺牲恰巧证明了她的从属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在男权话语的氛围内女性始终是被窥视的,女性始终都没摆脱“被观看者”的地位。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常常被异化成为两个对立的极端——不是“天使”,就是“女巫”。尼采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这是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身份的深刻体认和自觉承担。显然,陌生女人是属于“天使”的。尤其电影结尾中玻璃窗上幻化出的女主人公少女时代的面庞,纯净、不染纤尘——那分明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影片实际上是按照这种社会已经形成刻板印象在雕刻着男性所希望的女性形象,因此即使是女性导演的镜头依然避免不了陷入男性话语之中,使女性形象始终处于一个“被观看的他者”地位。
二、小鱼——恋父情结下的非独立个性
《我和爸爸》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段父女深情,它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记录了点点滴滴的感动。由于母亲的意外离去,小鱼回到她的亲生父亲老鱼身边,从陌生到熟悉,在非一般的另类父女情中,从不解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谅解。在共同生活的几年中,两人都感受到一种爱和一种人生的无奈。那种爱是无条件的,那种责任也是无法解除的。两代人情感的回归,跨越代沟的人生之旅,蕴藏着人生多少酸甜苦辣。正是这种爱与责任构成了小鱼和老鱼生活的全部痛苦和幸福。
影片在父女关系的阐释中,单身的父亲与独生的女儿,仿佛是另一种意义的夫妻或情人,形成一个完整家庭必不可缺的“男女关系”。情节的设置将女儿与父亲从一开始就置于既对立又依赖的微妙关系中。少女小鱼在故事的开始就遭遇了丧母的痛苦,此后,早年抛妻弃女、吊儿郎当、到处鬼混的父亲来和她一起生活。然而奇怪的是父亲似乎从
一开始就赢得了女儿的爱。“父亲”这一符号在小鱼的生活中一出场,母亲就死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的迷恋其实是她获得自我主体身份确认的过程,为此她强烈要取代母亲的地位。从这种意识上说,她是渴望独立的。
故事从一开始小鱼与父亲的关系就似乎抛弃了母亲的存在,两人的对白与其说是父女,不如说更像情侣在调情。进而我们还发现,“父亲”甚至影响了小鱼的“性”的世界。在她的青春期,她没有男友,甚至看不上任何同龄的男生,惟一的男友是在父亲入狱后出现的那个诗人。从小鱼和父亲就男友问题的争吵对白中不难看出小鱼与诗人相恋的原因:“我需要他在的时候他都在”,而“这个时候你在哪里”?这句质问父亲的台词则充分暴露出她对父亲的依恋,而诗人只是父亲暂时不在身边的一个替代品。接着,她结婚,出走,怀孕离异后回家,得到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带着孩子重新开始和父亲生活,并抚养孩子,“父女”二人的暧昧关系在这个段落里凸显出来。此后,父亲去世了,小鱼的生活中再次消失了男性,于是。她又一次选择了结婚。
作为女儿来讲,小鱼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毫无疑问深深爱着自己的父亲。父亲中风,只有女儿静静地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女儿对父亲的情谊在这样平静而温馨的生活中,宛如一丝清泉缓缓流淌。在这样一个只有父亲和女儿的家庭里,小鱼的生活不需要别的男人,只要她的父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电影并非描写一般的父女亲情,因为影片中根本没有描写徐父,因此我们不能把真实的徐父拿来比较。而徐静蕾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说:“这部电影能不能赚钱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让我自己满意,因为它是拍给我自己的。”影片似乎想要跳出固有的亲情和情感思维模式,但是始终还是没有摆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命运。小鱼在父亲离开自己以后,再一次选择了结婚,从父女情结中再次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生活本身。但是小鱼的依赖性却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依赖于一个男权社会构建起的保护伞。
事实上,小鱼自始至终都没能真正的实现个性独立。母亲在世的时候她与母亲相互依赖;母亲去世了,父亲走进她的生活,于是她开始依赖父亲,在父亲入狱的日子她依赖于男友,离异之后她又重新依赖父亲而生活;当父亲去世之后她又选择了再婚。而在影片结尾她选择再婚则预示着,在她以后的生活中,这个再婚的男人将代替父亲的位置,让她重新获得生活与精神上的依赖。在这种情境下,她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个性独立。
三、形象缺损的背后
在徐静蕾的电影中不论是陌生女人还是小鱼,她们的形象无一例外地被边缘化了,是缺损的、不完整的。小鱼和陌生女人这两个女性导演精心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依旧逃脱不了男性的视角与体验,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得她们成为被男性观看的角色、围绕着男性意识而被塑造。她们试图逃脱现实给予自己的命运,可是总是不自觉地陷入了反被现实愚弄。女性在男性社会中“注定是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即被责难、被琐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现”。
徐静蕾在电影创作中一直在试图解构男权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却在不自觉中解构了自己对男权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的解构。在这两部电影中,徐静蕾试图塑造出两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但是,最终她并没有成功。
陌生女人对作家炽烈而无望的单恋得到了极大地强调,导演的意图是为了表明“我爱你,与你无关”这样一个女性在爱情上占据主动地位的观念。但影片里的女主角的地位却始终是被动的,因为害怕遭到他的拒绝,她不说出自己是谁。她在信中说:“我不愿變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念。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所有取舍还是由男人的喜好来决定。作家想起她的时候心中只有爱情,没有怀疑和阴影,这就是她的追求。她默默地牺牲和奉献一切,她的自我是如此虚弱,实现自我的途径又是如此狭窄,她到死都只是在乞求她精神寄托的对象相信和承认自己的存在。这是自我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
《我和爸爸》中,在小鱼和父亲为男友的问题争吵时,小鱼曾说;“是,他没钱,挺穷的,人也长得一般,可是他对我好,我需要他在的时候他都在。”而“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她质问父亲。因为父亲不在场,所以小鱼把她对父亲的依恋和需要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身上,男友只是作为一个替代品而存在。从一开始,她就不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她的每一步成长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离开过父亲。
徐静蕾要塑造独立的、坚强的、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至此已经完全的处在了被动、被观看的他者地位。她本意原非如此,但是却在无意中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使她陷入了这种失语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