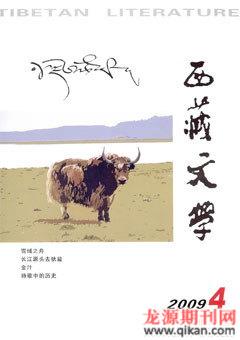精神张扬的历史影像
徐 燕
文化人类学家格勒在为马丽华的散文集《西行阿里》所作的序中描述他们在西藏科加村的所见所感:“当我们在科加村调查了解短短三十多年前这里存在的欧洲中世纪式的传统社会制度时,村里仅有少数人对此犹有记忆。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对此已经淡漠。不少人甚至不知封建农奴制为何物。”为此格勒预言:“再过一百年后,凡对阿里的过去感兴趣的后辈们是否也会责怪我们为什么不多出几本像《西行阿里》这样的书呢?很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人们怀着开垦处女地的兴奋和记录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文化之喜悦进入千里之外的阿里,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王寿民先生于1956年进藏,长期从事地质工作,特殊行业的流动性质使得他的西藏记忆别具一格,作为西藏民主改革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亲历者,他的老西藏系列纪实散文拂去了历史的尘封,将那些业已远去的半个世纪前后真实的老西藏生活图景呈现于喧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人面前,这同样既是一种文学创作,也是一位亲历历史的记录者。
一
马拉美说,涛歌是舞蹈,散文是散步。散文的撰写是以自我为中心,将可感可思的生活素材平稳妥帖、行云流水般地组织起来,营造出个人化的情境,彰显自我的个性。王寿民的老西藏散文沉潜在历史的洪流中,撷取了在历史中隐没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民主改革初期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仅是一个逐渐远去的时代交响曲在现代化变奏中的呼应遥响,电是那一代人曾经付出鲜血汗水与理想激情的精冲家园的寄托,这些混合了作者青春与困惑、欢乐与苦难的心灵奏鸣曲,将今天与过去。近处与远方结合在一起,在对半个世纪前的超时距观照中,合并成一个涤净了冷漠污浊,积聚了对于理想张扬的个体人生来说富于启示性永恒性的精神能量。从此层面上来说,这一类怀旧纪实散文既是作家个人青春的纪念,也是那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代群体的缅怀,还是今日挣脱精神缧绁重拾理想的精神返回。它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它是过去的,也是今天与未来的。
《难忘班戈湖》记录了五十年前班戈湖地质队进藏的历史,组成地质队的成员来源各有不同,有从浴血奋战的朝鲜战场默默返回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共和国‘最可爱的人,没有来得及脱掉血染的军装,也无法洗掉身上的征尘,更别说同亲人见上一面,就又开赴了新的战场”;有尚未真正完成学业的应届大学生,“在这天气极度寒冷,敌情特别严重的1958年的冬天,北京地质学院根据上级指示,挑选优秀学生提前毕业前来加强硼矿勘察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有年轻而专业精通的女性技术负责人,“一开始野外施工,老范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工地上。我眼里的范敏中,什么时候都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老范就是人们心中的‘花木兰”……,从各个方向汇合而来的精英或以祖国的需要为己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召唤,或为实现高远的理想而自动请缨,崇高的集体主义感与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宏阔抱负,激励着那一时代的人们投入辉煌炫目的理想激流,锤炼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西藏,刚刚经历民主改革,西藏人民从半封建半奴隶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生活秩序有所好转,但物质生活依然匮乏,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回想那时的情况,五十年前的那些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心里感到阵阵作痛”,所有参加这一历史变革的建设者们面l临的几乎是一个需要白手起家的建设对象,但与物质需求极其匮乏和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相对应,此时建设者们创建新社会的精神理想极度张扬,精神信念与人生理想在苦难生活的砥砺中尽情燃烧,人生价值在与艰难的个人生存的对抗中熠熠生辉,青春的壮丽在生命的极限挑战下得到确征。
好些年之后,我从一本书上看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人要学会超越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进入精神领域,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我觉得,那时候班戈湖的地质队员们,并非人人都看到了雅斯贝尔的书,更没有哪个人来教会他们“学会超越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但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却都是这样做了。1959年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在班戈三湖那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和困难面前,地质队员们的“最大价值”就是当时班戈湖硼砂厂人人皆知的那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又极具特定政治意义的话:“保卫马列主义”。还有那首“勘探队员之歌”:“……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难忘班戈湖》)
这是作者过滤了世俗人生的渣滓,代表曾经经历过的信仰坚定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书写的饱满的人生体验,在耗尽肉身生存的平凡人生的历程中涤静人们的心灵。寄寓了无尽的生命启示。
二
作者在散文中寻求支撑人们抵御外在生存环境恶劣的力量中,不仅有理想与激情的信念张扬,也有散发脉脉温情的人性光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如此描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当人们又重新拾起旧日的宗教和局部的及地方的旧有的民族风格时,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日的歌儿,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了人心。
王寿民的老西藏散文中,曾经辛苦艰难的现实表象经过时空的过滤,在个人情境的营造中,沉淀出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自由豪放、健旺厚道的人性结晶,这种人情之美氤氲在特有的西藏风情之中,散发出超越世俗的温馨淳朴的光彩。
驮队出发前,阿妈东江专门捎口信让妻一定要将那张狗熊皮垫到我的马背套里面,说:“这一去两个多月,一路上都要在冰冻的野外睡觉,身下凉了最容易得病。”等我来到格尔滩,她也已经将我需要的糌粑、奶渣、酥油、一腿牛肉和一些风干肉、茶叶全都准备好了。……阿妈除了给我准备的食牖之外,又另外用口袋给我装了两块“腿”(用酥油。奶渣混合揉制成的食品)、几块肉、一大坨酥油、一块茶叶和一小包盐巴。我说:“我的食品刚才都装好了,又带这么多,哪里吃得完?”阿妈笑着说:“……你是个‘波沙(第一次参加驮盐的人),按照规矩,你就要清全驮队的人吃一顿饭。这些东西就是为请客准备的。”
(《长江源头去驼盐》)
在物质极其匮乏的藏北高原,藏族阿妈东江一心一意地为一位汉族年青人准备驼盐远行的一应物品,宛若对待自己的亲人,这种道德的淳厚、人情的温馨在作者平实质朴的陈述中,浮现出压抑不住的对古老美好的传统人情的热情赞誉,“我想,湘江之水哺育我长大成人,现在,我又在藏北高原有了个爱我的母亲。三十九族故事的发源地——格儿滩,真正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在德庆县马区进行余粮征购任务时,住在阿爸益西家,宽厚仁慈的老夫妇将作者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疼爱,
老两口素朴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方式让作者不由地感叹“我十八岁只身来到西藏。今天又有了一个爱我的好妈妈!”
(《仲吉林卡学藏文》)
在那个物质环境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年代里,作者描述艰苦的生存空间的背后,凸显的是压抑不住的情感怀恋倾向,那既是对自己火热青春的一种缅怀,也是对已经飘逝而过的时代记忆中美好人伦的追索。文章的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仁厚之情比比皆是:地质队年底探亲,干部们布置一线人员回乡返乡,自己留下作为预备队员顶工,而一线人员感动之余毅然留下来接受新任务的挑战;(《难忘班戈湖》)在那个阶级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作者因出身不佳屡遭白眼,地质局办公室唐主任却毫无疑虑地将左轮手枪交付作者使用。(《仲吉林卡学藏义》)散文中流露出的充满作家个人情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经过悠远的时空浸润,抛弃了物质层而的重负,氟氲出强烈的对人伦温馨、道德淳厚的心理追寻轨迹。
三
新时期的西藏散文在几代人的努力耕耘下已经蔚为大观,随着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传统文化资源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关于西藏的各类散文以其独特的风姿也同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使得西藏文学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当中颇有独领风骚之势。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必然是因为它引起心灵的震撼共鸣或陌生化的新奇感,而由雪域高原的自然景观与神山圣湖的民族文化形成的独特的冲击力恰恰具备上述因素,由此吸引了众多的写作主体及其大量的写作受体的关注。
王寿民的老西藏散文选取的距今已达半个世纪的民主改革初期西藏建设、生存图景,显然与今人描写西藏的散文大异其趣,其中独特的时代烙印与某些浓郁的西藏文化随着现代化格局的确立已然远去,这也许是一位老地质工作者的散文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所在。去长江源头驮盐、在班戈湖勘测硼矿的艰难历险、在巴青与区长打獐子岩羊、与土匪的不期而遇的交火、在堆龙德庆县马区自然村的“四同一通”生活以及进行余粮征购任务的经历,无不刻有半个世纪前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时代印迹。作者亲身参与的藏北驮盐经历,在精制碘盐通行的当下,恐怕即将变成历史遗迹,他在文中以生动形象可感可触的文学性语言记述的“盐语”、驼盐禁忌以及采盐仪式,不仅仅是文学层面上的一种猎奇,也是一种西藏文化层面的展示,作者在文中也认为“上面的这个小小‘不同(指采盐新手的祈祷),也表明了,藏北高原即将消失的驮盐现象,应该算是一种‘非物质遗产,似有进行研究的必要。”在零下三四十度透寒彻骨的海拔4500米的班戈湖上用手摇钻探机勘测,如若不是曾经亲身参与者将之撰写成文,谁还能够体会到当年建设者们那经历过的不可思议的艰难困境。
那时“冬至”刚过不久,下午四点钟到机场接好班,太阳已经西斜,一点点热气也没有。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月亮。七点钟天就完全黑了下来。站在三湖那寒冷彻骨的冰面上,一股股寒气立刻像千百条冷蛇透过厚厚的胶皮底棉:亡作鞋,直往人们双脚心里钻,要不了多久,人们只觉得浑身冰凉,筋骨僵硬,血脉也好像马上就要凝固了。但是这一站就是八个小时……等到十二点下班,急忙爬上敞蓬汽车,一路上顶着寒风往回走,脸上像有无数把细细的刀子在划拉,那老羊皮大农改成的工作服,也变成了又冷又重的铁块,脚上套着的那两只厚厚的胶皮底棉鞋里也像是装满了冰渣渣。回到住地,人差不多成了冰棍,浑身冻僵了,连汽车也下不来了。马马虎虎急急忙忙再往肚子里“塞”点东西,钻进冰凉冰凉的被子。几个小时连双脚都暖不过来……
(《难忘班戈湖》)
这些曾经积淀在一代人脑海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已然悄悄流逝,或许将被后人淡忘。那是一段物质极度匮乏而自然环境极其清朝的岁月,那是一个在信念的支撑下不惜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的激情澎湃的时代,作者以亲所者的身份记录那个在时代突转的背景下一步步前行的现实生活轨迹,这既是一次对过往时代影像的回放、也是一次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精神折返,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返回往往是要在流逝的岁月中寻求能够照耀当前人类精神的光源,“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举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激情、理想、信仰、传统人伦,民族风情……,在作者精心撷取的于今已然陌生的往事会顾中,合奏出与当下性现代性有所变异的令人慨叹、有所感触的精神复调。
或许是作者过于追求对散文民族独特性的展示所致,文中藏文用语的呈现频率偏多,在藏语与用括号进行汉语翻译的反复叠现中,阅读有种不太流畅之感,毕竟,作为以“散步”为特色的散文,讲求的是一种行云流水式的接受顺畅感,在文本阅读的过多停顿中,那种接受的酣畅淋漓感或许会有所折扣。
然而毋庸置疑,王寿民的老西藏散文以其亲历历史的独特性为媒质引人开卷,文中对民主改革初期的物质生产、精神追求、民族风情等多层次的展示,投射出特有时代雪域高原的光与影,所呈现的审美形态的多层次性,对应了现实生活中读者的多重冀求,在以展示个人空间为主导的当代散文中,这种以展现往昔时代群体记忆为特色的个人抒写,让永不衰颓的理想激情在今与昔的时光隧道中不停地穿梭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