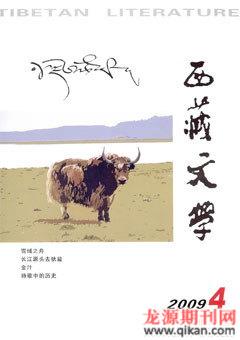牧人的爱情
梅 尔
牧人的爱情朴实而坚韧,在浮躁又多梦的都市人眼里,他们的爱情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青草味和浓浓的奶香。
牧人在空旷的草原上放牧着牛羊,也放牧着自己的爱情,于是草原上便有了一个个古老而年轻的爱情传说。
一
强巴常常坐在冬日的阳光中回忆,回忆年轻时候在牧场上与姑娘们追逐嬉戏的情景,那时候的强巴英俊健壮,骄傲中透露着霸道的自信。他正在追求草原上最迷人的姑娘——杨木措。杨木措不仅有着花朵一样的面容,还有着百灵鸟一样的歌喉。草原上的每一次盛会都有她们年轻而矫健的身影,她们唱歌、她们跳舞,她们甩着响鞭打马在草原上飞奔,释放着年轻而古老的热情……。
往事如烟,如今的她们都已经走进了垂暮之年,杨木措一叠连声的咳嗽早已掩盖了她年轻时候那迷人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满脸的皱纹写满了几十年的艰难和沧桑。强巴一边拍打着女人的背一边扭头朝门外望,正巧护士小李端着药盘从门口走过,她下意识地瞅了一眼病房,发现杨木措又在阵咳,无奈地摇了下头朝里面的病房走去。
护士又换班了,值夜班的人已经接班了,她们接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药,同时也进行夜班查房。强巴已经摸索出了他们交接班的规律,并且也摸索出了几个护士上班的次序,在值夜班的几个护士中,他最喜欢的还是小李这个丫头,整天乐呵呵地没一点忧愁,不像有些护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谁欠了她的一样。
强巴的女人又在咳嗽,一声紧跟一声,好像后面被人追赶着一样。强巴不轻不重地拍打着他老婆的后背,很无奈地听着这一声声的咳嗽,没有一丝惊慌。几十年来强巴一直用这种方式安慰和缓解着老婆的咳嗽。
女人得了个难缠的病,经常不停地咳嗽,咳出一团团的浓痰后方才舒服那么一点点,当痰咳不出来时,她的嗓子里就会发生像鸡鸣一样的声音,“咯——咯——”的。每当这时强巴的心就像是被人撕裂着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和难受,他甚至能听到被撕裂的那种疼痛的声音,于是就忍不住想起那个古老的刑法——千刀万剐,他觉得他早已被千刀万剐了几百遍,并且以后还将继续被千刀万剐。
他们是这个医院的老病号了,科里的大夫护士都非常熟悉他们,在办住院手续时,护士只问了他们两三项内容就把杨木措的资料填好了,然后很熟练又很习惯地将他们安顿在了这个并不宽敞但很安静的小病房里。他们知道,这是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习俗。
女人咳了一阵后停了下来,看着强巴喘着粗气,强巴明白女人的意思忙打开床头柜撕了块纸递给女人,女人将痰吐出后把纸扔进了床底下的痰盂里,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脸上出现了少有的轻松和舒畅。强巴急忙扶女人依被子躺了下来,然后将一杯半温的水递给她。
女人叫杨木措,是强巴服侍了几十年的老伴。此时的她并不急着喝水,而是双手端着水很感激地看了一眼强巴,然后才慢慢抿了一口。几十年了,强巴已经能完全读懂女人的眼神了,并且根据她的眼神能正确无误地判断出她的需求。他习惯于老婆的咳嗽和咳嗽后的需求,并对这个习惯总是持着无怨无悔的态度。
冬日的暮霭匆匆来临,顷刻间便笼罩了杨木措半躺的那张病床,也笼罩了整个病房。病区里昏黄的灯光此时不得不陆陆续续亮起。照顾完女人咳嗽后的强巴提起暖瓶去水房打水,这是这个冬天里他每日必做的事情。三十年了,足足有三十年了,对于强巴来说,好多个冬日的傍晚都是这样度过的:拍着老婆的背听着她的咳嗽声,看着年轻而美丽的护士从门口走过。有一天他忽然感觉到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他想他应该换个冬天的生活方式了,可换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怎么换?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护士走进来,将药片放在床头柜上,简单询问了一下杨木措的病情后扭着腰肢走了,他看了看那些药片后提暖瓶倒水。他的女人杨木措看着那满满一小盒的药片摇了摇头,很习惯地露出了非常为难的表情。吃药是杨木措每天必做的功课,而期盼药物尽快发挥作用却成了强巴每天最强烈的愿望。
这是第几次住进医院的内科病房了?在高原草丛中放牧了几十年牛羊的强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这里的好几个护士曾经还是小姑娘,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小媳妇。
这是坐落在高原草地上的一家企业医院,来这个医院就诊的病人并不多,自从强巴带着他的女人住进这个医院,这个并不宽敞的小病房就似乎成了他们的专用病房,接诊护士每次都会把他们安置在这个病床上。
强巴很熟练地伺候着自己的女人服下药物后有点沮丧地看了看逐渐落下去的晚霞。在强巴看来,这样的晚霞已经不美了,它只发给他一个信息,那就是一天又过去了,女人的病还是没有起色,生活的烦恼依然没有改变。于是强巴开始厌恶冬日的黄昏和黄昏中妩媚妖娆的晚霞。
二
强巴和他的女人是十多年前走进这个医院的,而在这之前强巴一直带着他的女人到省城去治病。在强巴看来,他女人得的这个病是个很难缠的病,方圆几十里的牧场上还没有人得这个病。牧场附近那个三代单传的小医生对这个病简直可以说是无从下手,认为只有省城那样的太医院才能治疗这种病。就介绍他们到省城医院去治病。强巴理解医生的难处,就毫不犹豫地带着女人去了省城。从那时候起他的生活轨迹似乎被固定了下来:每年秋天,他总要挑选一大批膘肥体壮的牛羊卖掉,然后赶着剩下的那些老弱病残或者怀孕的母羊返回他们的冬窝子,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而这时候杨木措嗓子里那个“咯——咯”的鸡鸣声就会开始响起,脸色也由原来的紫红色变得铁青。好像那只小鸡知道强巴的口袋鼓起来了一样。看自己的女人那么难受,强巴不得不带着她到省城去治病。强巴怀疑杨木措的嗓子里真的养了那么一只冬醒夏眠的小鸡,而这只小鸡似乎是专门来吃他这一年心血的。
牧场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牛羊也养成了好几茬,可强巴的日子却似乎没有多大改变。每个冬天强巴唯一的选择就是带着杨木措去省城治病,而把那个一贫如洗的家撂给那一对逐渐长大的儿女和亲戚朋友。他不想他的女人早死,也不想西北风夹杂着女人的“咯——咯——”声响彻他的整个冬天。好在强巴的怀里揣着卖羊得来的几千元钱。而在这之前他早已经计划好了这几千元钱的用处:冬窝子的房子得翻新,牛羊的简易草棚得翻新,得买个新式的大烤箱,还想准备点煤炭,据说煤炭取暖比牛羊粪取暖要省事的多。可这一切在杨木措“咯——咯——”的喘息声中统统化为了泡影,他不得不像往年一样过这个冬天。
求医的路很漫长,在省城的那些冬天过得就更漫长。他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想起那一个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在强巴看来,省城的什么都好,就是钱太不经花。那可是卖掉了三十只肥羊才筹起来的血汗钱,自己整整一个夏天的劳动成果,现在却换成一瓶瓶的药水流进了杨木措的身体里,去处理杨木措嗓子里那只“咯——咯——”叫唤的小鸡去了。强巴一想到这些就想喝酒,可大夫不容许他喝
酒,说这是在医院里,一个牧人喝得醉醺醺的像什么?你以为这是在你们草原上?大夫是个小青年,估计年龄跟他的儿子一般大,说话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不像自己的儿子,只上了个小学五年级就跟着他去放牧了。其实儿子当时还可以上的,可他自己主动提出不上了,说什么去中学的路太远,一个月只能回来一趟,他担心冬天父母亲去看病时家里没人照顾,自己是老大,就应该有个老大的样子,帮父亲挑起这个家。儿子的话让强巴着实吃了一惊,也感动了很久。他没想到儿子这么快就长大了,并且有了一个男人所具有的责任心,这让他欣慰,也让他难过。因为长大的儿子要娶妻生子,可他拿什么给儿子娶妻生子?如果儿子当初继续读书,也能像这个小大夫一样大学毕业成为公家的人就好了,那他就根本用不着愁娶妻生子的钱,也用不着每年跑这么远来给老伴治病,他们可以让儿子回家去给老伴作治疗。当然,那样的话他们也不用整天跟在小大夫后面说好话,而是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告诉儿子病情就行了。强巴一想到这些就更后悔没有坚持让儿子上学,于是就越发地想喝酒。
记得在省城的一个冬天,有一天强巴转了好几个商店才找到他爱喝的那种青稞酒,然后便独自坐在马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里喝了起来,他没有像在草原上那样握着瓶子灌,而是学城里人的样子要了一盘花生米,并要了一个玻璃杯,将酒倒到杯子里一口一口地抿了起来。在他看来,这个动作是很斯文,但同时也很虚伪,远没有那种拿起瓶子往嘴里灌的动作豪爽和过瘾。于是抿了几口后他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可又不好意思拿起瓶子灌,只好端起杯子一口接一口地喝。
店很小,却很适合喝闷酒,除了他店里还有一个人也在喝闷酒,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是不是和他一样有一个常年生病的女人,是不是也在为女人的病和医药费发愁?不,也许他还没结婚呢?如果那样他一定是因为得不到自己喜爱姑娘的青睐而喝闷酒。强巴这样想着,嘴角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笑容。强巴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于是就拿起杯子猛猛地喝了几口,这时候的他忽然有了在草原上喝酒的感觉。
一夜未归,到底醉卧在哪里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却挨了大夫狠狠地一顿训,小护士歪着脑袋瞪着眼睛警告他:如果再喝酒就立刻出院,医院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强巴被小护士的厉害着实吓了一跳,不敢作任何反驳,只是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冲护士说:“呀!呀!呀!”
好几年里强巴的日子就是这么周而复始地度过的。每个夏天的放牧和每个秋天的收获似乎都围绕着冬天的这次出行而忙碌。在大家看来他们全家人的劳动都体现在这次出行上,只有这次出行的成功与否才能体现他们全家人的劳动价值。每一次出行前他们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杨木措喉咙里的那声鸡鸣声从此消失,而她百灵一样的歌声又响起在他们那块美丽的草场上,至少应该响起在他们那顶已经陈旧的帐篷里,那时候强巴一定骑在马上甩着响鞭也唱上那么几句。可每一次的希望很快就会被医生那摇动的脑袋否定掉,医生会用无奈的语气告诉他病情比去年又重了点,治疗一阵子可能会得到缓解。可能会?这是多么含糊的话,难道就没有治愈的可能了?强巴的心有点麻木,麻木的不知道怎么打理眼前的生活,只好听从医生的安排。
一整套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拍片、超声、心电图等,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抗炎支持疗法。直到将强巴口袋里的钱折腾光时,大夫才会告诉他杨木措该出院了。杨木措喉咙里的鸡鸣声已经消失了。
强巴的几个冬天过得都是这么麻木而无奈,强巴真不知道该找谁去诉说心中的无奈。
三
上医学院的侄子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这一家企业医院。侄子告诉他这家医院是对外的,离他们家只有三十公里,快马加鞭也就一个上午的功夫。更让他高兴的是侄子说这家医院完全能治疗杨木措的这个病,并告诉他这个病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慢性病而已,由于拖的时间太长,所以才显得这么难缠。
这个冬天强巴破例没有远行,而是带着杨木措来到了侄子上班的这家企业医院。
强巴觉得这个冬天要比以往的几个冬天简单和轻松些,至少少了对家里的那一份牵挂,大概半个月左右他就可以到家里去走上一趟,看看家里的孩子,给杨木措带点风干的牛羊肉和酥油等。
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已经很滋润了,早晨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饮食习惯冲一碗酥油茶喝,周末他们自然会改善一下伙食吃一些牛羊肉,平时又不间断地吃一些肉干。这样的冬天对强巴来说要比以往的冬天幸福得多,也轻松得多,强巴的脸上有了一丝淡淡的久违的笑容。
强巴在这个医院度过了十几个这样简单而轻松的冬天,这十几个冬天里强巴除了少了一份牵挂依旧很忧伤也很无奈。当这个冬天来临时,杨木措喉咙里的鸡鸣声又叫了起来,他又一次走进了侄子工作的这家医院。
四
他信这个医院,从走进医院的那一刻起,他就对这个医院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大夫和护士们那整天微笑着的脸让他看着舒服,那和蔼亲切的话让他听着顺耳,虽然好多衍他同样听不懂,但他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并且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理解。这让他和他的女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踏实感,感觉就像是到自己家帐篷里了一样。
杨木措时常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对他说:“今年冬天的阳光这么好,我的病也一定好得比往年快,等过了这个冬天,我就可以跟你去放牧了。我们又可以像年轻时一样骑着马追着太阳跑了。”“呀!”看着杨木措充满向往的眼神,他也会忍不住向往起寒冷过后的那个春天,春天多美啊,绿草成荫、野花朵朵,牛羊悠闲而自在地逗留在草地上,牧民们甩着响鞭放声唱着没有什么曲调的歌,同样过着悠闲而自在的生活。许多城里人说那简直就是神仙的日子,无忧无虑,与世无争,浪漫而悠闲。可现在杨木措的病似乎消耗掉了他心中最后的那一丝浪漫,他不得不无奈地期盼清晨,迎候夕阳。每天他看着最后一丝夕阳落下去时他就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没有人知道他是在叹息落日还是在叹息他女人的病,但大家却能听出他那声叹息中的无奈和忧伤。
杨木措的怒火就是从这一声声的叹息中蓄积起来的,她恨自己,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患上这么个半死不活的病,拖累得全家人都没过上好日子。可她听到强巴的那一声声叹息时还是忍不住怒从心起,她认为强巴已经厌烦她了,并且早就开始厌烦她了,从这一声声的叹息中就能听出来。她不怪强巴,一点儿也不怪强巴,强巴是只鹰,是一只能翱翔天空的雄鹰,是她把他拖成了一只瘟鸡,几十年来只能在原地打转转。想想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从刚过三十岁开始到已经走进六十岁,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来他们的每一个冬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挑二三十只放牧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绵羊赶到自由市场出售,然后数着钱回家开始准备去医院的所有物品:酥油、奶茶、糌粑以及风干的肉。起先这些东
西装在羊毛纺织的褡裢里,过了几年后褡裢换成了大大的尿素提兜,又过了几年后尿素提兜换成了人造革的漂亮大提包,现在却开始用上了新式的双肩背包。时间过的可真快,光包都换了四茬,人自然老得都能在水杯中看清白发和皱纹了。杨木措的怒火不能不说掺杂着病中的坏脾气,不仅很不讲理,还无端地发脾气,摔东西,弄得强巴不知所措。
强巴常常独自坐在冬日的阳光中遐想,想他们年轻时候的美好时光,想他们遗落在草原上的那一幕幕浪漫,想那些流传在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还有故事中那些年轻而勇敢的主人公。往事如烟,曾经冬天里的那一个个梦想越来越遥远,遥远的让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他的女人杨木措老了,他自己也老了,老的已经步履蹒跚,思维迟钝了。老的已经懒得搭理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了。
强巴其实挺郁闷的,尤其是跟杨木措生完气后就更郁闷。就常常独自来到医院院子里闲坐,一坐就是大半天。他好想找个人说说话,说说他心中的郁闷,说说他的苦恼。可周围没有人听他讲他的苦恼和郁闷。闲坐的他感觉又回到了自己那空旷的牧场上,于是就忍不住自言自语起来:“年轻时你也是百里挑一的,我也算是草原上的一只雄鹰,可没想到我们的好日子像射出的箭一样短暂,还没到三十岁你就得上了这种病,整天里咳嗽吐痰,吐痰咳嗽,可没少折腾我。夏天放牧,秋天卖羊,冬天带你住院看病,从三十出头,这种日子就从没改变过。我总想着有一天能把你的病治好,然后有钱给儿子娶房媳妇,要娶一个健康的媳妇,再让他们生俩个娃,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我们老去。可这个梦想现在已经破灭了,完全地破灭了。儿子已经过了娶媳妇的年龄,你的病却越来越重了。现在物价涨的这么快,卖羊的钱越来越不够你的医药费了。我老了,真的是老了,许多的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了,我真担心有一天我支撑不住了也倒在床上。那时候我们的儿子怎么办?他到哪里去借钱给我们治病?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难过的很。我甚至想有一天我们能一觉睡过去,永远再不要醒过来。你已经拖累了我几十年,我不希望你再拖累儿子。他要娶媳妇,修房子,现在草原上也流行修房子,在自己的牧场里修几间漂亮的砖房,再做个大火炕,冬天把烟筒放进火炕里,将炉子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坐在火炕上聊天唱歌喝奶茶,那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可要是你的病不好,我明年还得凑钱来给你治病,那么这样的话,这一切的想法都是空的,我们的冬天会越来越凄惶,越来越寒冷。说到这里强巴的眼圈红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强巴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把自己对生活的怨恨都哭出来,全部地哭出来。他怨恨老天给他安排的这种日子,他不知道他错在哪了,只是感觉到老天对他太不公平。对儿子也太不公平。跟儿子同岁的人都结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唯独儿子依然跟他们一起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可强巴终究没有哭出来,而是忽然擦干眼泪站起身朝病房走去。
吃药的时间到了,他还得伺候杨木措吃药。
五
杨木措没有熬过这个冬天,她那折腾了强巴几十年的肺心病终于在这个隆冬的午后加重了,并且出现了心力衰竭和昏迷。
强巴傻傻地站在走廊里看着急匆匆在病房里进进出出的护士们,自言自语地叫着杨木措的名字,叫她赶快醒过来。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等过了这个冬天后去给儿子看媳妇,要一起到夏窝子里去扎帐篷,要去区里赶集……。
杨木措终究没有醒过来,而是永远地闭上了那一双因呼吸不畅而憋得有点泛红丝的双眼。强巴梳理着那一头干枯的灰发,平静得像一尊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