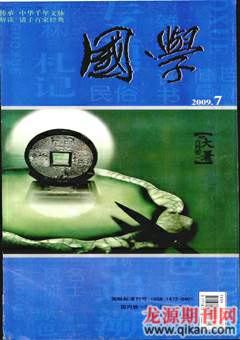老子:颠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学
鲍鹏山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硕大的头颅内究竟包含着多少人生的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际密密的皱纹中不知隐藏着多少阴谋与陷阱;当然,他还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历史罢了。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他生在那么多既有的历史之后,如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般。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不外乎也就是他最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纵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如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幅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您抛弃我们之前,能否劳神一下,为我们留下您的思想?
于是,老子写就了五千言《道德经》。而我从中理出两条思路:一曰治国,二曰处世。
老子的治国之道
大约是看多了历史上君主种种行为所带来的灾难,老子对症下药地开出一剂治国药方——“无为”: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为。”
“贤”是什么?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无知无识、无是无非的宁静。因此老子要“不尚贤”。“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这当然是很阴险的愚民政策。不过,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却不能忍受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中国穷,黄河流域尤其穷,所以必须是以大部分人吃不饱来保证一小撮吃得好的。这一点,倒是档案馆中读死书的老子不能明察的,或者,在这里,他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者当权要仁慈得多了。
作为“为”的产物,“仁”“义”“礼”等等,老子都大加反对。他认定一切都在堕落:“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所以他预言: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我们只要看看周公之德,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就可知他对历史的惊人预见。大约到了荀子的“礼”,再往下便无法收拾了,只好用韩非的“法”,于是出现暴秦,真正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通过这段话,我们也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悲观,对人类文化史的基本评价。在他看来,人类道德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甚至是对其的取媚。所以,他认为,人类历史应该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就是他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的过程。他以为,这是人类唯一的自赎之路。你看他“逻辑”地推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
把这一章和上引三十八章对照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已有的历史是人性的退化史,而逆向行走,才是人的进化史——这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诧的“进化论”!
“小国寡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另外,小国林立,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吧,要“偷渡”不就容易些吗?抬起腿就可以“适彼乐土”。
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原始的自然关系。他还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但人却“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是“无为”的结果,既然“无为”,哪有往来?又何必往来?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
老子的处世哲学
《道德经》中引人注目的第二方面便是老子的处世哲学。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才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新精神。但老子不要。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进步有关,但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吧。我们要注意,这地方是“不敢”而不是“不愿”。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敢”到“不敢”的过程。为什么要“不敢”呢?因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勇敢”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但老子的原意恰恰是否定这个“勇敢”的,他好像在推崇“勇于不敢”。“不敢”是懦弱,是畏缩,为什么还要“勇于”才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敢”并不就如“不敢走夜路”、“不敢喝凉水”那么单纯,很多时候,“不敢”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的,比如当懦夫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这生而发白的老子,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卑鄙地活着吗?
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否定老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的社会就太卑污了,我们自身也太肮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辩护一,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有些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们是把它看成老子的理论主张的,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可以吗?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词,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象的愤激之词不也可以吗?辩护二,我认为,读老子的著作,重要的不是看他提倡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我们来看看老子生活的时代:什么样的血没流过?什么样的阴谋没有被制造过?什么样的悲剧没有上演过?什么样的正义与良心没有被扼杀过?什么样的邪恶与残忍没有猖獗过?什么样的信义没有被出卖过……历史太黑暗了,在阴暗的散发着霉变之气的档案馆里青灯苦读的老子,心灵也不免随之阴暗;现实太邪恶了,饱学博识的老子亦不免随之油滑,甚至狡诈。这是黑暗的历史与现实侵蚀正常的心灵,使心灵亦随之蜕化变质的典型事例。
而老子的处世哲学,正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技术,是苦难重重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是专制社会中唯一能保护自己肉体存在的法术。其诀窍就是通过压缩主体精神与人格,来取得苟且偷生的空间。一句话,有专制,必有老子思想。正如有专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变态。
看老子,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