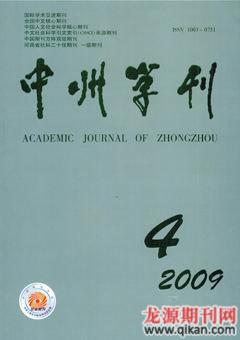《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
刘群栋
摘 要:《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赞誉,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五臣注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关键词:《文选》;五臣注;李善注;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197—06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
据目前的史料看,《文选》五臣注在产生后即得到了广泛流传,世人争相学习。五臣注是第一个成为刻本《文选》的本子,五代后蜀时五臣注已经雕版印刷。直到宋代,五臣注仍然受到相当的重视。以现在已知的宋代刻本来看,李善注刻本僅有北宋国子监本及尤袤刻本两种,而五臣注刻本则有平昌孟氏本、杭州猫儿桥钟家铺子刻本、陈八郎刻本三种。再以宋代的合并本来看,第一个合并本的六家注《文选》——北宋秀州本即是以五臣注为底本,将李善注逐段铨次编入而成。五臣注排列在前李善注排列在后的六家注本有秀州本、广都裴氏本、明州本三种;而李善注排列在前五臣注排列在后的六臣本只有赣州本、建州本两种,由此也可见五臣注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从宋代热衷于合并五臣注和李善注的事实来看,五臣注和李善注都有其合理之处,所以合并本在宋代要比单独的李善本或五臣本多。
近代以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唐钞《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五臣注的价值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新时期以来,随着《文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倪其心、顾农、陈延嘉、王立群、甲斐胜二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五臣注,初步论述了五臣注的合理成分,呼吁重新认识五臣注的价值。但仍有很多人对五臣注的价值认识并不全面,还停留在批评的阶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五臣注的价值进行深入探究。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
一、《文选》五臣注产生的背景
五臣所处的开元年间,李唐王朝达到鼎盛时期,有足够的财力物力进行文化建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又喜爱文事,对文化事业比较关注,专门下诏令人整理修补散乱残缺的四库藏书。据《唐会要•经籍》记载:
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省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辑,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
七年九月敕: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①
同时,唐玄宗鼓励学术的百花齐放,不仅命人编辑整理了大量新的书籍,如《初学记》、《群书四部录》、《文府》、《六典》等,他还亲自
注释《孝经》、《道德经》,并颁行天下。五臣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文选》自编成以来,在南北朝时期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为一般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所以《文选》在隋唐时期成了士子必读的书籍。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断调整,进士科加试了杂文和诗赋,《文选》在唐代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五臣
注释《文选》之前,隋代萧该著有《文选音》,唐代曹宪著有《文选音义》,李善著有《文选注》、《文选音义》、《文选辨惑》,公孙罗著有《文选注》、《文选音义》,许淹著有《文选音义》,等等。由于《文选》本身不易读懂,所以这些
注释也成为士子们必不可少的阅读工具。特别是《文选》李善注,更是风行。李善注从详备的角度说确实无可挑剔,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士子们研习《文选》的目的。对大多数士子来说,学习《文选》仅仅是其谋取进身之阶的手段,他们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李善注的详备该博扩大了《文选》的篇幅,对精心研读者可能大有裨益。但对于只是为博取功名的士子来说,浩繁的篇幅无疑造成了学习的困难,因此,认真钻研者寥寥无几。急于求取功名的士子往往走捷径,热衷于学习那些内容少、简单易学又能奏效的学问,我们可以从明经的学习情况窥其一二。下面两条史料很能说明问题:
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②
开元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瑒奏:“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请量加优奖。”遂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③
上述材料表明,士子明经仅仅是为了进入仕途,都愿意学习文字少、易学的书籍,《左传》、《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因文字多,士子大都不愿意学习。虽然国家三令五申鼓励学习《左传》等文字多的经籍,但收效甚微。这里虽然说的是明经,但对于进士科的人同样适用。士子们为了获得出身,往往避重就轻,他们的学习仅仅是为了获得进入仕途的阶梯。
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的记载了解一下当时士子们的应试态度及学习效果。据《大唐新语•惩戒》记载: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④
张由古在高宗朝曾任侍御史,虽然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官场的,但其连班固字孟坚都不知道,可见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当然,这仅仅是比较特别的现象,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士子们的学习态度和效果。
《唐会要•贡举中•进士》又载:
长庆元年……三月丁未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实才,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眷言败俗,深用兴怀。郑郎等昨令重试,乃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至多。其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余落下。”⑤
这里记录了当时科考取中的郑郎等人在重试中不知“孤竹”之出處本事,亦可见他们专为应试的学习态度。张由古生活在高宗朝,或许当时李善注还没有成书,但是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仍然有这些现象,说明他们肯定没有认真阅读李善《文选注》,否则即使他们没读过《周礼》,也肯定会知道出处。所以,以《文选》李善注来说,
注释虽然比较详细,但对一般只要求获得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未必适用。这种时代风尚为五臣重新注释《文选》提供了契机。
李善注本身的特点也为五臣提供了重新注释《文选》的空间。李善注着重释典,探究其出处,训诂务求原典,或引前人成说,很少解释大意。这种注释方法对学者们确实方便,但对于初学写作和应付考试的士子来说却显得过于繁复,使士子们望而却步。五臣注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它是为了让一般读者借助注释就能直接阅读《文选》,它明确知道读者的阅读需求,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原文,了解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引导读者体味文本本身的特点。因此,五臣注尽量避开李善注的特征,训诂尽量简便易懂,虽难免有臆解之处,但却通俗易懂,注重串释大意,避免了李善注“释事忘义”的缺点。据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所言,五臣因为李善注存在“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⑥的缺陷和不足,才重新注释《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优略暂且不论,我们仅从注释宗旨来说:李善注寻根溯源,讲究注释典故出处;而五臣注则“是从写作文章的角度出发的,重在‘述作之由,要求注出‘作者为志,便于学者揣摩。因而五臣注不求训诂精确、释事翔实,不多征引,而以疏通文意为注”,“实际上这是文人作注,与学者李善作注迥不相同。但是对于学习写作、揣摩文章的士子来说,五臣注的简注详疏,比较便宜”⑦。五臣注和李善注所面对的读者群和
注释目的不尽相同,李善注面对的是高层次的读者,适合学者钻研;而五臣注则更适合初学者和一般士子应付考试,学习写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唐代中后期五臣注一直比较盛行。
二、《文选》五臣注的特点
《文选》五臣注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五臣注的特点体现出来。笔者在参与整理六家本《文选》的过程中,参校了多种《文选》注本,对五臣注的特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发现其有独到之处。下面结合五臣注的文本以及笔者的校勘实践对五臣注的特点进行大致的概括。
注重串释大意是五臣注的第一个特色。串释大意是五臣注最主要的特色之一,也是五臣注和李善注的主要区别之一。李善注一直有“释事而忘义”的弊端,虽然李匡乂认为李善绝笔之本“事义兼释”,但从今天流传下来的李善注来看,主要是释事,虽有疏通语句之处,其篇幅也很少。五臣注则主要以疏通文句为主,间有释事之处。这样的例子在五臣注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谓弥补了李善注“释事而忘义”的缺憾。串释大意更便于初级读者理解文意。五臣注以串释语句为主,抛开了李善注征引式的
注释方法,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李善注的训释模式,另外也避免了李善注所说的“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的问题。五臣注的串释不乏点睛之笔。如卷九班彪《北征赋》“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諐。何夫子之妄托兮,孰云地脉而生残”,李善注仅引其本事曰:“《史记》曰:赵高者,诸疏远属也。为中车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赐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壍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毋绝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药自杀。”而五臣吕延济注除了引本事外,末又加了一句:“彪言恬至死不知其过。”这句话言简意赅,点明了作者的意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注重解题是五臣注的第二个特色。据陈延嘉先生统计,“《文选》按六臣注本是714首,其中无解题者167首,有题解者为547首。在这547首中,李善与五臣都有题解者270首,李善有五臣无者19首,五臣有李善无者258首”⑧。从此可以看出五臣注更注意揭示写作背景和创作原由,有多出李善注者。五臣注在吸收前人训诂成果的基础上,将具体篇目的创作背景与作者生平相结合,挖掘出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文选》
注释学上的一大进步。五臣解题一般都在作者下面,在介绍作者的同时进行创作原由的分析。即便是李善和五臣同有解题,五臣亦有多出李善之处,重在揭示作者的创作原由和创作意图。如卷四张平子《南都赋》下,五臣李周翰注曰:“南都,在南阳光武旧里,以置都焉。桓帝时议欲废之,故衡作是赋,盛称此都是光武所起处,又有上代宗庙,以讽之。”又如卷四左太冲《三都赋序》下,李善注曰:“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遂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卭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遍于海内。”而五臣吕向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李善注突出了左思的生平和作赋的情况,五臣注不仅交待了左思作赋的具体情况,还交待了作赋的原因,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又如卷十一王仲宣《登楼赋》,李善注曰:“盛弘之《荆州记》曰:富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又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献帝西迁,粲从至长安,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后太祖辟为右丞相掾。魏国建,为侍中,卒。”而五臣刘良注则曰:“《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少而聪敏,有大才,仕为侍中。时董卓作乱,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李善注交待了王粲的生平和大致情况,五臣注不但交待了王粲的生平,还交待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原因和他当时所处的境况。此种例子还有很多。这种题解正是五臣注揭示“作者为志”⑨的地方,也是五臣在李善注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写作背景的可取之处。这些创作背景的揭示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对写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此外,五臣解题还有指明《文选》所列序之是非,如卷八扬子云《羽猎赋》下,李善无注,五臣张铣注曰:“此赋有两序,一者史臣序,一者雄赋序也。”五臣此注指出了此赋所以有两序的原因。当然,五臣的解题也不免有臆测之处,但其对作者创作原由的探索值得肯定。
直接释词,
注释简略是五臣注的第三个特色。李善注的训诂方式是引经据典,或引旧注,或引集注,或引前人成说,很少直接解释词义;而五臣注则务求简约,所以直接释词,不再一一交待其出处。五臣这种
注释方式使注本篇幅大幅度减少,方便读者阅读。如卷一班孟坚《两都赋序》“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国家之遗美,亦雅颂之亚也”句,李善注仅释“揄”、“扬”二字,作:“《说文》:揄,引也。孔安国《尚书传》曰:扬,举也。”而五臣则直接解释词义,且解释了6个字,多出李善注4个,作:“雍,和;容,缓;揄,引;扬,举;亚,次;嗣,代也。”又如班孟坚《西都赋》“辍而弗康”李善注曰:“郑玄《论语注》曰:辍,止也。孔安国《尚书》传曰:康,安也。”而五臣张铣注则曰:“辍,止;康,安也。”
注释同样两个字,李善因为要援引出处,所以多出很多篇幅,五臣
注釋时直接释词,不交待出处,且简单明了,更便于读者阅读。这是五臣注所面对的读者层面所决定的。
突出写作方法是五臣注的第四个特色。五臣注既然是为学习写作的初学者所用,那么对写作方法的揭示就成为其
注释时的重点。如卷一班固《西都赋》“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下,李善于此处无注,五臣吕延济则注曰:“假为宾主,以相问答。”又如张衡《西京赋》“有凭虚公子者”下,李善注引薛综曰:“凭,依托也。虚,无也。言无有此公子也。”而五臣吕向注则曰:“凭,托也。虚,无也。实无有此公子,假言发问答也。”五臣注揭示了文章假借宾主问答而展开的写作方法,而李善注则未明言。又如卷九班彪《北征赋》“惟太宗之荡荡兮”,五臣吕向注曰:“文帝庙号太宗。彪云太宗者,互其文也。”这里揭示了文章互文的写作手法,便于初学者有针对性地学习。又如卷二十潘岳《关中诗》“锋交卒奔,孰免孟明”句下,李善仅注其出典,而五臣吕向则注曰:“言锋刃始交,士卒奔北,军将谁免孟明之败者。孟明氏,秦将,尝为晋所败,以为喻也。”这里交待出了作者写作中常用的比喻手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文选》保存了先秦至南朝梁代的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所收多为传颂已久的名篇,为后世的文体写作提供了范本。《文选》本身的选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满足了当时文人学士学习写作的需要,是习作的范本。五臣注这种揭示写作方法的
注释方法更便于初学者结合具体的篇目学习不同的写作方法,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正文夹大量音注是五臣注的第五个特色。李善注虽然也有大量的音注,但李善音注都在注文中;而五臣音注则夹于正文中,更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从音注的总量上来看,五臣音注要比李善音注多出许多。以唐写永隆本《西京赋》残存的部分统计,写本音注共计212条,北宋本243条,尤袤刻本245条,陈八郎本和正德本都有的五臣音注共计308条,其中北宋本脱掉1条,而尤袤刻本则有1条北宋本无,而五臣音注有,这明显是五臣音注混入者,如此则刻本李善注中音注共计244条,同篇幅的五臣音注则为308条,五臣和李善共同有音注的则为202条,李善有音注而五臣无者有42条,五臣有音注而李善无者则有106条。此虽是抽样调查,但仍能体现出五臣音注比李善多的特点。《文选》中保存了许多中古词汇、诗歌用韵。在正文中夹音注的方式对于学习者来说有积极作用,不仅方便读者阅读正文、理解文意,可以起到因音辨义的作用,而且有助于读者学习诗歌用韵。
三、影响五臣注评价的两个重大问题辨析
这里顺便辨析一下前人关于五臣注袭取李善注以及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的问题,因为这是后人诟病五臣注的两个重要理由。辨明这两个问题,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五臣注的价值。
先说五臣注袭取李善注问题。晚唐李匡义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这种批评对后世影响深远,贬五臣注者往往奉为圭镍。五臣生当李善注已经成书的盛唐时期,当时已经流传的《文选》注书有萧该的《文选音》、曹宪的《文选音义》、李善的《文选注》与《文选音义》、公孙罗的《文选注》与《文选音义》、许淹的《文选音义》等书,五臣注《文选》时必然要吸收之前的
注释成果,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五臣注的最主要特征是引典少,主要疏通文意,从这个层面来说,五臣继承了汉代以来的注疏方法。以日本所藏唐钞《文选集注》中所保存的《钞》和《音决》来看,《钞》中经常有疏通文意的语句,而在《音决》后又常收有五家音。五臣注中的串释大意处最多,而串释性
注释在李善注中比较少,即便说是抄袭,也可能抄袭了《钞》或者李善所引各家旧注,而《钞》或者李善所引各家旧注中的串释性语句比起五臣注来说,其篇幅更少,所以五臣注应该是在总结各家旧注的基础上进行的
注释。一般认为《音决》是在权衡各家音以后做的音注,其中各家音注不同时引有萧、曹、许等人的音注。《文选集注》在《音决》后仍然引有五家音,这说明五家音有多于其他各家音注者。既然可以权衡各家音注而后作《音决》,那么五臣为何不能在注释时吸收各家注音成果进行音注呢?
五臣注中不但有许多与李善音注和《音决》相同者,还有多出李善音注和《音决》者,更有许多不同于李善音注和《音决》者,这可以从古汉语语音发展中找到原因。从古汉语语音发展情况看,语音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王力先生认为,隋至中唐的声母和魏晋南北朝完全一致,共有33个声母,只是到了唐天宝年间,在原来声母的基础上又分化出来3个声母,变成了36声母。《文选》李善注成书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文选》五臣注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两者相距仅60年,语音的声母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二者的音注出现相同的情况应是自然而然的。但同时,隋唐之际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语音也出现了更多的韵部,随着社会的发展,韵部也在不断进行着分化合并,这也会使一些词语的读音发生变化。从初唐到盛唐,随着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语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五臣
注释《文选》时,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五臣注中体现出这些变化。那么,五臣注有多出李善音注和《音决》者,更有许多不同于李善音注和《音决》者就可以理解了。
总而言之,五臣作注时已有很多《文选》音义之书及注释,所以五臣在注释时一定作了参考,但如果全部断为抄袭,则并非公论。五臣注在吸收了以前各家注释的合理成分以后,又避免了其过于学术性的缺点,注重了注释的普及性和通俗性,这是五臣注之所以流行的主要原因。
再说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问题。五臣注与李善注在正文文字上有许多差异,过去总认为这是五臣私改李善注的结果。李匡乂也因此批评五臣注“轻改前贤文旨”⑩,这种批评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后人长期否定五臣注的一个重大原因。自李匡乂之后,凡是批评《文选》五臣注者皆说其正文不可据,因其轻改前贤文旨故也。笔者在校勘韩国奎章阁藏本六家注《文选》的过程中,参阅了许多目前发现的《文选》写本和刻本,根据目前的校勘结果来看,五臣所用《文选》底本和李善所用底本不是一个系统。如五臣本中曹植《七启》中“寒芳苓之巢龟”的“寒”字,一直以为是五臣改“寒”为“搴”,今《文选集注》中引《钞》作“《钞》曰:搴,取也。”又引《音决》曰:“寒,如字。或作‘搴,居辇反。非。”又有按语曰:“今案:《钞》‘苓为‘灵。陆善经本‘寒为‘宰。”根据《文选集注》所引书顺序,《钞》、《音决》成书都在五臣注之前,说明“寒”作“搴”并非五臣擅改,而是其来有自。《钞》所用本“寒”即作“搴”,而《音决》则认为作“搴”不对,陆善经本则作“宰”,与李善本和五臣本皆不同。这种例子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尚有很多,足可证《文选》在唐代已有很多种钞本,正文文字互有不同。敦煌写本的发现,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五臣注的价值提供了珍贵的文本依据。敦煌写本保存的《文选》原貌,许多地方比后世公认的最好版本——李善本更好,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五臣本与今存李善本不同的地方往往与敦煌写本相符。如五臣本鲍明远《东武吟》中有“倚杖牧鸡”句,李善本“牧”作“收”字,然敦煌写本亦作“牧”,和五臣本正文相同,李善亦无解释,是李善本误,或所本不同也。又如鲍明远《东门行》“行子夜中饭”句,李善本“饭”作“饮”字,然敦煌写本和《文选集注》亦作“饭”,和五臣本相同,是李善本误,或所本不同也。这样的例子尚有很多。南宋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后附有李善本、五臣本同异,今所见宋刻本五臣、李善合并本亦标有李善本、五臣本异同,且五臣、李善各有解释,注释文字亦可证明李善本、五臣本正文用字不同。此种情况是由于抄写过程中出现了误字,或因为字迹模糊难辨,或因为抄手误写,原因很多,不可尽知。另据《文选集注》中所下校语来看,五臣本很多正文和《钞》、《音决》、陆善经本相同,而和李善本不同,这也说明并非五臣擅改文字,而是李善和五臣文本皆有所据,不是出自一个文本系统。总而言之,不能轻易下结论说五臣“轻改前贤文旨”,只能说李善、五臣必有一误,或者两者皆误。五臣本、李善本正文不同者并非全是李善是,五臣非;也并非全是五臣是,李善非。若没有敦煌《文选》文献及《文选集注》的出现,则五臣将永世蒙受不白之冤。在已经有很多唐写本出现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比较客观地说,李善本和五臣本正文各有千秋,皆有错误,都并非完璧无瑕,但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其价值。
我们还可以通过宋代五臣和李善合注本中对五臣本、李善本异文的取舍来看宋人对待二家正文中异文的态度。秀州本几乎全部采用五臣本正文,按语中只是交待出李善异文;明州本基本也采用这种方法;赣州本正文则兼取李善本和五臣本,其校语或说五臣作某,或李善作某。正文全取五臣者,不容易看出整理者的态度,因为其选用五臣本作底本。但其为何选用五臣本而非李善本作底本,本身也暗含了一种态度。正文兼取两家的赣州本则明确地体现出整理者对待五臣本与李善本异文的态度,即他们认为五臣本合适的就采用五臣本,在按语中列出李善本异文;认为李善本合适的就采用李善本,在按语中列出五臣本异文。虽然赣州本整理者的取舍未必都很恰当,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待五臣本与李善本的异文不是简单地是此非彼,或者是彼非此,而是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些异文。
总而言之,《文选》五臣注具有重要的价值。它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它和《文选》李善注、《文选》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此外,五臣注还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在版本方面,五臣注有自己的优长。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注释
①②③⑤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2、1630、1627、1634页。
④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页。
⑥⑨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正文社影印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活字本,1983年,第5页。
⑦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俞绍初、许逸民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305页。
⑧陈延嘉:《论五臣注的重大贡献》,俞绍初、许逸民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82页。
⑩李匡乂:《资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