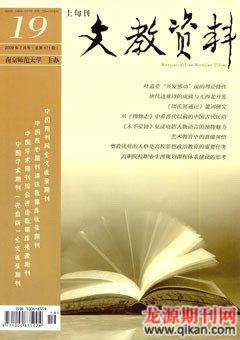试析徐陵为何没能成为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
张 俊 孙 超
摘要:徐陵和庾信都是南朝重要的宫体诗人。他们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徐陵最终没有成为庾信那样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重南朝、轻北朝的诗学观;有家不得归的游子情怀与元家可归的乡关之思;北齐与北周文化政策不同;南返后的诸种原因。
关键词:徐陵 庾信 融合南北诗风
徐陵历来被视为著名的宫体诗人。其诗歌也被评为流丽轻艳。实际上。他的诗并非全是艳诗,他也写过一些边塞诗,如《出自蓟北门行》、《关山月(二首)》等,在取材、布局及写作手法方面已有开启唐代边塞诗风的迹象。如“天云如地阵,汉月带胡秋”(《出自蓟北门行》)、“平生燕颔相,会自得封侯”(《出自蓟北门行》)等诗句就充满了一种类似盛唐边塞诗中昂扬亢奋、积极进取的激情。其中,《关山月(二首)》对李白的边塞诗产生了直接影响,屠隆赞其“壮浑”(《徐陵孝穆集·引》)。另外,徐陵也有一些清新的写景、送别之作,如《新亭送别应令》等。《山斋》历来被推为其闲适诗的代表作,这更与那些轻靡浮艳的宫体诗不同。徐陵晚年作品留存较少,其临终前一年所作的《别毛永嘉》,平淡质朴,感情真挚,沈德潜云:“似达愈悲,孝穆集中不易多得。”(《古诗源》)其诗在格律上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陈绎曾的《诗谱》说阴铿、徐陵、江总的诗乃“律诗之源”。总的来说,徐陵是梁陈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与同时的庾信相比,地位却相差很远,他最终没能成为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
徐陵与庾信早年有着相似的经历,其父均是梁朝著名官体诗人。“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北史·庾信传》)。徐陵和庾信在梁朝已有文名,仕途得意。承圣三年(554)四月,庾信出使西魏,同年十二月,江陵陷落,萧绎被杀,庾信羁留北方,至死未归。以此为界,庾信后期在北朝的作品多写乡关之思、羁旅之恨,风格也一变而为苍劲。后世一致认为他“是最早把南方文学的文采和北方文学的气骨在作品中溶化、统一的大作家”。㈣而徐陵于太清二年(548)出使东魏,因侯景作乱而滞留北方长达七年之久,至绍泰元年才返回江南。表面上看,他们有几乎相同的遭际。那为什么徐陵没能成为融合南北诗风的大家呢?以下试析之。
一、重南朝、轻北朝的诗学观
徐陵生活在以“重娱乐、尚轻艳”的文学思想为主潮的梁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提倡,以及“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使“宫体”文风笼罩文坛。《南史·徐搞传》云:“徐搞……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搞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徐陵作品的风格近似其父而成就过之,他的这种诗学观坚守了一生。
,像陵出使东魏,可谓挟重名人北朝,而此时的北朝文坛正处于向南朝学习的阶段。史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唠,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日:‘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睹。”(《北史·魏收传》)可见,北朝的两位最重要的作家均模仿南朝文人作品。由于南北文学的差距,以及徐陵自身的文学成就,“北朝文士重徐陵”(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徐陵也自视甚高,轻视北方文人。刘觫《隋唐嘉话·下卷》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日:‘吾为魏公藏拙。”徐陵轻视北方文人,没有主动向他们学习,这是徐陵没有成为融合南北诗风大家的最主要原因。
庾信作为亡国之臣,屈节仕敌,这使他不仅在政治上谨小慎微,而且在文学创作上迎合统治阶级的口味。他人北后创作的一些刚劲豪迈的边塞诗,如“阵云千里散,黄河一代清”(《奉和平邺应诏》),“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同卢记室从军》)多是应制唱和之作,其创作动机与他在南朝所作的《奉和咏舞》类的艳情诗并无二质,都是服从统治阶级意志的作品。这也促使庾信主观上愿意主动学习和接受北朝雄浑的文风,从而融合南北文风,创作了大量“穷南北之胜”的佳作。
二、有家不得归的游子情怀与无家可归的乡关之思
徐陵与庾信都曾被迫羁留北方,但在北朝生活期间。二人的心境大不相同。徐陵被迫滞留北方,他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他的思念是具体、真切的。是对父母妻儿的无限眷恋,这在《在北齐与杨遵彦书》中有集中的体现。文章首先对北齐强留他的八种借口一一驳回。析理透彻,不卑不亢,辞藻华丽,用典灵活贴切。而后,说到思归之情时,又流露出了深沉的哀愁,真挚感人。文日:“且天伦之爱,何得忘怀?妻子之情,谁能无累?”徐陵独自羁留北方,而南方烽火不断、生灵涂炭,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对强留不还的怨恨,对亲人的思念。使他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忧愁和哀思。文日:“如得身还乡土,躬自推求,犹冀提携,俱免凶虐。”人生命运的巨大转折、荣辱福祸的强烈反差促使他思索人生,对人的生命意识进行探寻。文日:“岁月如流,平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弛扬越,朝千悲而掩泣。夜万绪而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这种对人生有限的感慨极似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但是相对于曹操感叹生命短暂、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统一天下的壮志,徐陵流露出的更多的是深深的哀愁,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叹息。
相比而言,庾信的乡关之思却并不那么具体。历代学者都认为庾信后期作品的苍劲风格来源于他的乡关之思,但实际上庾信的思念是泛指的、抽象的,是一种概念上的思念,并非痛彻心扉的牵挂。庾信在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出使西魏,其父已于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去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死于战乱中。江陵陷后,庾信被留长安,西魏统治者将十万俘虏带至长安为奴,其中就有他的母亲和妻子,幸亏好友宇文泰帮助,才得以放还。至此,庾信终于与他仅剩的亲人相聚了。至此,庾信与南朝已经没有了实际上的关联,他无家可归,西魏已经是他真真切切的家了。所谓的乡关之思也只是他在政治上不被信任,失意时对业已灭亡的梁朝的留恋,以及对自己显贵生活的怀念罢了。庾信对陈朝不但毫无感情可言,还十分轻视行伍出身的陈霸先:“锄援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之气,终于三百年乎?”(《哀江南赋·序》)因此,庾信“无家可归”的乡关之思可以融化于诗句之中,他可以通过诗句来冷静地总结梁朝灭亡的原因。而徐陵“有家不得归”的痛楚却使他哽恸难言:“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愤,恒表思乡之梦。”(《在北齐与杨遵彦书》)可见,无法消释的思乡情使徐陵无法专注于文学创作,更不会主动去吸收北朝文风了。
三、北齐与北周文化政策不同
北齐与北周虽都处于北朝,但其文化政策却不尽相同。北齐统治者高洋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与其父高欢一样都不赞成汉化,不仅敌视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而且对汉族文化颇为轻视。高洋贬谪王昕的罪过之一便是“伪赏宾郎之味,好泳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北史-王宪传附昕传》)。他的这种文化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南北文学的融合。徐陵被拘的七年正是高欢、高洋父子掌权的时期,他处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自然不会有良好的文学创作环境,无法自由地与北方文人唱和、文会,因此北朝文风对其影响甚微。而北周统治者实行的是团结当地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的政策,在文学上继续推行汉化,因此,庾信仕魏之后立即与宇文氏“有若布衣之交”,经常与统治阶级交游、唱和,这为其学习北朝诗风提供了客观条件。
四、南返后的诸种原因
徐陵在梁敬帝绍泰元年(555)五月返回江南,南返之后即开始了他看似辉煌的政治生涯,他历任尚书左丞、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可谓仕途得意;在文学上,“业高名辈”,被称为“一代文宗”、“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陈书·徐陵传》)。然而在如此尊贵的地位背后,徐陵却生活得谨小慎微。徐陵由梁入陈,参加过反叛武帝陈霸先的军队,后来又得罪了宣帝陈项,这两次站错队,是徐陵政治生涯中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尽管两位帝王后来都对他“恩宠有加”。但他不得不在政治上更加谨慎。这种微妙的政治地位,使他对当朝主上忠心耿耿,努力工作,很少敢于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因此,徐陵后期虽然著作颇多,但大多是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很少有诗作传世。“吾身归来乡国,极徙炎凉,牵课疲朽,不无辞制,而应物随时,未曾编录”(《答族人梁东海太守长孺书》)。他此时的心态仅仅是“徒怀北氓之切,未遂东都之期”(同上)罢了。虽然在晚年,徐陵表现出了对“文制兼美”(《与李颐之书》)和“披文相质”(《与李那书》)等融合南北诗风的向往,但陈朝文学仍以宫体文学为主,他已失去了融合南北诗风的环境。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徐陵最终没能成为像庾信那样融合南北诗风的诗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