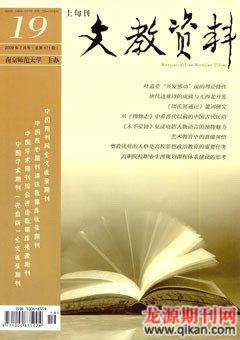析陶渊明的狷隐人格
田 玲
摘要:陶渊明的隐逸生涯显露出鲜明的狷者风度,狷与隐交织,难分因果。本文试对陶渊明的狷隐人格加以分析。以彰其节。
关键词:陶渊明 隐逸 狷
隐,或为沽名钓誉,或为隐忍待时,或为避世悠闲,或为求仙问道,目的不一。关于隐较早的评述源于《易经》坤卦引辞:“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日:“幽人贞吉。”狷者也经常以隐士的形象出现,他们多是不满现实社会并对人生有着不同于流俗看法的高洁之士,他们选择隐居,有所不为,洁身自好,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是著名的隐士。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记载了他的名字。观其一生,陶渊明的隐逸生涯显露出鲜明的狷者风度,狷与隐交织在一起,难分因果。
一、出仕与隐逸
中国文人习惯于以儒家思想中“兼济天下,泽被苍生”的现世功德作为自己人生价值实现与否的衡量标准,陶渊明开始亦不例外。而立之年,陶渊明作《命子》诗,追述先辈的勋业——“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的昌隆,“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的伟业,陶侃“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显赫——作者为陶唐氏在华夏历史上的“历世重光”而骄傲,对自己年届而立却毫无建树感到羞愧,不由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拟古九首》之二中,陶渊明写道:“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同感于孑L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之遗憾。
然而,在接受儒家立功立德的价值信仰之外,陶渊明的性格还有与此矛盾鲜明的另一面。在诗文中,他屡屡述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宴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明自己少年时就远谢俗缘,崇尚淡泊,喜爱自然。也许正是由于诗人个性气质的多面性。儒家的积极进取与道家的任性超脱才能交织在一起,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真正产生恒远影响。
青年陶渊明,一副积极人世的热肠。但是,他身处的东晋末年“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感士不遇赋》),个人事功的成败根本不取决于自己的才华与努力:“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因此,“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而徒勤”。并且,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刚直仵俗的性格必然会与黑暗的官场发生冲突,在仕途上势必难以前行。
更重要的是。汲汲于事功的潜在鞭策造成了陶渊明精神的躁动紧张,耿耿于穷达使得他的人生陷入动多滞碍的境地。功业不成,心灵就会处于一种渴慕状态而失去平衡。精神就会驰骛于外而不是反求诸己,失去自我生命的真性情。每一次踏上仕途,陶渊明都感到心为形役、为人所羁,不得自由。从29岁起为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陶渊明时隐时仕了13年,每次做官的时间都非常短,而且每次都是始出便思归。初仕起为州祭酒,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在义熙元年陶渊明41岁的这一年里,他竞两次出仕两次归田。从向立年到不惑年,陶渊明频繁地忽隐忽仕,在隐与仕之间矛盾挣扎——仕有仕的痛苦,隐有隐的不安。终于,在义熙元年,陶渊明结束了这种痛苦徘徊的状态,辞去彭泽县令,从此一心归隐田园,终身未曾离开。《归去来兮辞》堪称陶渊明的归隐宣言。为了免于逢迎世俗,为了顺应自己刚直的个性,为了精神与心灵的自由,陶渊明最终选择了解缨弃冕,躬耕田园。
受儒家文化影响积淀而成的社会习俗是“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出仕是士的素业本职,如同农夫耕田、商人经商一样。士之不仕犹农夫废耕,相对于各自的社会角色而言都是一种离职失职。陶渊明弃官归隐这样的离职行为必然遭到众人的不解、议论甚至责难。在《祭从弟敬远文》中,陶渊明回顾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推手,置彼众议。”可见他为归隐之举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陶渊明选择归隐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特立独行,乖时悖俗。在《饮酒二十首》之九中,诗人表达了自己不屑世俗毁誉、杜门不仕的决心。
二、君子固穷
对中国文人而言,人世为官不仅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还是生活经济的来源。孟子云:“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鄙视稼穑的观念到了魏晋已经成了士人的基本共识。陶渊明纠正并突破了儒家鄙视躬耕的局限与偏颇,无视当世读书人鄙夷不屑的眼光,将躬耕田亩等同于忧道守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躬耕是为了能够“志长勤”。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虽不乏鄙夷之意,但在古代中国倒是一句符合国情的实话,耕者总是辛苦劳碌却难图温饱。陶渊明放弃官职,便意味着要坚持终身地辛苦劳作,要忍受耕不救穷的煎熬,“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不得不付出的生活代价。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陶渊明除了从事种豆、收稻、灌园等田园工作外。还兼织席子、打草鞋、卖蔬菜,仍是难以满足基本的温饱之需。
陶渊明晚年,生活犹为艰辛:“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有会而作》序)诗人甚至挨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檀道济任江州刺史时,曾去看望陶渊明,而诗人当时“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诗人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赠粱肉,陶渊明“麾而去之”。陶渊明战胜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望,坚守君子固穷的节操,在贫困中不坠其节、不改其志:“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并且更为难得的是,诗人能在心理上不为贫困所局限,将外部环境完全摈弃于自己的心境之外,让个体精神超越日常的贫富枯荣:即使是穷困到出门乞讨的地步,诗人也没有呼天抢地,我们甚至连一句申诉与叹息都听不到。当主人用酒饭请他饱餐一顿后,他便全然忘记自己的艰难,忘记了明天等着他的饥饿,快乐地闲谈赋诗。这种不愁下顿的旷达,源于非一般的精神超脱与执著。
陶渊明曾作《五柳先生传》,时人称之为“实录”。钱钟书先生解释如下:
“陶潜《五柳先生传》。按‘不字为一篇题目。‘不知何
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
三、纵浪大化
生命是人存在的根基,对人而言,“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因为“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看,儒家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事奋斗,从而赋予短暂的人生以密集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超越日常的平庸与死亡的局限,试图在现实人际和短促人生中赢得永恒。陶渊明曾经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来超越自我生命的有限。但是,价值世界往往与现实世界脱离甚至对立,贤士多不遇且不幸:“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感士不遇赋》),儒家的功名贤达在复杂的人世风云面前显得苍白、空泛。
并且,儒家不朽的名与个体自身的命又是相互外在的东西。生命倏忽如白驹过隙,仅仅持此生命一世的人又怎么可能不朽呢?千古留名对死去的个体自身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且“穷达不可外求”(《与子俨等疏》),求不到功名,痛苦抑郁;求到功名,又为功名所累。陶渊明屡屡纠缠的功名进取之心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首》之四
“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已酉岁九月九日》),死亡吞噬并带走个体生命曾经拥有的一切,陶渊明强烈意识到生命的虚无:“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于他这般敏感的人而言,如何面对这种幻化感、空无感必定成为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道教企盼羽化登仙长生不老,来抗拒和回避有限生命的虚无。魏晋时代,儒学价值大厦的崩塌促进了士族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生命的珍视和喟叹成为精神生活的中心。生的自觉必然导致死的恐惧,因而服药修道之风大盛。陶渊明否定了这种途径,肉体怎会长生呢?“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形影神》组诗三)。即使肉体真的能长生不老。这种长生也仅仅只是个体在时间上的单调重复,必然会使生命苍白无聊、失去意义:“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八)。
儒家的立善求名,道教的炼丹修道都缘于个体对自我有限生命的珍视。执著于自我必定为自我的生死问题所拘,有限的人生便不得自由。陶渊明看破了此两者试图不朽的诱惑,强调只此一生:“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并以巨大的勇气直面生死:“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组诗三)。与大化同流纵浪大化之中,让自己与永恒宇宙融为一体,摒弃局限于自我的细碎意识,也就获得了一种无挂无碍不沾不带的悠然洒落。陶渊明作《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将死亡视为辞别人世“逆旅之馆”而“归于本宅”罢了,眼见死神缓缓来临却无半点惶恐与悲哀,泰然自在从容自若。《挽歌三首》是陶渊明的绝笔诗,临终前诗人依然说得自自在在,语调纡徐舒缓,不落半点哀境。告别人世前的反应是如此平静旷达,人类真正的大智大勇或许便是这种面对死亡时不喜亦不惧的静穆吧。
陶渊明纵浪大化的取向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有相承之处。陶渊明好《庄子》,朱自清先生曾统计过陶诗的用事,以《庄子》最多。不同的是,陶渊明在庄子式的超旷背后仍有儒家忧勤惕厉的支撑。陶渊明让人与自然在某种价值与意义的观景上重新合一,归隐田园并没有中止自己的社会人生关怀,并没有让自我生命等同于自然的混冥,非历史非价值,无是无非。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道德修养:“自我独报兹,黾勉四十年”(《连雨独饮》)。“任真”在陶渊明的概念中并不是一任本能的放纵冲动,而是不让世故俗念扭曲自我的本性,“独报兹”是通过“黾勉”使一个人的内在之性与外在之命融和。斯亦为狷。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2287.
[2]朱熹.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266.
[3]朱熹.孟子·万章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317.
[4]萧统.陶渊明传.全梁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58.
[5]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1228-1229.
[6]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刻(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8.
[7]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刻(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