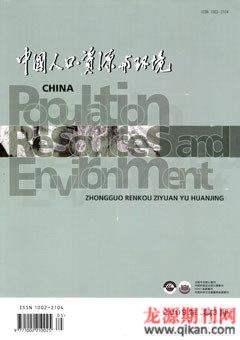论紧急状态下的个人环境权及其保障
李荣荣 郜凌云 沈钰婷
摘要个人环境权在宪政语境下应为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但这是毋庸置疑的。紧急状态为宪政的非正常状态。非常态下的基本人权理论应不同于常态。个人环境权应有所限制。但是,由紧急权力的自身属性所造就的环境权危机而导致的对个人环境的侵害,也应当得到救济。在紧急状态下。对于个人环境权的限制应当遵循行政应急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正补偿原则、监督与救济原则。在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救济亦不应等同于一般情形下的权利救济方式,这里至少包含了三种形式:正常秩序所排斥的私力救济方式;正常状态所喜好的ADR救济方式;包括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三大板块的公力救济方式。通过对国家紧急权的约束以及三大救济方式的协调,以期获得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与国家紧急权力的张力平衡。
关键词紧急状态;个人环境权;权利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60-06
在正常的宪政状态下,个人环境权能否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以及在遭到侵害时是否可以得到救济是我们在常态中所思考的问题。如果对此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紧急状态下,当一切权力和权利旨在以恢复国家至正常状态为目的时,个人环境权是否一样不可侵犯?笔者对此的回答是,个人环境权在非常态下是特殊情形下的基本人权,对它的保障应区别去常态。
1紧急状态下的个人环境权利危机
1.1个人环境权乃宪政国家之基本人权
1.1.1个人环境权的概念
个人环境权,即个人所享有的拥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在这里之所以将其称为个人环境权而非公民环境权,是因为公民是个政治概念,我们不应当将一项基本人权局限在政治领域,它应当具有普适性。
1.1.2个人环境权是基本人权
个人环境权可否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历来存在争论。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法理、人权属性还是实践角度出发,个人环境权都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来对待。
首先,个人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的理论依据。第一、这是人类生存、自由、平等、可持续发展、共存的要求。第二、自然伦理要求。第三、传统法学理论的不足,即传统民法理论对民事权利设计的欠缺、宪法对基本权利设定的不足、国际法对国家环境保护的不力。
其次,从人权属性来看,公民环境权也应作为一项宪法上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据人的自然属性,并基于人的社会价值要求,一切社会制度的设置及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与幸福,即是为了充分实现人权。保护环境,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创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保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最后,从实践角度出发,环境权正在从应然权利走向实体权利。从1960年原西德医生的起诉行为,到1992年《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附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公平的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个人环境权正逐渐走向实际层面。
1.2紧急状态对个人环境权的克减——危机之体现
1.2.1紧急状态的概念和特征
从广义上说,紧急状态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即,有权的国家机关在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以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公共事件等非常情况下,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依法以紧急命令的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暂时中止宪法或法律某些条款的全部或部分效力并强化行政权作用的法律制度。
紧急状态是宪政国家的非正常状态,同正常社会秩序相比,具体有以下特征:
第一、宪政秩序的突破。在紧急状态下,宪政秩序无法正常运转,宪政秩序失灵。无论是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模式还是现代的授权法模式,其宪政理念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即分权、制衡、民主都将在极大程度上被突破。
第二、公权力的集中与扩张。为了应付国家危机、挽救、维持国家,公权力必须高效行使,强调分权与制约的三权分立体制无法应对。因此,突破原有体制成为必须。另外,基本人权原则的不可侵犯性,在此时也显得苍白。常态下的基本人权并不再不可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通过正当程序,并且符合比例原则而且要给予事后救济。
第三、消极除碍的目的。紧急状态的目的,在于排除国家非正常状态下的危险,恢复国家至正常状态。紧急权力的行使应以此为目的,而非以增进福利、改造社会秩序等积极社会项目为目的。
第四、急迫性和短暂性。紧急状态的发动,乃是因非常态事故的发生,这种事故具有危机性和紧迫性,宪政秩序面临紧急危险已经或者即将无法维持,必须通过紧急状态制度加以恢复。但是这种状态,绝不能常态化。否则,紧急状态便失去其最高目标。无论是何种情形,一切国家权力皆应以保障民权、为民谋利为宗旨。在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的克减是必然的,如果使其常态化、永久化,则践踏人权的历史将重演。
1.2.2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的克减
“在政府与自由的永久争议上,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之事情时,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向其所认为的必要让步”。而在这种宪政维度的视角下,权利也应有所限制,这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更何况在危机下,权利更应有所限制。
紧急权力的扩张与集中,以及公权力高效性的要求,必然造成对公民部分权利的限制与干涉。它的正当性是有着伦理、道义、法理和宪政基础的。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回答是否应当全部不得侵犯。但是作为崇尚宪政的法治国家,必须为个人发展留有余地,至少是给个人生存所赖以必须的个人环境权留有空间。因此,就有必要区分个人环境权的克减地域和不可克减地域。而区分的理论基础也正在于个人环境权在紧急状态下的限制和保障。
可克减的个人环境权,是指在紧急状态下可以为紧急状态目的而让步的权利,这种权利根据紧急状态的种类和级别而有所差异。不可克减的个人环境权也就是不能为此种种类和级别的紧急状态目的而让步的权利。它们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在不同的国家,因为宪政法治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越为发达的国家,不可克减的个人环境权领域就越为宽泛,相反则越为狭窄。
2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限制的理念
紧急状态下紧急权力如何限制个人环境权是一个宪政问题。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紧急权的作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以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环境权。如果紧急权超越这些限制,紧急权的行为就是非法与不合理的,这也就为个人紧急权的救济提供依据。
2.1行政应急性原则
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治原则可以分解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应
急性原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以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重要补充。在常态下,主要由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发挥作用,而在危机时刻,行政应急性原则便要发挥作用。它要求,行政紧急权得以集中全社会力量为恢复国家秩序而服务。它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这种措施在宪法上又被称为“宪政独裁”。因此,必须将这种措施限定在应急性原则内,应急性原则应是紧急权行使的底线,否则,就有可能危及宪政的基础。
2.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称为“禁止过度”原则,是行政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奥托·迈耶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居于‘帝王条款,当不为过”。
该原则表明政府的侵害行为不得逾越宪法所容许的范围或特定目的,若有同等效用手段足供役使,应选择对人民自由权利侵害最小者之。它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方式。在紧急状态下,这种利益衡量更应有发挥余地。对个人环境权的侵犯同样应当进行符合比例原则的利益衡量,选择最有利于实现既使行政目标得以实现而又对个人环境权损害最小的行政应急方案。具体包含:
第一、足够重要的目标。该措施必须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才能成为无视个人环境权的理由。
第二、与目标的合理联系。该措施必须谨慎设计,以便实现有关的目标。它们不得是专断的、不公平的或建立在不合理的因素之上的。简单地说,它们必须是与目标合理联系的。
第三、最不激烈的手段。有关的法律应该尽可能少地损害个人环境权。
第四、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均衡。在为限制个人环境权的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和已确定有足够重要性的目标之间必须具有一种均衡。
2.3正当程序原则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在紧急状态下,紧急权力为紧急行为时,也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不能仅仅因为紧急状态而赋予其权力滥用的合法性。但这种正当程序应当是灵活的,而非固执死板的。否则,它将给紧急权力带来极大限制,影响其高效性,甚至造成毁灭性打击。限制个人环境权,应当事先公告或通知,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于那些因紧急而无法事前通知或宣告的,应在事后及时采取补救性程序措施,并给予其申诉抗辩的机会。
2.4公正补偿原则
所谓的公正补偿原则,也就是指在紧急权合法行使的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产生的公平补偿。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如同征收一样,应当给予公正合理的补偿。这是宪法上的基本原则。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侵犯个人环境权应当给与合理补偿,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力的规制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下对紧急权力的控制。
2.5监督与救济原则
所谓的监督与救济原则,是指公众对政府紧急权的行使有权予以监督,并且在紧急权给自身造成侵害时,有请求救济的机会。强调对紧急权的监督是因为:第一、防止权利滥用;第二、贯彻分权制衡理念的需要;第三、保护相对人人权的需要。而强调救济是因为:第一、紧急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侵害相对人的权益从而产生争议;第二、通过救济对紧急权的享有主体形成一种有力的监督。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7条规定:凡依法受到紧急处置措施羁束的人,可以要求撤销该项措施。
3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的保障
个人环境权在紧急状态下作为一项特殊的基本权利,存在有不可克减的地域,而对于可克减的地域也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并给予被克减者以合理公正的补偿。如果紧急权力侵犯了不可克减的地域或者违法的侵犯了可克减的地域的拥有者的合法权利,应当给予救济。在前者应当通过个人的紧急救济权来实现,后者则可以通过事后救济的办法去弥补。另外,按照个人环境权保障的方式,可以分为第一性的保护和第二性的保护:第一性的保护主要通过在相关立法中规定对个人环境权的规定来实现,紧急权应自觉遵守之;第二性的保护,则是在紧急权违反相关立法时对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前者是制度上的建构,涉及到在紧急状态下对紧急权的分配以及立法权的保留领域,因此这里主要对第二性保护方式进行阐释。它在理论上主要包括私力、ADR和公力救济三种模式。
3.1私力救济
个人环境权的私力救济,就是指个人为了保护自身合法的环境权,在遭受环境污染和破坏而情况紧急又不能及时请求公力救济或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的状况下,而采取对侵害者的人身或者致污设备等予以强制力迫使其停止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其正当性“是基于核心环境权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保证核心环境权得以实现的一种补救性权利。”
个人环境权的私力救济因侵权主体的不同应有所差别。在紧急状态下可分为两类:第一、普通主体侵权,即一般公民、企业对个人的环境权侵权行为,对这类权益救济应同于正常状态;第二、特殊主体侵权,即享有紧急权的主体的侵权,它又包括合法行使紧急权的侵权和违法行使紧急权的侵权,权力行使是否合法,个人所享有的私力救济权深度也有差别。
可以得到正常救济的第一类侵权无须特别关注,而对第二类侵权,则应当重点关注。首先,必须正确区分紧急权主体的侵权和紧急状态下的自然因素而导致的个人环境权的受损。紧急权的高效、集中性要求其全盘考虑,为更大利益而放弃较小利益,而个人环境权可能正包括其中,也就是可以克减的个人环境权。其次,对于紧急权的合法限制行为,即合比例原则的限制行为。在这类情形,公民当然不得享有自力救济权。最后,对于紧急权的非法限制行为,公民的自力救济权是可得的。关键在于这里的“非法”如何理解?毕竟不同与正常状态一切权力皆应有法律依据,在紧急状态下,紧急权集中大量立法和司法权,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第一,紧急权所颁布之临时决定是否称得上为权力依据而被称为临时立法?如果可以称得上是权力依据,那么,我们是否享有知情权?第二,紧急权立法后又由自己依照所立之法行使紧急权,这是否违背自然公正原则?
随着从传统自由法模式向现代授权法模式的转变,紧急权需要有宪法或者紧急状态法授权才能在紧急状态时期行使,而享有紧急权的多少自应与紧急状态的深度成正比。事实上为了应付危机,紧急权必须享有紧急立法权和紧急司法权,因此,自然公正原则在此的效力必须暂退二线;而且由于立法程序的紧急性在此显示为其非规范性。因此,如何衡量行政紧急权力是否违法,就有必要运用一些基本原则,即本文第二段所述之。如果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紧急权就是违法的,个人私力救济将得以行使。
3.2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3.2.1ADR的概念
ADR源于美国,通常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调解、仲裁、早期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