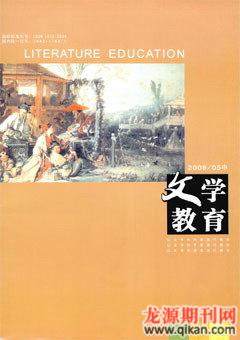苏轼与李清照词作风格之成因新解
赵兴燕
[摘要]苏轼词作品的豪放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的生命活动超越了现实生活的束缚,进入了无拘无束地自由放歌的境地:而李清照却没能实现这种超越,她的心灵始终被现实困扰着,通过词作这一文学形式,她倾诉着自己的哀叹,所以形成了婉约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词作风格;生命活动;自由;被困
在宋词的研究领域内。被保存下来的词作品通常被划分为两个流派,即“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是指那些在内容上抒写了广阔的社会人生,在基调上又具有昂扬向上精神的词作品;而婉约派是指那些抒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题材,又具有委婉细腻基调的词作品。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新的视野的开拓,学者们也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对宋代的词作品进行研究。张仲谋先生在《婉约与豪放词派新论》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豪放与婉约不是一般意义的流派,而是词的两大创作范式,即两种创作风格。他进一步指出:婉约作为词的基本风格之形容界定,正好适应了词的女性文学特质。和其它许多文学风格术语一样,婉约与豪放也是由人的风度气质的品藻鉴赏用语引入的。这正应了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的那句话,意思是说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作家个人的气质、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家对此早有论述:曹丕曾说过:“文以气为主”,气,即指气质个性,就是说文章应该显明地体现作家的个性气质。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这样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刘勰认为:创作风格的形成是由一个人的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还要经过“情性所铄”与“陶染所凝”的过程。由上文所述,我们不禁要深思的是:既然婉约与豪放是词的两种创作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又是由作家的才气与气质、个性所决定的,那么,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与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他们的才气与气质、个性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从才学方面来看,苏轼才智过人,二十二岁因科举中第而一时名满京城,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李清照作为一名闺阁中的才女,虽不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才智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时人王灼就曾这样评价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
其次,再从才气及情性方面来看,苏轼秉性直而不随,刚正不阿,曾因此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例证。还有一则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年轻时冒死所写的《谏买浙灯状》,熙宁二年,宋神宗因个人所好下令减价收买浙灯四千余盏,“尽数拘收,禁止私买”,命有司立即执行。苏轼得知情况后立即上疏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指百姓)口体必用之资。”苏轼作为朝廷命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社会中,竟取于上书批评皇帝的错误,其正直、不畏权势的品格显而易见。比他的行为更值得称道的是李清照,在出嫁从夫、在家从父的男权社会中,作为儿媳妇的她竟敢写诗批评官至尚书右丞的公公赵挺之,她以“炙手可热心可寒”的诗句批评赵挺之依附奸臣蔡京得势的错误行为。再者,李清照晚年,因受张汝舟“似锦之言”的蒙骗,为摆脱孤苦的生活境况而再婚。婚后不过百天,当她发现了张汝舟图财的丑恶真面目时,甘心受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讼告其夫,与之离异,并愤然写下“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这样的话,其不屈的叛逆个性同样彰显在我们面前,正如时人的评价:“易安佣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这样一来,值得我们探究的是:苏轼以浩然正气的个性特点理所当然的形成了“豪放”的创作风格,而李清照怎么就凭着一腔刚强的丈夫之气,却成了“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呢?
文学刨作归根到底是一种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作家通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外界的反应。缘此,我们应该从研究生命活动入手,来对李清照与苏轼词作风格的形成进行探讨。“人的存在方式显现为生存、实践、超越三种基本的活动样式。其中生存活动是人的基础存在,从根本上制约着其他生命活动形式;而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的生命的自觉性能,是人类存在活动的主导方式。”在实践活动的层面上,人确立自身为“自为”的主体,以改造对象世界为自己的目标。从一般意义上说,对象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这样,人这种“自为”的主体与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就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二分的态势。而对于文学家来说,与其生命的创作实践活动形成对峙的客体世界是人类社会,具体地说就是作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大部分文学家通过作品表现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个体生命对于社会生活体验的直接反映,李清照的创作就是这样的。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清照,少女时期过着优越而又比较宽松自由的家庭生活。这种幸福的生活使她的早期作品大都洋溢着快乐的体验。例如,我们熟知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警起一滩鸥鹭。”写得是她外出游玩,非要兴尽而归,虽然返回时已经很晚了,可心中毫无顾虑,这时,牵动她视线的却还是那“误入藕花深处”的船只在“争渡”之时,“警起一滩鸥鹭”的动人的景象。这是她早年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的生动体现;婚后的李清照,虽然与丈夫赵明诚感情深厚,但是丈夫宦游四方,有情人不能常相厮守的苦恼使她这一时期的作品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愁,不论是《一剪梅》中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还是《醉花阳》中的“莫道不消魂,廉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是对于这种相思之苦的倾诉。
晚年的李清照,经受了丈夫离世的打击。宋王朝南迁之后,背负着国破家亡之痛的她独自漂流异乡,过着孤苦的生活,孤苦的生活体验反映在她的作品中就凝成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的痛;“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的愁;还有“如今憔悴,但余双泪,一似黄梅雨”(《青玉案》)的苦。总之,李清照总是怀着真实的情感,以我手写我心。其词作品都是生活的风风雨雨作用于她那颗敏感的心灵而产生的心灵回响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来看苏轼的创作,苏轼的人生之路很曲折,一生在宦海的沉浮中跌翻了两大跟头。第一次是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经营救出狱,被贬到荒凉的黄州。从一个名满京城的才子,即而成为朝廷命官,可谓人生得意。然而随即却又要面对被杀头的危险。人生的起落之大,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可经受了这一切的苏轼,没有悲观、消沉。在谪居黄州时,于
宋神宗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这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生活的风风雨雨的袭击中,坚强的苏轼正拿着竹杖,穿着芒鞋,披着蓑衣,无所畏惧地吟啸前行。第二次是哲宗皇帝亲政后,为打击“旧党”,苏轼被列入惩处之列,被朝廷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荒远的岭南。在条件非常艰苦的蛮荒之地,苏轼却过着:“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悠然生活,也体会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快乐。我们看到:不管外界的逼迫多么严酷;不论生活中的风雨的袭击多么犀利。苏轼那颗坚强的心始终没有象李清照那样被困住,他的心始终在自由地跳动,他的心灵始终在自由地放歌。
苏轼与李清照都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然而,对于生活的磨难,两位个性、气质相似的作家却发出了不同的心灵回响。“生存与实践构成了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但还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部。在这两种活动方式之外,人更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它摆脱了一切现实的干碍,直奔那最高的自由境界,故而最能显示生命对自由的向往。”;“生命活动进入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才算达到了自我圆成的境地。”以此观点,我们认识到:苏轼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是因为他的生命活动进入了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层面,他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圆成。所以,不论面对多么困苦的处境,他的心灵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的放歌。而李清照却没能够达到这样的生命境界,她的心始终被现实生活困扰着,虽然具有大丈夫的倜傥个性,也不缺乏过人的才学,但是,无法超越现实的精神活动,使她不能够昂首挺胸的自由高歌,她的心灵始终带着枷锁,她只能深情地诉说。
针对上文的论述,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认识到:苏轼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达到自由的境界,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生命观,即身与物化。他在《赤壁赋》中这样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他把自己的生命进程置于自然万物的变化流行之中,以与万物同生共亡的观点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终极的寄托。而李清照却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归宿,她始终很茫然。她的《渔家傲》就说明了这一点,“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警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渴望实现生命价值的她在梦中来到了天帝的居所,她告诉天帝自己很有才学,却日暮途远,没有出路。虽然表示自己正要像鹏鸟那样高飞远举,但是,也仅仅是幻想而已。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没有给李清照留出一片施展才华的自由天地,被拘囿的心灵只能无奈地诉说着生命流失的悲苦。诸葛忆兵先生在《李清照个性成因及其表现》一文中这样说:“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之下,个性泯灭,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强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李清照是幸运的。”但我们从生命活动的角度来看,留芳青史的李清照,其生命的旅程又是满载着痛苦与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