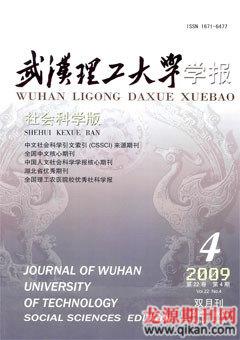社会资本培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 颖 黎正稳
摘要:虽然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已通过社会学家的论述尤其是现实生活得到了证实,但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想到它与高等教育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能始终坚持教育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本理念,并知道社会资本很大程度需要通过“投资”才能具获,那么,就会发现,如同德育、智育、体育一样,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培育亦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社会资本;培育;高等教育
中国分类号:G40-0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18
高等教育当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旨归,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但细察时下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教学情况,却会发现它们均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没能将社会资本的培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他们没能对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着意指导和有效训练,致使后者中不少人在毕业后应对相关问题时,长时期处于被动甚至困窘的状况之中,需要花大气力调整才能缓解这种不利的局面。
一、社会资本理论:一种可用于诠释高等教育的理论框架
在稍具社会学知识的人那里,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当然不会陌生。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厄迪对这一最早由奥地利学者庞巴维克提出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将它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不少学者也都对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中最突出者如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林南等还提出了系统的理论。由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任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之间结成的一种网络状联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共识性规范和信任关系。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的协调机制,因此,在不少方面都能生发效用。比如,在经济方面,它“是促进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提高其它资本运营效率的关键因素”;在政治方面,它是“社会信任的来源和‘公民社会的黏合剂”,即“产生社会自治的基本条件”;至于在社会方面,则既是“个人能力的储备”,亦是“一个组织或社会凝聚力的基本来源”,等等。也正是因此,尽管迄今仍有人对它的存在及作用表示怀疑,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它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是能够成立的。它实际上是人们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对一个影响个人、社会发展的要素的认识和概括。
从学者们开始对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起,时间已过去了20余年。大量事实证明,这一资本确实有助于其拥有者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各种效益,因此,它不仅被他们经常使用,而且被学者们作为一种学术框架,用以阐释多种社会现象。然而,就在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功用非常看好,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当代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课题的时候,一个问题同时也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这一理论与高等教育的联系,人们一直没能看到多少这方面的讨论和见解,从而无法知道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应对。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将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确乎有“对这一概念超越社会学学科界限不加限制的任意使用”,从而出现“社会资本的泛化”的嫌疑呢?显然,事实决非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就摆在人们面前: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而大学生亦是社会成员,由是在任一社会成员那里都存在的社会资本问题在他们那里也同样存在,尤其是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培育才能具获,而恰恰使大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来就是高等教育的宗旨所在。
前已说到,对于社会资本与人们的关系,不少社会学家进行过论述。在他们看来,由于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对每一个人来说,只要他与其它人有关系,他就自然拥有这种很大程度上与“关系”同义的资本。也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布厄迪在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定义之后,紧跟着又指出,“它与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关”。波特斯亦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也许,在某些熟知社会资本理论的人看来,这样的表述太寻常不过了,但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这一点对于大学生以及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学生那里,也有一个社会资本的问题。大学生同其他人一样,亦是一个群体的成员,作为个体,他们和其他人有着确定无疑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逻辑,决定了他们拥有社会资本,拥有这种“嵌入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和动员的资源”。
然而,之所以认定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除了大学生同其他人一样既需要也一定程度地拥有这种资本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种资本虽然因关系而产生,却需要着意培育。否则,至少其存量难称丰厚,对其拥有者来说不能生发出应有的效用。在谈到这一资本是如何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时候,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要么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它需要培育,要么是通过自己的论述使读者获得这样的感觉。如林南就认为这种资本的获得需要行为主体“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布厄迪则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联系,而这就等于告诉人们,加入不同的社会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从而建立更多的组织网络,是增加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当然,无论是林南还是布厄迪,都只谈到了社会资本的具获需要培育,而并没有涉及到大学生及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讲培育就有一个途径和方法的问题,而对以提高素质为学习目的的大学生来说,所有涉及途径和方法的问题都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高等教育来解决的。对高等教育的诠释来讲,社会资本理论确乎是一个有效的学术框架。经由对它的解读,人们得以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的,能为自己带来收益的工具和手段;也正是经由它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人们得以知道,教会大学生如何具获社会资本,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方面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则所谓大学生应通过高等教育得到全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句套话。
二、匮乏及培育的缺位: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当下状况
一种理论的成立,除了在逻辑上能自洽外,更重要的是能得到事实的证明。社会资本理论之所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和信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效用不断为后者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和体验到。诸如:它有利于降低学校失学率;有助于解决社会排外;有利于提供健康利益;有利于实现民主的良好运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有利于改善经济角色和建立良好的信用
社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等等。但凡对这一资本有所了解的人,都无不在如何具获它上下工夫。即便是那些对此没有多少自觉认识的社会成员,亦会从经验出发,通过各种方式,来有意识地积累这种资本,以获取各种利益。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偏偏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相对一般社会成员而言综合素质要高得多的大学生却表现出了一种不容乐观的状况。对此,人们甚至无须做深入地了解,只要看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会有所发现。比如,他们相与交往的人员基本上是自己的侪辈,而与其它社会群体(阶层)则很少有实质性的互动,这样一来,便使得他们活动的圈子实际上非常狭小。这一点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就是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仅同质性很高,而且规模很小,从而使得杰克逊所谓三种“隔离”(不同生产线上的地理隔离,不同阶层的空间隔离,休闲上的社会隔离)在他们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又比如,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始终以讨论网为主要构成,而在学者眼中对资源的吸纳最为重要的支持网在他们一直难以形成;再加上他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既不是工具性(以经常的明确的交换为基础)的也不是友谊性(以长久亲密关系,相互承诺与象征交换为基础)的,而是指向并不那么明确,只能勉强归为混合性的,这样,便导致了他们很难与同学以外的人建立起共识性规范,致使这一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若以存量计,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非常有限。再比如他们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人信任,因为它们的建立仍主要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为纽带,那些更多指向和有利于系统信任形成的要素如业缘、志缘、趣缘等并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也正是因此,他们对他人的信任便没能因为生活在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而摆脱某些学者所说的那种“工具性差序格局”,表现出制度化的态势。
总之,在大学生那里,其社会资本的拥有完全可以“匮乏”概括之。这样一来,便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素质构成,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的适应。不过,以上所述虽是大学生在社会资本问题上令人遗憾的所在,却并非是最值堪忧的地方。相比之下,真正令人难以看好的还是高校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因为大学生毕竟还在学习,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育来使社会资本匮乏的状况得到改善。问题在于各个高校不仅没有对此采取多少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就是相关意识亦非常欠缺。
毋庸讳言,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匮乏是有着多种原因的。比如他们身处大学校园之中,而后者在今天仍很大程度是一“象牙塔”,这种与社会保有相当距离的空间位置,使得他们很难去与其它社会成员进行广泛的群际交往,从而实现他所谈到的促进自身社会网络的建构,为成为主导性角色创造条件。又比如他们一般都在20岁左右,而这一年龄段对社会资本的具获来说无疑是非常微妙的。因为人们选择相同年龄段的人作为朋友是随机选择的四倍,而恰恰20岁和60岁是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和退出点,这种年龄结构中的“断层”位置,使得超出这个范围的朋友选择变得相当不可靠。再比如有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证实,尽管“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和社会资本”,培养人情是建立和维持一种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拉关系和攀交情又多会引起沉重的社会投资和负担。而一旦人们据此去观察大学生,显然能对他们缺乏社会资本有所理解。因为他们尚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不可能承担因拉关系和攀交情所导致的沉重的社会投资和负担。不过,人们又不能不承认,这当中,还有另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等学校没有将社会资本的培育作为教育教学的一项内容。须知遍察国内所有高校,人们几乎举陈不出有哪一所曾为此开设过相关的课程,或进行过专门的训练,而恰恰在大学生各种素质的形成和提高的问题上,诚如世所公认的那样,以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为主要工作手段的高等学校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的,是应通过各种具体的教育教学措施来落实的。换言之,尽管时下所有的高校都知道应使自己的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德、智、体、美、劳等各种维度,却就是没有意识到在大学生的素质构成中还有社会资本一说,更不曾为他们最大限度地拥有这种资本采取过任何专门而又具体的措施,结果,便使得后者不仅非常缺乏这种资本,而且对这种资本的重要性及如何具获亦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就大学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而言,前者非常缺乏后者固然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而各高等学校的工作缺位更是一严重的问题。如果它们在这方面一直有所认识,并有所举措,则大学生断不会因欠缺这种资本而在求职、流动等问题上常常处于被动以至困窘的状态,更不会事到临头(如毕业求职)时方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补救的重大缺陷。
三、社会资本培育:高校教育教学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确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大学生非常缺乏这种资本,而且这种缺乏与几乎所有的高校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举措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无疑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对大学生进行有关社会资本知识的教学和具获这种资本的能力的训练,是当代中国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各高校只有在这方面深入探索,提高认识,加强规划,具体落实,方能使现存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并使自己真正承担起全面培养新一代大学生的职责。
对此有人肯定会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在现实生活中,各高校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它们很少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在时下的大学校园中,就存在着在校方(具体来说又主要是学生处、团委等)指导下的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它们一方面是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增进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平台,但同时是学生编织自己与他人的网络关系,培育自己的社会资本的场所。特别是有不少学生并不是只隶属于一个社团,而是同时参加多种自组织活动,如此一来,便相当程度地使自己的网络关系具获了“非剩余”的性质,或者说使自己在角色关系种类这一问题上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尽管他们的这种表现与伯特所说的占有“结构洞”还不是一回事,但至少能导致诸多“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建立,获得“信息桥”的效用。此外,还有不少从内容与形式上讲与此有所不同的活动,也都可归为在校方的指导、组织下进行的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如学生们在教学基地开展的实习活动,以及已经成为一种制度的“三下乡”活动等等。因为按照劳曼、布劳、费切尔等提出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选择理论”来解释,它们都属于群际交往的行为,而这对于由人口的组成成分和分布状态产生的结构性社会(社区)限制无疑是一种突破,至少,它们可以提高位置差异较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程度,使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互动能够实现。
应当承认,在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具获上,时下各高校的某些举措是生发了一些作用。但问题是,这些作用究竟有多大,尤其是举措者的自觉意
识到底如何,尚不可知。比如以校园社团活动来说,尽管参与者都能形成自己的网络关系,与同处一个网络中的人建立起共识性规范和信任关系,在吸纳资源,获取助力的问题上较社团外的同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些都发生在校园这一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一旦步入社会,就会随着社团成员彼此间的天各一方,渐行渐远而逐渐衰减,直至最终不复存在,一如奥斯特洛姆所说的那样,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尤应注意的是,在社团活动、教学实习和“三下乡”活动中,组织者要么是着眼于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要么是服务于人力资本的增进,而很少将具获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目的,更不曾将此种意识通过具体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传达给学生,结果便使得后者很难将此作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去自觉考量和追求,致使他们在社会资本的拥有上是那样乏善可陈,而且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补救。
某些熟知社会学理论的人对此又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强调高校在学生具获社会资本的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对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践行,而时下不少研究者对于这一理论恰恰持有疑义。
的确,对于学生能否知晓有关社会资本的知识,以及如何运用这种知识去使自己获得这一资本,高等学校一旦将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职责所在,并且付诸行动,便证明他们确实在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那样行动,即:第一,相信个体(这里自然是指大学生)是有目的的行动者;第二,相信行动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至于说到理性选择理论,也确乎有一些有待不断完善的地方,如怎么看待人类行为中那些非理性和反理性的行为,怎么看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规范和习俗的指引,等等。至少,它要对大多数社会学家乐于相信个人行为全部依社会力量而定这一点做出合理的解释,使自己不致在“经济学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做出某些选择,而社会学关心的是人们为什么不做出某些选择”这样的定义面前感到为难和乏力。只是,在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同时,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个人按照一种“投入一产出”的精于计算的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过程,确乎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现象。因为大量事实证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为等,归根结底是个体追求最大功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后理性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作为以健全受教育者的理性为旨归之一的高校就没有理由对有助于大学生之功利追求的社会资本置而不顾。如果它们拒绝承认这一点,则马克思一再强调且一直被奉为圭臬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的观点,就很大程度会停留在一般宣传上。至于教育学家们孜孜以求地把现实生活同已确立的理想和价值联系起来的目标,亦很难得到实现。
关于社会资本培育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的理由,人们还可举陈许多。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曾指出:“在生产社会资本方面,政府可能拥有最强能力的则是教育。教育制度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还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他认为,“不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这样”。
总之,对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社会资本的培育无论如何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有关方面只有从这一点出发,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方能帮助学生具获这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从而使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后能更好地应对各种(特别是事涉资源吸纳)问题,让高等教育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体现出应有的效用。
[参考文献]
[1]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2]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5.
[3]Bourdieu,Pierre.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M]//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C. T.:Greenwood Press, 1986:241-258.
[4]Portes,Alejandro.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 gration[M]. New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2-3,1995.
[5]Lin Na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1999,22(1):28-51
[6]Lin Nan.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M]//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Sage,1982:131-145.
[7]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M]//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5-76.
[8]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9]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J].新华文摘,2003(7):159-160.
[10]Duesenberry J. Commnet in Universities 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Developed.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ty Press, 1960.
[11]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71.
[12]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新华文摘,2003(7):165.
(责任编辑曾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