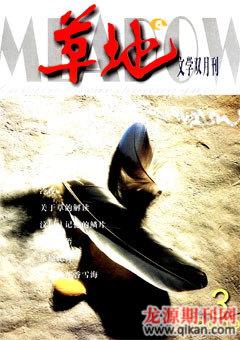墙上的阿公
白 丁
母亲坐在床头打毛线,昏暗的屋子里我只听见那细细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好像一种温暖的水流在心间。母亲说阿公如何如何和蔼可亲,如何如何喜欢我,还给我取了这样一个特殊而有意味的名字。我蹲在地上一边玩毛线团,一边愣愣地听着,却想不起阿公究竟长什么样子。那时我四岁,正是懵懂无知的年纪。阿公已经去世两年了,母亲总是在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向我倾诉往事,絮絮叨叨,语气里洋溢着对阿公的哀思。我说,妈妈,阿公去哪里了,阿公好久没来看我了吗?母亲就捉住我的小手往墙上一指,便看见衣柜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相框。框中的老人头发稀疏,瘦瘦长长的脸,刻满岁月无情的沧桑,嘴角隐约的弧度,眉宇间的开阔却透出一种坚韧与睿智,尤其是那双清澈的眼睛使我心中一凛。母亲在背后推我,说,该给阿公磕个头了。于是我有模有样地屈膝下去,额头咚咚咚地响,一个,两个,三个。我整理膝盖,抬起头,看见阿公的嘴角露出了微笑。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眉毛上,闪烁晶莹,好像弯曲了。母亲说,阿公会保佑你的。
十岁的时候,我全身长满了一种湿疹,大如指甲,奇痒难耐,用手一抓,血肉模糊。母亲见此情景,一时手足无措,哇的一声吓哭了。父亲冒着烈日走了十几里地,找到一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老中医却连连摇头,说他行医这么久也没见到过这种怪病。父母无奈,只好用茱萸熬成浓黑的汁水给我喝,药水下肚,一种锐利的疼痛穿肠而过,贯达全身。冷汗水流出来了,我觉得我像棉花一样轻,我渐渐听不见母亲的呐喊了。我觉得我就要死了。恍恍惚惚我看见一片蔚蓝的天空,天空上面漂浮着白云,白云后面有歌声。那是阿公坐在村头无垠的油菜花地里吹着笛子,蝴蝶飞绕着阿公白白的长须,清风吹起他的衣襟,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阿公向我微笑,我似乎遥远地听见他呼唤着我的小名。我应了一声“阿公”便飞跑过去……,一下我就醒了。母亲坐在床头眼睛红红的,她说,你都昏睡三天了,话没讲完便泪如雨下。我安慰母亲,翻起身来吃完了桌上的饭菜。第二天,背上的湿疹变少,变小,慢慢消失。母亲说,是你阿公救了你。
每到阿公生日、祭日或清明,天尚未亮,母亲便到床边来叫醒我。把里屋打扫干净,点上几炷香,燃起几根蜡烛,烧上数叠纸钱。这是对逝者的馈赠与祝福,烛光与青烟带着我们的思念抵达另外一个世界,也惟有此时我才觉得我们是那样的血脉相连。整理洁净的新衣,跪下,郑重其事地磕三个头。石板地面是冰凉的,宽广的,好多次额头触地的那一瞬我都以为那是阿公的额头。祖孙触额,这是多么美好。只是我连阿公最初的记忆也没有,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悲凉,我的身子打了一下闪。母亲把阿公的相框从墙上摘下来,用湿布擦掉上面的浮尘,蜘蛛网,污垢。然后卸掉螺丝,把相框里面也擦得干干净净。相框被挂上去,墙上的阿公在我的眼前变得清晰起来,触手可及。我再次下跪,磕头,石板地面立刻变得温暖起来。那确实是阿公的额头。
十七岁的那年,我考上了大学,要离开乡村到远方读书。临走的那天,我到镇上借了一只相机,把阿公的照片拍下来,书页大小,装在信封里。我想阿公与我是不会相离开的,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与我相连,思念相连。阿公永远佑护着我。母亲给阿公献上一只烤鸡,在香气氤氲之中,我又跪下去磕头,额头触到地板的那一瞬泪水滴落,不能遏制。抬头,看见墙上的阿公水汪汪的眼睛。他也是泪眼朦胧了。
责任编辑:杨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