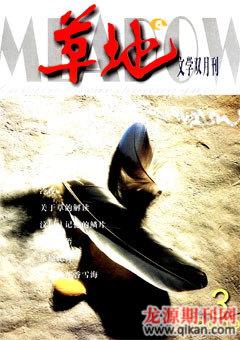关于草的解读
冯 源
在已有知识构建的认知系统和理性界面里,我以为草是整个植物世界里最平凡又最为弱小的一族:色彩是简索而单质的,身躯是稚弱而低矮的,经络是纤细而易折的,生命是低调而短促的,魂灵是卑微而柔软的。草的这些生命本在特质和原生态表述不得不使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种稍有硬度的物体都可以随意封闭它们向上生长的空间,任何一场有力度的大雨就能轻而易举地毁掉它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何一股寒冷的秋风便足以使它们鲜嫩翠绿的色彩消失殆尽。然而,震后初春那几株顽强挺立身躯的小草和昭示的生命内蕴使我对它们的美学描写魂灵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拐弯,更召唤起我对它们进行重新解读的欲念。
一
那条用水泥铺成的不足两米宽的蹊径,每天都要从它的上面经过,这就好像每天要重复做的那些事情一样,对它的感知领受和熟稔程度已经近乎于模式化了。或许是铺的时间太过于长久,水泥本身的质量根本没有达标,接纳的风风雨雨难以计数,再兼缺乏应有的修缮和养护。蹊径表面上块块的沙化,片片的脱落,微微的凸凹比比皆是,显得很有些破碎感,仿佛一张历经了一系列寒彻骨髓的风雪的猛烈拷打和一桩桩悲凉世事的剧烈震荡而皲裂得非常严重的苍老面孔。蹊径两侧生长着高入云天的松柏、白杨、香樟和茂密蒇蕤的修竹,以及一丛丛叫不出名儿的低矮的灌木,它们年年月月有如亲人般的生活在一起,和谐共融有如一家,同心协力抗击风雨,又彼此提携,相与攀援,互为映照,构造了一条绵长起伏的绿色走廊。站在山顶上眺望,从那条清流边逐级而上的蹊径在游弋的晨雾里犹如一条银灰色的长龙在绿廊中迤逦地穿行,依山而上,渐行渐远,愈高愈攀,欲意抵达九霄云外的神秘天宫。
较之于高大伟岸的树木,幽眇回绕的蹊径显得实在是有些细腻与柔婉、平实与沉静,没有一星半点儿张扬的神色,这就好像一个始终都保持着低调生活的沉默的人,所以每天那么多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过路人,很少在它的上面流连与眷顾,总是匆匆忙忙,来去如风,即或偶尔有一个人慢步缓行从它上面经过,也都是昂首挺胸,眼光一直瞄着高处,自然就很难得有闲情逸致去俯身亲近和怜爱从它身躯里生长出的那些绿叶小草。的的确确,在生活已经完全以物态化标准来衡量人的存在价值的时代,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地在经济创富的道路上竞赛攀比,不分昼夜地在富营养的时尚怀抱里尽情欢歌。置身于这样的现实生活,人是很难在情思的土壤上生长出“草根意识”的,更不要说在内心构造稳固健硕的“草根情结”。
正是在这样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角落里,那几株小草在震后的第一个春天突然闯入我的眼帘,并一直牢牢镶嵌在我记忆的心壁上。那几株小草零零散散地静立于蹊径之上,有的是从水泥路面细细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有的则是在一小撮泥土上长着,还有的竟是站在一颗极小的土粒上,一个个都睁着眼睛谛视世界,在柔软中蕴些许坚强,在细腻中藏几分真率。粗略地看上去,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皆是用柔软细长的根须努力抓着土,有两株草的根须大部分裸露在外面,只用根须那细细的尖抓着土的表面,晨风拂来,它们就有些摇摇晃晃,颤动的身体有如在呻吟一样,但顽强执着地根须一直牢牢地抓着大地,始终没有让它们的身躯倒下。风过后,小草们重新站直身躯,静静地伫立着,满含青绿的安详、眼神的柔和、性情的温婉、生命的顽强,与水泥路的灰白、冷漠、生硬、僵直形成很大反差。正是小草们的柔软细弱的根须的生命力显和一脸自然淡定、与世无争的神情,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触动。这样的生存方式要耗费它们多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呢?人是很难想象和精确估算的,因为人是没有根的,没有根的人自然很难理喻有根的生命的奇异力量所在。
因为正是初春时节的清晨,小草们都吮吸了一整夜的天地甘霖,个个清粼粼水汪汪的,仿佛几位绿妆倩然的处子,又像几个刚刚晨浴了的美人,饱几分楚楚动人的清雅,含些许撩人心绪的妩媚。或许是吸收了充足的甘霖,它们小小的身躯上浸出了些许大大小小如水沫般的露珠,这些露珠要么静静地伫立在叶面上,要么非常安恬的卧于枝叶的结合处,有的则小精灵般悬垂在叶尖上,仿佛一粒粒清纯透明的光子、一个个幽趣曼妙的细节。那些在草叶上慢慢移动和从草尖上滴落的水珠,则更像是一个个轻吟曼唱的音符、一曲曲错落有致的韵律。整个世界仿佛因为这些小草的存在而一下子平添了许多精美的章节、美妙的音乐、意蕴的清新、生命的灵动。在慢慢升起的春阳的照耀下,小草身上的那些露珠开始越变越小,以至彻底消散,小草有如卸下了重负,愈发彰显出绿意昂然的生命朝气。几株稚嫩的小草所创造出的如此灵妙鲜活的生命世界,非常容易触动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柔软也最敏感的神经,令人顿生心旷神怡的审美感怀而急遽扩展思想的空间:几株小小的草居然个个都有如此尖锐有力的根须,居然都蕴蓄着穿越厚实泥土的精神力;一株小小的草就建造了一个微型的世界,令人在瞬间寻找到人类与大自然链接的神秘因子,生发出对浩瀚宇宙的诸多顿悟。
大凡生长在平原、盆地、丘陵之类肥沃土地上的小草,皆不免有其生命较为脆弱的一面,眼前的这几株小草自然不能例外。或许是要用尽自己最大的生命力和生命意志才能牢牢抓住自己存活的土地,才能穿破水泥路坚硬的阻挡,它们小小的柔弱的身躯上已经明显地带着几许伤痕,即便是承载那几片稚嫩细长的绿叶的重量似乎都有些力不从心,它们身上的那些叶片也就有些东倒西歪的,或是在腰部折断,在越来越强烈的日光照射下一个个无不显露出十分的懒散和慵倦。这样的情景不由得使人深深地眷顾那些一直在高原上生活的小草。
二
那是一个秋意相当浓深的时令,我们一行几个文朋诗友驾车行驶在川西高原上,车窗外古人绘声绘色描画出的水是眼波横、山如眉峰聚、青松掩落晖、白云竞空谷等诸如此类的情景,同高原上那些自然天成的画境相比真可谓相形见绌。在这里,巍峨的高山与绵延的山峦挥洒出轮廓分明而浪漫迤逦的五线谱,幽深的峡谷与千仞的绝壁雕刻出大自然的邃密意境与生命坚挺,参天的古木与缤纷的落叶谱写出悠长的光阴和斑斓的色彩,翱翔的雄鹰与低飞的鸟儿吟唱出雄壮的音律和轻灵的歌词,激越的河水与飞流的瀑布协奏出水的乐章和山的心声,它们有如大师精心剪辑过的电影镜头一幕幕地走过,又像画圣着力描绘的一幅幅泼墨山水在缓缓流动,其线条、色彩、细节、语言、图式、声音共构的画镜不是江南远胜江南。
因为走的是从平武、经水晶、到黄龙的那条基本废弃的老路,路基全由原汁原味的黄泥土或是零零碎碎的石块儿筑成的,路面的凹凸不平自不待言,大部分路段皆处在高山与峡谷之间。经过夏天大雨的疯狂肆虐,不间断的有坍塌的山体或滚落的巨石挤占逼仄,道路狭窄得近乎于羊肠小道,汽车从上面经过,同一边的两个车轮有三分
之一都是悬在空中的;有的路段则因为过量雨水的长时浸透发生大面积的沉降,路面是用河里的卵石临时铺成的,再兼坡度又非常大,汽车在上面行驶简直就是一条蜗牛在爬行,有时甚至要经过来回几次的猛烈冲锋才能驶上去。每每此时,我们都只能下车小心翼翼地跟在车后面步行,或者是用力推着汽车行走。正是在这样的行程间隙里,我偶然看见了那些身形各异、姿态万千的高原草。
或许是土质结构的太过于坚固,或者是一直都没有种过庄稼而根本无人问津,抑或是平均海拔很高、气温长年偏低、氧气较为稀薄、风力十分强劲,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寂寂生活着的高原草,较之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平原草、丘陵草、盆地草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茎部明显的要结实粗壮许多,叶子更有厚度与宽度,根系更为繁茂发达而充满硬气,它们的身躯通常都不是很高,只有生长在河畔溪边的才略微高一些。因为是深秋时节,地势不同,高原草的色泽也不尽相同,但润泽的黄色却是它们的共性。但这些高原草所昭示的仍然不过是一种常态化的生存意义,尚难以使人赋予它们更为深切的关注倾情的爱怜无限的眷顾,而那些栖息在古木上、直立于绝壁间、生长在巨石缝、存活于湍流中的高原草却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内心震撼和审美冲击。在我们步行经过的一个绝壁上,一株高原草就直立于绝壁间,它的那些稍显细小的根几乎裸露在空中,只有主根深入在绝壁的缝隙里,几乎与绝壁构成直角,绝壁已不是泥土式的构造,全是坚硬的石块儿,植根于这样的坚硬中需要多么大的生命力和坚强意志呢?有风从深涧中轻轻拂来,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它的一丝寒意,那株高原草也仅仅是轻微的摇曳了几下,风过后,又一如既往地在绝壁上挺立出坚强的生命气概。这株高原草尚且如此,那些栖息于古木上、生长在巨石缝、存活于湍流中的高原草更不难想象。
从有着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风景区出来,依托着陡峭险峻的公路缓慢地曲绕而上,一眼望去,扑满灰尘的道路两旁,业已有些秃顶的山峦上,陡峻奇险的长长斜坡里,到处都生长一丛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高原草。或许是因为海拔皆在三千米之上,也或许是土壤更为贫瘠的缘故,那些高原草一律呈现出古黄铜色,都紧紧地贴着十分干燥的地表,叶子都仿佛失水了一样,叶面上的经络苍黄而偏白,茎部的支撑力已经非常分明的衰减了许多,身躯也似乎更显得矮墩墩的。汽车抵达山顶时将近黄昏,一道道金色的霞光从巨大的乌云的缝隙中穿越而出,犹如一盏盏光力十足的远程探照灯,把远方起伏绵延、峰峦叠嶂的高原照耀得脉络清晰、轮廓分明,更彰显出气象的磅礴、山河的壮美、意境的深邃。我们都被这奇异的高原黄昏景象迷住了,鱼贯而出,极尽目力眺望。正在我们都沉醉于这幅极写高原大观气象的画境而浮想联翩时,突然飘来的巨大的乌云覆盖了我们头顶的天空,纷纷扬扬的雪霰开始飘落,接着是一颗颗玻璃球大小的冰雹砸下来,大地随即被处置于一片迷蒙烟雾和一连串沉闷声响的肆虐中。在我们纷纷快速地钻进车里躲避时,那些身躯弱小的高原草却只能寸步不离毫无声息地承接着冰雹的猛烈砸击。坐在车里听着冰雹击打车顶的脆响,我们的眼神都有些发愣,更显露出些许忧虑或担心:在这人际罕至的高原上会不会出现诸如大雪封冻之类的意外?有人已经在思考解困的办法,其他人则保持着沉默或各怀心事,至于车窗外的那些高原草该用怎样的坚强意志和坚韧精神来抗击如许猛烈而沉重的砸击,我们都根本没有提及。
一路上上下下的回绕,全程颠颠簸簸的行驶,夜较深的时候我们才抵达一个叫元坝的小镇,躺在那间散发出淡淡松树香的小木屋里休憩,怎么都难以入睡,脑海里全是白天冰雹猛烈砸击高原草的场面或细节。那些已经被砸击得伤痕累累的高原草还能侥幸存活吗?正在我静静地思量之际,突然有人在外面高喊:快出来看啊。我慌忙穿上衣裤出来,这时一道巨大的闪电从天而降,远处的红军纪念碑刹那间通体放光,且发出一连串哧哧哧的声响。在人们的一片惊讶声中,我分明地感到:那座早已成为高原一部分的红军纪念碑就是一株巨型的高原草,它所发出的光芒和高高矗立的英姿,不就是高原草灵魂的闪烁、英姿的矗立!
三
稍有世界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近代美国有一位叫惠特曼的伟大诗人,都知道他曾出版过一本誉满世界的诗集《草叶集》。在这本诗集里,诗人放声吟唱着:“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我邀了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闲游,/我俯身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独自在遥远的荒山野外田猎,/漫游而惊奇于我的轻快和昂扬,/在天晚时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烧起一把火,烤熟了刚猎获到的野味,/我酣睡在集拢来的叶子上,我的狗和枪躺在我的身旁……”虽然诗人在他诗歌里所描写的草,已经是一种非常诗意化的存在而极富强烈的象征意味,但这样的象征意味产生的原动力又莫不与大自然中的草的本象紧密相关。
不独乎惠特曼,只要你静下心来阅读,阅读得越来越广泛深入,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古今中外的不少诗歌大师都曾或多或少地描写过草,尤其是那些终其一生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游历、感知、领受、悟会、冥想的文学名流,草更成为了他们作品意蕴系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他们对草的如此描绘和反复吟唱仿佛携带了巨大的穿透力和隐蓄的震撼力,从悠远深邃的历史时空向我们走来,一直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改变着人们对草的认知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大家名流专注于对草的爱怜,挥毫于对草的描写,钟情于对草的歌吟,这可能不仅仅是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或审美意象系统的构造问题,更重要的尚在于他们都有着对人类社会对大自然予以终极关怀的思想、情怀、魂灵。在这样的精神关怀下,那些只有生活形态意义而没有理论形态意义的草被精神形态沉淀为一种对人类生活有着重要启悟意义的象征,而富有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文化意义,并且长久的珍藏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处。
但在我们生存的当下,披着迷人外套的功利主义日益强化着人类贪欲的合理性,急遽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渐渐让人们放弃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虔诚之心,惟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人愈加远离了同情和仁爱,威势逼人的权力至上主义又使得局部的上层文化遮蔽了真理的天空。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势下,文学与自然与生态的关系日益疏离,越来越缺少与自然与生态的真心对话和真情交流,文学话语在面对自然时也越来越缺少敏感,越来越陌生和苍白,越来越不能抵达大自然的怀抱,这一切都在表明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已经正在从文学的精神领地中悄然退却。草,或者说草背后处于隐蔽状态的那些深刻性的东西也一一从当下的很多作品中离散消失,即或是偶尔有些许对草的描写和吟咏,但这种笔下的草已经没有精神形态的长时积淀与深度过滤,已经远离了人文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