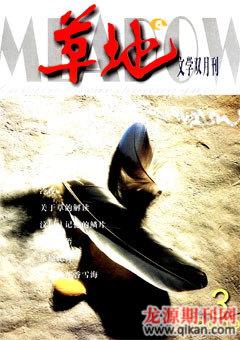冷夜
文晓东
我躲在被窝里大气都不敢出,父亲的吼声太大了,隔着棉被也能让我发抖。除了父亲的吼声,我还听见母亲的哭声。父亲的吼声像雷,母亲的哭泣声像雨,一阵接一阵,没完没了……
二十多年后的某个深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一个孩子的呼声缠住我不放,使我不得不忆起这个似曾相识的夜晚。
有一会儿,父亲没吼了,母亲的哭声也渐渐弱了,我偷偷用手指将棉被撑开一丝微缝向外窥视。我没看见父亲,也许他已经走了。母亲披头散发,衣着不整,她什么都不顾了,只顾哭,哭得泪雨滂沱。我准备鼓起勇气将头从被窝里探出来安慰母亲两句,喊她别再哭了。父亲不知从何处一下子又冒了出来,他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把揪起母亲的头发,像提个温水瓶似的将母亲提了出去。先是母亲的脚碰到客厅桌椅与一些杂物的声音,然后我就听到一声重物撞击玻璃发出那种尖锐的碎响,这响声伴随着父亲的叫骂而炸开,紧接着就是母亲高分贝的惊呼——“妈呀!我的妈呀!”。我知道是父亲在打母亲,揪住她的头发往墙壁上乱撞,刚才那声音肯定是撞着了卫生间里的镜子。
母亲的呼叫像闪电在强烈而决绝地撕破夜空,又像一根锐利无比的钢针在我心尖上扎。我的心陡地一下就被悬在了半空中。我想:完了,母亲肯定出事了。
母亲的哭声让我很心疼很难过。我想,在这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我心疼和难过的了。此刻,我很真切地感觉到整个世界都伴着我的心跳在微微发抖,像地震后的余震一样让人心怵。
“你一天就只晓得跟老子谈钱,谈你家妈卖X,你以为老子打不死你。”这是父亲的吼声在我耳朵里回旋。
我受不了了,颤颤巍巍地掀开棉被下了床。可我毕竟只是个小孩子,我的力量太小了,帮不了母亲。我跑出屋,站在楼道上使劲地喊:“张伯伯、李婆婆,我爸爸打妈妈了,你们快来啊。”
夜已很深,张家李家的邻居们似乎都睡了。我父母的打骂声与我的喊声在这样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但张家李家的邻居们都还是没有醒,或者是醒了也在假装没醒。
外面漆黑一片,漆黑的空气中弥漫着阴森森的气味。我一个人无依无助地站在楼道里,站在茫茫夜色中,有一种快被吞噬的感觉。
我彻底失望了,只好伤心地走回屋,走到母亲的哭声跟前。
母亲在抽泣着,好像没发现我。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凝滞,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想,我这是在哪里呢?朦胧中有一扇门在我面前虚掩着,一股异常的臭味在提醒我,这里是我们家的厕所。我轻轻推开那扇似有若无的门,没开灯,里面仍漆黑一片。我看不见母亲具体在哪里,只听见她在哭。我赶紧喊了一声妈妈。当我的第二个“妈”字都有没来得及喊出时,我胸中就有一股酸涩的力量在强烈地往外涌,并不顾一切地冲上我的喉头与鼻腔。我明白自己快要哭了,就赶紧闭上嘴巴,咬牙将这股味道吞回了肚里。如果我不这样,就一定会哭出来。我想劝母亲不哭而自己又怎能哭呢?
我赶紧伸手按了一下厕所墙上的电灯开关。灯亮了,我发现墙壁上的镜子果真被打碎了,锋利的玻璃碎片散布一地,很恐怖地映照着母亲这副可怕的面容。母亲的屁股刚好坐在便槽里,蓬乱的头发已遮住了她的大半个身体,没遮住的地方不是血就是泪。
我咬了咬牙,努力地把母亲扶了起来。母亲站起来了,我伸手去为她擦眼泪,她没要我擦,却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很紧。
母亲一边哭一边哽咽着对我说:“幺儿,我要是同你爸爸离婚,你跟到我们哪个?”
我明白母亲问我的意思是想让我说跟她。我很想说自己愿意跟着母亲,但我还是放不下父亲,我不想让他们离婚。我最想的就是马上有一样像“神笔马良”手中的神笔似的宝贝,我要让它为我制造出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就把钱分给爸爸妈妈。我想,要是他们都有钱了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不会说离婚了吧?
“神笔马良”只是个神话故事,但那时的我却不懂得什么是神话故事,我认为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确信无疑。我真佩服自己当时的这种想象,天真、可爱!我真恨自己后来也不知是何时就把这种想象力给弄丢了。
我既可怜母亲又同情父亲,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替我想一想?我不要家里时常都是埋怨、吵闹和打骂;我不要哭声,我要欢乐的笑语和甜蜜幸福的生活。
我已经记不清父亲和母亲是第几次打架了。不,他们这也不是打架,因为母亲根本就不可能打父亲。但父亲像今天这样地往死里打母亲还是头一次。以往,母亲每次挨打后都叫我别出去乱说,她自己当然也是忍气吞声,没敢张扬。尤其是在亲戚面前更是从未提起过这方面的事。我想,肯定是母亲怕让自己的不幸会进一步连累别人。母亲明白自己没有正式工作,她还不想真的同父亲离婚。但今天母亲却亲口说出了要跟父亲离婚的话,我不知她是不是已经狠下心了?
母亲继续喋喋不休地唠叨着。
父亲一气之下又走了。
长大后,我也厌烦女人喋喋不休。想来父亲也值得同情。
父亲回来时我与母亲都已经睡着了。父亲喝醉了,他没能从身上找到开门的钥匙,就一股劲地用拳头打门,打得门都快要垮掉了一样。我醒了,母亲也醒了,但母亲没去为父亲开门。我实在听不下去,准备去为父亲开门。母亲在被窝里捏了我一把,并悄悄叫我不要管父亲这个酒疯子。于是,我也没动了。
尽管我也特别可恨父亲醉酒,但也不喜欢母亲悄悄地捏我一把并叫我别管父亲的行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我是在上初中以后才听说的,但我觉得这句多年后才听说的话完全可以提到这时来用。
父亲终于把门打开了,他进屋就一股冲天的酒气。母亲很生气,说不准父亲上床睡觉。父亲二话没说,伸手过来一把就将母亲从被窝里抓了起来。母亲还没来得及反抗父亲的耳光就狠狠落在了她脸上,很响亮很清脆,也许是父亲的力量太大了,母亲的鼻血都被打了出来。望见母亲的鼻子淌血了,我很心疼。我想去阻止父亲,去帮母亲打抱不平,但我太小了,只能蜷在被窝里,根本就不敢出去。透过被子的缝隙,我还望见母亲简直就如一只陀螺,被父亲打在原地旋转了若干个圈。当母亲旋转的惯性都还没完全消失时,父亲的拳头又上来了。母亲的头、胸、手、肚子等部位连续遭受袭击……
母亲已决定要跟父亲离婚。她说她什么都不要,就只要我跟着她就行了。父亲说不行,因为我是他儿子,我是跟着他姓的,他不能让母亲将我带走,他还说母亲没得工作养不活我。母亲说她也是人,她虽然没有工作,但她吃得苦,她不相信现在这社会能将我们娘母俩饿死。父亲说,行,离就离,明天就离。见父亲这么说,母亲似乎还高兴了起来,怕父亲到时反悔,她赶紧抓住时机,加强语气地质问父亲,哪个哪样不离?为了面子,父亲只好硬着头皮诅咒发誓地回答说,哪个狗日的不离!哪个日他妈的才不离!
我想,这时父亲的酒肯定已经醒了,因为我发现他说了这句话后就渐渐地有点不敢正视母
亲了。母亲像个乞丐似地站在屋中间,但她早已经没哭了。她双手叉腰,目光如炬,看上去活像电视里的丐帮老大。父亲这下反而有些胆怯了,他就埋头一个劲儿地抽烟。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父亲开始变得温柔起来时母亲反会变得有些坚强了?我还是个孩子,我没抽过烟,但我能理解父亲作为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要不停地抽烟,认为他在这时抽烟是最恰当不过的。我想,烟草的味道或许真能减轻他内心的苦闷。与此同时,我觉得再待在父母面前听他们谈离婚的事和讨论自己到底应该跟谁这些问题会很尴尬,便提着扫帚去厕所打扫那些玻璃碎片。听着我扫玻璃的声音,父亲或许也觉得自己刚才打母亲的确有些过分。他谨小慎微又吞吞吐吐地问母亲,问她伤得重不重?要不要去医院上药?母亲说,反正还没死!不过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前我一次次的让你,让你喜欢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可是从现在起,我是不会怕哪个的了。如果不信你就试一下,若把我逼急了,就是杀人我也敢!
父亲无语,把头埋得更低了,神情颓丧得活像一条垂死的狗。他先前打母亲的那种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完全一副束手待毙的可怜相。除了继续抽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干点别的什么?比如给母亲道歉认错或帮我整理与打扫一下房间。
我把地扫好了又用拖把将地上的血迹拖干净。
我从厕所出来时父亲和母亲都没说话了,他们的沉默同样让我胆战心惊。我想了想,望着父亲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再打妈妈了,行吗?父亲没回答,但我看得出他内心也很惭愧很内疚。我甚至想,要是他们现在再打一架就好了,再打一架父亲就肯定不会还手。如果能让母亲狠狠地打一顿父亲,或许这样就能让母亲消气,这样情况就会有转机。于是,我又望着母亲说,妈妈,你就再原谅一次爸爸行吗?只要你们不离婚,我今后一定不再贪玩,一定听话,好好读书。母亲也没回答我。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只有墙上的钟在哒哒哒的走着,我抬眼看了一下,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好想这一切都是假的,是在做梦。天真地想,要是自己睁开眼睛时不是这番景象就好了。见我闭上了眼睛,母亲以为我真的困了,就说,小不点,现在不早了,你明天还要读书,快上床去睡吧。我说,妈妈,你答应我啦?母亲说,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父母亲都睡在我身边,很平静的样子,仿佛昨晚什么也没发生过。这种貌似平静的表象让我很高兴也很迷糊,感觉这里面似乎蕴藏着某种玄机。我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我黯然神伤,很想知道真相又不敢也不愿叫醒他们去问个明白。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下床,蹑手蹑脚的走进厕所。我想去看那面镜子还在不在。厕所干干净净的,没有镜子,更没有一丁点儿血迹。我迟疑片刻,企图寻点痕迹。同时,我心里又带有另一种期望,巴不得自己找不到什么痕迹,这就证明前面的那一切是假的,是一场噩梦。可是很遗憾,我终究还失望了,因为我发现墙壁上有几颗挂钉和一些小玻璃残片。
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背上书包就上学去了。课堂上,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不了。我没打瞌睡,也许在老师看来我正听得很专心,其实我一点也没听懂老师在讲些什么,老师的讲话没能进入我的大脑。整个早上,我都在一遍遍地回忆着父母之间的事,像看一部又长又臭的恐怖电影。我本不愿去想这些事,但它们似乎已牢牢地刻进了我的心里,无论怎么努力逃避都无济于事,我已经上瘾了,不想都不行。同时,我又特别的紧张,担心放学回去后家里还会发生些什么事。
我回到家的时候,率先出现在我眼里的是一双脚与那脚边的一地烟蒂和几个啤酒瓶。我原以为那是父亲,但一双高跟鞋与那条我再熟悉不过的花边裤告诉我那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母亲的脚上方就是灰蒙蒙地回旋着的烟雾,这烟雾让我看不清母亲的脸,只隐约发现她的脚上方有一点如萤火般的亮光在忽闪。我明白那是母亲正吸着的烟头。我以前从未发现母亲也会抽烟喝酒,今天是个例外。我怔了怔朝着那个亮光问父亲的去向。亮光那儿发出一个微弱得几乎不能听见的声音——他走了。他走了?走哪儿去了?他为什么要走?他还会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我脑子里一下就冒出无数个问号。我想继续朝着这个这个亮光将这些问题逐一问遍,但我努了好大的力都没能张开嘴巴。
父亲走了。母亲却开始学着父亲一贯的样子不停地抽着烟。母亲怎会这样?她是不是中邪了?面对此情此景,我脑袋一团糨糊,仿佛面前这人不是我母亲而是一个魔鬼!
后来我也无数次地见过女的抽烟,也有人对我说女人抽烟的样子比男人更有味道,更性感,更酷!但我总觉得抽烟的女人可怕,像魔鬼。
我没吃饭,也没饭吃,当然也不想吃饭。此刻,我最想的就是马上去找父亲,但我周身发软,双脚一步也迈不开了。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哭。父亲真的走了,他真的不要我也不要我们这个家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脑子里嗡嗡地响着,像是什么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恐怖气息,我像是置身于一个可怕的魔洞里,到处都冒着彻骨的寒气。我胯下一阵奇痒,紧接着裤裆一热,一股尿液不受控制地淌了出来,把整个下身都给弄脏了。我不知自己怎么会这样糟糕,我想自己去找条裤子来换,但我就是动不了。恐惧还在继续扩张,我也随之而越发感到眼皮很沉重,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发现自己穿了一套新衣服,红色的,胸部还有我最喜欢的米老鼠。父亲已经回来了,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母亲在厨房里煮饭,她一边煮饭一边不停同父亲讲着笑话。我问他们自己哪来的新衣服?父亲说是他和母亲刚刚上街去给我买的。我乐了,咯咯咯地傻笑。这时,母亲丢下手的活儿,从厨房走过来,走到我的面前。她撩起围裙揩了一下手上的油污,然后就弯起右手食指在我鼻尖上轻轻地刮了一下,并告诉我说,小不点,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喂!小朋友,你醒醒,快醒醒!一只手轻轻地在我脸上拍打了几下,我睡眼惺松地抬起来,模模糊糊地看见面前站着几个高高大大的人,好像还穿着警服。我想,他们肯定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我抬用揉了揉眼,终于看清了面前这几个人,前面站着的两名警察叔叔,后面两个就是爷爷和奶奶。我愣了一下,确定自己刚才是在做梦而现在才是真正的醒来。我有些发懵,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叔叔说,你问我,我们还要问你呢!我更加懵了,怎么回事?难道……难道……我不敢想下去。
爷爷与奶奶的眼睛都红红的,他们好像也刚刚哭过。奶奶很勉强地冲我笑了一下,说,乖,你不要担心,没有发生什么事,只是你爸爸妈妈闹了点小矛盾,现在这两位警察叔叔来向你了解他们最近的一些情况,你不怕,只管如实地向两位叔叔讲清楚就行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父母的关系不好,知道他们昨晚打架的事,再说,既然都知道了,又干嘛还要来问我?其实,从内心出发,我不想让
别人知道我们家的这些事,因为我清楚这些都是丑事,家丑是不能外扬的,但此刻我父母都不见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为他们保密又有何用?我咬了咬牙,又深吸了一口气,强装镇静地将他们想听的话讲了一遍。最后,奶奶又说,乖,这几天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从现在起你到奶奶家去,奶奶煮饭给你吃,送你去读书……
奶奶的眼眶湿润了,她的泪水在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他们都在瞒我、骗我。
我觉得人都是在成长或者说是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欺骗的,仿佛人成长的过程就是学会欺骗的过程。一般来说行骗的都是大人受骗的总是小孩,很少有相反的现象。大人们不仅爱欺骗小孩子,而且也常常欺骗他们自己。
我想我父母肯定出事了,而且是大事,至于大到什么程度,我还是不敢想下去。
我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时她也穿上了黄色的马甲,那上面很明显地写着一个“囚”字。我仍是被那两名警察叔叔叫去见母亲的。他们说我母亲也要走了,让我去见她最后一面。这时,我忽地想起母亲那天说的那句“若把我逼急了,就是杀人我也敢!”的话。我的头皮倏地一下就炸开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就像一场噩梦醒来一样,真相大白。但一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爸爸,紧接着就会没有妈妈了,想到我的这个家就这样地毁掉,我心里害怕到了极点。一股寒流朝我倏地袭来,我身体的每一根毛发在这一瞬间都竖起来了,每一个毛孔都在用力地向外冒着冷汗。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已经不再是我了!
我在看守所的办公室等待警察叔叔去叫母亲,我将要在这里同我最亲最亲的人——生我养我的母亲作最后的道别。看守所办公室的墙上同样挂着一只摆钟,那秒针在一点一点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每敲一下我的神经就紧张一次,心里就剧烈地疼痛一次。我知道这些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也许此刻此时不应该被称为宝贵,但它去一点就永远的少了一点。
母亲低着头走了进来,很颓丧的样子。她双手戴着闪闪发光的手铐,双腿一直都在不停地打抖。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母亲很可怜,现在我才知道母亲除了可怜以外还很可悲、可耻、可怕。我甚至希望她不是我母亲,因为她亲手杀害了我的父亲。尽管父亲以往对母亲和我都很恶毒,很过分;有时我都恨死他了,但真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还是很想念他,我想,不管咋说,他说是我的父亲。我现在正在这里与母亲作最后告别,但我父亲呢?他在哪儿?为什么不让我也见他最后一面?
母亲终于抬眼望我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充满了血丝。就在这一瞬,我发现母亲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就老得不成样子了。她额头上的皱纹像群山一样重重叠叠,眉毛也脱落了许多;松弛的眼皮耷拉下来,把眼睑下方遮出了两道可怕的阴影。
见了我,母亲疯狂几步就奔到了我面前,并毫不犹豫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这时,我看见母亲的嘴唇也正在没有规律地颤动,她似乎要对我说什么,却没能吐出一个清楚的字就涕泪俱下。不知为什么,这次见到母亲流泪,我心里反而开始温暖了起来。除了母亲的哭声,屋子里就静得怕人。为了不冷场,我清了清嗓子,很平静地喊了一声妈妈。母亲更加激动了,她将戴着手铐的手伸过来摸我的脸,一时泣不成声。
母亲的泪水流得更凶了,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凶若干倍。我忍不住又喊了一声妈妈。母亲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幺儿……是妈妈不好……妈妈对不起你……
我一时不知该说点什么,大脑一片空白。
母亲又说,幺儿乖,以后你一定要坚强,要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听爷爷奶奶的话,听老师的话,长大后千万不要学爸爸,也不要学妈妈,你要做一个有文化有良心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男子汉!
我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对母亲的话却似懂非懂。
二十多年后的某个深夜,我悚然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打骂与一个小孩凄厉的呼声惊醒:张伯伯、李婆婆,我爸爸打妈妈了,你们快来啊!这呼声在这样的夜里同样刺耳和让人揪心,我仿佛触电般起身想寻找这声音的来源,四周却寂静如初。
我怀疑这呼声来自自己?
呼声渐弱,夜又重新静了,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
夜已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
责任编辑:蒲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