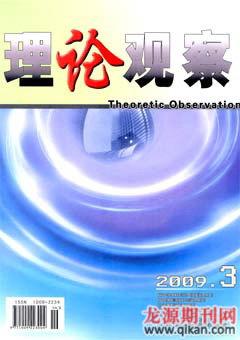制度资源与制度选择:第一届人大组建的现实逻辑
陈家刚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采取了让第一届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过渡办法。到了1952年,一届政协即将到期。这时候一个重要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是召开二届政协?还是召开一届人大?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意味着不同的制度选择:是正式确立人大制度?还是让政协制度继续发挥代替性作用?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最终选择了召开一届人大,正式构建人大制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斯大林的制度建议是一个催化剂;其次,革命者的制度理想提供了根本性条件;最后,现实形势的变迁别提供了现实性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届人大组建的现实逻辑。
[关键词]一届人大;制度资源;制度选择;制度理想;现实逻辑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3-0063-04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以别于1946年1月召开的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三个为新中国政治架构奠定基石的历史性文件。会议还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载入史册。
那么,为什么1949没有召开一届人大,建立人大制度,而是召开了新政协会议,让政协代行人大职权?既然已经决定让其代行职权,那么,为什么仅仅在短短三年后就决定召开一届人大,构建人大制度?通过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眵势的变化进行一番梳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答这一问题。
一、现实的制度背景:政治协商制度
一届人大召开以前,尽管《共同纲领》规定了人大的政冶地位,但是现实中代行人大职能的却是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1954年以前的一段时期,新中国实行的是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人大制度。人大制度因为没有组织载体,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政治协商制度构成了到1954年才正式确立的人大制度的制度背景。
那么,新中国为什么没之初首先建立人大制度,而让政协制度成为了先行者?事实上,历史对这一问题做了解答。首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使蒋介石反动政权更早的垮台”。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时,当时的军事形势尚不明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将一些爱国的党派和民主人士有效动员起来。其次,政协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延续。林伯渠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需要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重要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倡导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政治协商会议借鉴了已有的形式。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己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基于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首先建立了政协制度,而不是人大制度。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后者产生以后,可以向后者提出建议案。因此,一届人大召开以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但是,事实上,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并无本质的不同。林伯渠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譬如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了协商的办法,真正的发扬了民主的精神,使各方面的意见集合起来。”既然两者并无本质不同,为何政协只能暂时代行人大职能,扮演一种过渡性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理想与现实妥协的结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方面,人大制度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另一方面政协制度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新政协的过渡性命运。
1952年,一届政协即将到期。这时候就将一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召开二届政协?还是召开一届人大?就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算什么问题,两会可以同时召开。但是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两个答案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后果。既然政协是代行人大职能,如果召开一届人大,就意味着政协代理地位的终结;反之,如果不召开一届人大,则意味着政协仍然可以代行权力机关的职权。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如果顺应民主党派的意愿,一届人大可能还需要推迟召开。但是,随着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及党内有人提出制定宪法的问题,召开人大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10月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致信斯大林请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何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斯大林建议立即召开人大和制定宪法,这实际上起了一种推动作用。
二、斯大林的制度建议:寻求合法性
斯大林曾三次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第一次是在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之时;第二次是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时候;第三次是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之时。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作此建议呢?其理由是什么呢?斯大林在1952年10月24日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提出,“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白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中国的敌人和外国的敌人)
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我同意你在信中所提出的意见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基本大法,这种宪法自然是一种粗制品,但有一个宪法,比没有要好。”。事实上,类似的话,斯大林早在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之时,已经表达过。只不过这一次,斯大林的表述更为完整,更加明确。
斯大林的制度建议事实上反映了他的合法性考量。在斯大林看来,只要有了选举和宪法,即使是敌人,也不得不认可统治的合法性。所以,斯大林指出了现代民主政体的两大合法性来源:选举与宪法。正是因此,斯大林才在1952年10月28日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进一步指出,“印度有宪法并已实行选举,因此,尼赫鲁就可以说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基于这种考虑,根据当时的形势,斯大林提出,“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为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利的。”事实上,一届人大也正是在1954年召开的。所以说,“中共中央之所以改变初衷,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与斯大林的建议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斯大林的建议影响下,中共中央基于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和对国际局势的准确判断,早在1952年11月就作出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1952年12月1日,经毛泽东同志审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决定,拟于1953年9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由于195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没有提出来,宪法无法制定,所以,最终一届人大推迟到1954年召开。
三、革命者的制度理想:根本性条件
斯大林的制度建议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但是召开一届人大,实现人大制度的组织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理想有关。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948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更是直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可见,早在建国以前的数年里,毛泽东的制度理想就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其制度理想也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理想。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的胜利,这一制度理想也逐步为党外人士所接受,进而为广大国人所接受。1949年政协会议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事实上,这一制度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而非毛泽东的一时想法。毛泽东的制度理想不过是对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制度实践的一种反映和发展。一般认为,构成新中国人大制度源头的包括农民协会、苏维埃、参议会、人民代表会议等在革命实践中先后产生的各种政权组织形式。不过,从最终的源头来看,这些制度实践都源于俄国(1936年以后的苏联)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人大制度的建立是制度移植的结果,所以它总是会或多或少反映被移植国家制度实践的一些特征。
正是这一制度理想的存在,才决定着人大制度的最终建立具有必然性,剩下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即使1954年不召开一届人大,其后的时间里也必然会召开。只不过一些现实的国内外条件,促使一届人大最终在1954年召开。所以,1954年召开一届人大,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出现交集的产物。
四、现实形势的变迁:现实性条件
制度理想提供了制度建构的可能性条件,但是制度建构还需要现实性条件。一般认为,1949~1952年是新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现实的形势变迁,提供了人大制度建构的现实基础。这就为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人大制度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经过土地改革的地方,仍然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地主与乡绅在广大的乡土上,还拥有着巨大的权力。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到1952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基本摧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彻底摧毁了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宣告翻身解放。因此,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意味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2经济环境逐步实现稳定。建国伊始,因为战乱影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创伤,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当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管理经济,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52年,财政经济工作已经统一,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国民经济也逐步实现了全面恢复。从数据上来看,1952年的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因此得到比较显著的改善。这就为全面建设一个新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3政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国,其权力的限度是皇权不下县。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权威江河日下。随后的军阀割据对整个政权体制的破坏是巨大的。当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实现全国统一的时候,在政权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也十分有限。建国三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就,通过党组织的渗透和地方政权建设,基本实现了对整个社会,乃至基层社会的牢固控制。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广泛召开,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它们代行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初步的选举经验,使他们得到了政治锻炼,提高了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这意味着新的普遍的选举具有了可控性,可以稳步有序地进行。这就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初步的组织条件。
4国内环境趋于安定。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时,解放区还主要局限于黄河以北,决定战局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大规模战争远未结束,更不用说小规模的动乱和破坏行为了。但是到1952年底,中国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而且1950年底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溃散武装、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极大程度地提高。所以,1949年没有进行普选召开人大的一大障碍,到1952年底已经基本扫除。这就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选举,召开全国人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5国际环境趋于稳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签署,持续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样,国际环境总体上已经趋于平稳。其实,早在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分析朝鲜战争形势时就指出:“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国的基础。”318朝鲜战争结束实际上印证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构建新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适应这一形势,毛泽东产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就相应提出制定宪法的问题,而制定宪法需要召开经过普选产生的全国人大。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普选提高了社会条件;政权建设的进展为普选提供了组织条件。因此,召开一届人大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五、制度资源与制度选择
1制度资源。一届人大召开以前,至少存在着两种制度选择:延续政协制度和建构人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理想,而政协制度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时期的制度实践。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统一战线尽管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它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那里。这一历史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者的命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而言,统一战线是获取胜利的法宝之一,因而在革命中扮演的是手段性或工具性角色。而人大制度则是革命胜利后的制度理想,所以,它是革命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协制度和人大制度的地位在一开始具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尽管面临着两种制度资源,但是制度选择似乎在最初就是注定的。建国初政协代行人大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注定是一种权宜之计。《共同纲领》第十三条规定,全国人大召开以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政协可以全国人大提出建议案。因此,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都明白,政协终将被人大取代,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制度选择。事实上,在建国之初政协制度和人大制度异中有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所以,即使在毛泽东的眼里,两者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如此,为何不坚持政协制度呢?这可以在两者的差别中寻找答案。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普选产生。普选意味着代表是经过普遍的选举产生的,所以,普选产生的人大,更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具有更高的合法性。这也许是中国共产党视人大制度为制度理想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是选择了某种制度,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刻实行,制度实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立刻组建各级人大的原因所在。现实形势的变化提供了建构新社会的可能,毛泽东产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为此需要制定宪法,而制定宪法需要召开人大。这就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原有制度理想的深层背景。与此同时,一届政协即将届满提供了重新进行制度选择的契机,斯大林的制度建议,是推动这一选择的催化剂。最终结果是决定1954年召开一届人大,由此开启了人大制度组织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杨建新,等,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2]刘少奇,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穆兆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尹世洪,朱开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7]袁瑞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v
[8][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