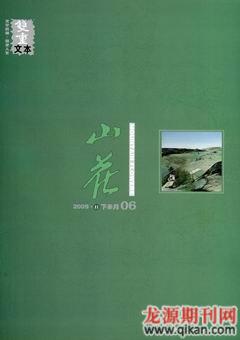在寻求平衡中成长
一、引言
一百多年来,每当论及《简·爱》时,评论者的眼光通常落在简·爱的反抗上,把她视为男权社会叛逆者的典范,并试图赋予她崇高的社会意义。然而,简·爱作为一个纯粹的反叛者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简·爱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表现暴露了她思想与行动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仅仅从性格中反抗的一面来把握简·爱的形象,难免会以偏概全:同样,若把她的妥协放大为人物的绝对失败,也未免过于求全责备了。本文从人与人性的角度看,阐释了一个普通女性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中不平凡的心路历程,从而帮助大家全方位地感受和理解简·爱这一自立、自尊、自强的新型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
1、自尊与自卑的同行并立
毫无疑问,简·爱是自尊的,她甚至将自我的尊严视为高于爱情和生命的一切。为了神圣不可玷污的尊严,即将走向婚床的简·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在爱人苦苦的挽留声中重新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力量造就了简·爱如此强烈的自尊心?其实,造成这种强烈自尊的原动力,恰恰是简·爱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感。
简·爱是自卑的,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让她摆脱人类这一可悲的心理障碍。简·爱的自卑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对自身容貌的不满,对自身身世地位的不满和对自身财产的不满。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在简·爱身上发生作用,从而塑造了简·爱那奇特而又极富魅力的性格。
简·爱的自卑首先表现在对自我外在形象的渺小感、卑怯感上。在被舅妈关进阴森恐怖的红屋子时,简·爱用“鬼怪”来形容和定义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这说明“她对自己相貌的自卑感已经不只是对外表的不认同,而是深深嵌入意识中的对自我价值的否定。但是,简·爱平庸的外貌,像一把摩克立斯之剑,悬挂在她的头顶,既威胁着她的正常生活,更成为她反抗压迫的最初动力。
如果说对容貌的不满仅仅是简·爱自卑心理的表层,那么孤儿的身世,寄人篱下的地位则是导致她自卑心理的深层原因。在舅母家中,简·爱只是一个累赘,甚至比不上一个仆人,谁都可以欺负她。“亲情和母爱的缺乏使简·爱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从小到大,简·爱都把自己排除在她所认识的世界之外,似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可亲近的事物都与自己无缘无分。
简·爱贫困的经济状况,也是使她自卑的又一因素。父母没能给她留下一分钱的财产。身处舅母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却忍受着自身贫困的无情煎熬,现实的强烈反差在简·爱内心深处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不,我不愿做穷人,”足以表明她对自身贫困的极度自卑与不满。简·爱与罗切斯特处于热恋中时,罗切斯特迫不及待地要把家传的珍宝和一半田产许诺给她时,却遭到了简·爱的毅然拒绝:“我要你的一半田产有什么用呢?你以为我是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我宁可要你完全跟我推心置腹。”事实上,简·爱拒绝罗切斯特的慷慨馈赠,不单是至高无上的爱情在做主,更是因为罗切斯特的行为触动了她内心深处那根敏感的神经——男女双方财富的巨大鸿沟使她觉得这是一种施舍,而这无疑刺激了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并使之转化成一种极端的自尊行为。
《自卑与超越》一书的作者阿德勒曾这样说:“自卑感并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正如科学的兴起是源于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自卑感既能摧毁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使人发奋图强,而这后一种作用,在简·爱身上,则表现为一种极端的自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爱的全部奋争,都在围绕着“自卑”一词展开。简·爱的性格是自尊与自卑对立统一的结合,而在这一对矛盾中,简·爱深处的自卑感,无疑是促使矛盾发展变化的内因所在。她一无财产,二无姿色,一个孤女,在夹缝中求生存,再没有谁比简·爱更清楚自己的尴尬境地了。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可,简·爱选择了“用知识、美德和人格力量来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冲淡人们长期形成的偏见”。这由自卑而迸发出的自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她八年发奋苦读,勤勉好学,日渐成长为一位具有高雅修养、独特魅力、沉静气质的脱俗女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简·爱最初的自卑造就了最后简·爱的自尊。
2、“天使”与“魔鬼”的平衡
“在传统女性世界里,父权制文化将女性形象限定为两种固定的模式:要么是代表精神与灵魂的天使,要么是代表性与物欲的魔鬼”。这两种固定的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的自我和个性。而简·爱将“天使”和“魔鬼”统一为同一女性的不同两面。“海伦和女教师谭波尔小姐是‘天使的化身”,她们对父权社会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而且在传统道德理念方面深刻影响着简·爱,并教会简·爱忍耐与自我克制。疯女人伯莎则被归为“魔鬼”一类,她拒绝像“家里的天使”一样服务于男主人公及他的利益,而反过来对他产生巨大的威胁;伯莎象征简·爱压抑的自我挣扎着要获得自由。可以说,同学海伦、老师谭波尔和疯女人伯莎等人合力构成的传统女性世界的正面或反面的教育和影响,对简·爱的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形成的影响是深刻而重要的。简·爱在对照自身和上述两种角色时,既不对传统的“天使”完全否定,亦不对叛逆型的“魔鬼”完全肯定。“天使”与“魔鬼”的倾向在简·爱身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前者表现的是她的理智和约束,以及对传统观念某种程度的遵循;而后者体现的是对她对男权压迫的愤怒与挣扎。这种要求统一的初衷,代表了简·爱理智、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价值选择,以及“她对传统女性世界信条的大胆取舍和中和,使得简·爱具有了崭新的生命气息,”成为一位雅俗兼容的新女性。正如简·爱所大声宣布的:“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这一声划破传统女性天空的呼告意味着其发出者即将给这个沉闷的世界带来惊喜。
在寄宿学校,海伦对特权阶层对自己的欺压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和耐心。对此,简爱不能理解,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愤:“她要是用那个教鞭打我,我就把它从她手里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然而,这种看似极端的个性并未妨碍这两位苦命的女孩成为知心朋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简·爱和海伦所展示的只是同一女性的不同两面。如果说简·爱所展示的是不受约束的女性自我,海伦所体现的则是女性自我充满理智而又倍受压抑的一面。其实在海伦循规蹈矩的外表之下仍然有着矛盾与挣扎,她只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她只能期待来世。简·爱在对待不公正待遇时的态度与海伦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简·爱在受到舅母一家欺凌时,曾多次选择躲藏到隐蔽的角落以避免攻击,甚至想过要改变自己去迎合和讨好他们。虽然简·爱比海伦不安分且热烈得多,但作者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简·爱和海伦有着相似悲惨的孤儿出身和受虐的经历,两人的对待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走向和结局也不一样。简·爱不认同海伦的妥协,但她爱海伦,意识到海伦的信仰中有着她所应当吸取的在艰难生活中生存下去的理由。
疯女人伯莎与简·爱之间的直接沟通并不多,但她同样对女主
人公的成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伯莎是作为孤独的“恶”的一面,用自身惨痛的失败来警告简·爱要在反抗现实的行动上更慎重。伯莎也是一个可怜的父权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她的悲剧是由其父亲、公公和丈夫等男权人物共同造成的,她作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却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因为她疯了,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受到伯莎“魔鬼”式的困扰后,罗切斯特想要寻找一个“天使”来拯救自己,而简·爱不小心踏入了罗切斯特为她设好位置:“一个真正的天使”。然而,简·爱却是清醒的,她坚决否定了强加给她的这个角色:“我可不是天使……在我死以前我不会成为天使。我将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能指望也不能要求我这儿有什么天堂里的东西——因为你得不到的;我压根儿就不期望这个。”简·爱之所以否定自己的崇高,是因为害怕自己在男性温存的赞语下逐渐失去清醒的理智和独立的意志,成为另一个“伯莎”。可见,她同情和理解伯莎,因为她也曾想过要做男权统治的坚定反对者,但同时,她也从伯莎身上意识到了希望的渺茫和反抗的危险,所以她只能在心底里可怜这个疯女人,并时时警告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因此,简·爱要极力强调她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而不是某一固定的如海伦式的天使或者伯莎式的魔鬼的模式。通俗地讲,简爱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反抗,但要有策略地反抗,才会使自己真正成为现实中的自由人。
3、“能屈不能断”的性格
命运对于简·爱是不公平的,她一生都在走着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幼年丧失双亲一在舅妈家受凌虐一在环境恶劣、制度专横苛刻的孤儿院学校劳渥德遭受束缚、摧残→桑菲尔德府上受上层贵族小姐鄙薄的教师生活和罗切斯特疯妻的揭秘一毅然离开桑府途中差点沦为乞丐→在贫穷的小山村办乡村学校,摆脱恩人牧师圣·约翰的逼迫纠缠→几经周折重新找到失明的罗切斯特先生。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诱惑,她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凭借自己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在保持自己做人尊严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尽量对事件做出弹性灵活的处理,竭力在社会上取得自己的立足之地。正如罗切斯特所描述的:“对于明亮的眼睛,雄辩的舌头,火做的灵魂和既柔和又稳定、既驯服又坚定的能屈不能断的性格,我是永远是温柔和忠实的。”这就是罗切斯特眼中的简·爱,一个聪慧、独立,特别的简·爱,尤其是“能屈不能断”这一性格描绘,更准确地刻画了简·爱的刚柔并济的个性。他要爱上不美、贫穷、矮小的简·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通篇中,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简·爱那倔强的叛逆性格。从童年时期与里德表兄的血肉抗争,到桑菲尔德的愤然出走,都表明了简·爱的刚烈性格和敢于反抗的精神。然而,简·爱也不是纯粹的对立者,她作为一个善良、沉稳的女性,其阴柔一面在调和自身与外界的矛盾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反抗的道路上表现出叛逆与妥协的互接互融,这要求我们要对人物进行矛盾性解读。
简·爱是一个鲜明的反叛者,“她对现实中的种种压制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和叛逆”,然而,她又是一个善良、温柔、宽容的女性,本身的特质使得她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又表现出忍让和包容。当罗切斯特放下主人的架子,与她平等相处的时候,她接受了他送过来的玫瑰:当他摆出绅士的尊贵,用居高临下的口吻与她说话时,她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斗士。正如她对罗切斯特大男人主义般的婚姻设计毅然进行出走,而当她历经煎熬,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爱情需要后,又决然地回到爱人身边。这是因为简·爱的精神是独立的,她可以为了自尊离开爱人,同样可以为了真爱回到爱人身边。这种大情大性、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使得她可以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追求适时调整自己的原则,但决不能放弃,因而造就了她能屈能伸却不能断的柔韧品格。
简·爱在叛逆和妥协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利用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清晰认识,综合自己对于精神和物质的需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考,从而作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最后,简·爱终于找到了独立的自己,一个刚烈却不失温柔的自己。她是在走着属于她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可以这样替简·爱表白:忍让不等于屈服。反抗不等于反叛。适当的妥协不等于放弃追求。对传统性别意识发起进攻不等于要逃避自身性别所带来的责任。简·爱再独特,也首先是一个女性,有着女性天生的体质和气质,而不是“无性”人,因此她必须在传统女性女性和现代女性之间寻求历史的平衡。可以说,简·爱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形象,因此她的身上体现了女性在面临各种境遇而产生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促使简·爱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女性特征,成为颇多争议却始终惹人喜爱的文学形象。
四、结论
对于简·爱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纠正以往将简·爱放在过于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性别对抗中去评判的错误,而要努力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人物生活,争取给简·爱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当我们把简·爱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而不是一个十足的反叛者,我们就会发现人物的更多魅力。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刘易斯所说的:“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有着凡人的种种弱点和常人的优点,一个女人而不是一种模式。”简·爱的出现已经使得同时代那些“天使”的女性形象黯然失色,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既坚强又柔弱、既叛逆又妥协、既刚烈又温和的综合特征,这也是她为何能吸引各国读者长达百年之久的魅力之所在。
作者简介:
宋利存(1968-),女,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个“疯女人”的反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