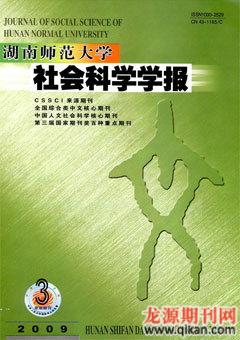“性灵”内涵变迁的历史考察
熊江梅
摘要:性灵说首先是一种生命学说、心性学说,而当其由生命的向度向文学投射或渗入,方能转化为一种文学批评言语,晚明性灵说分潜蕴期、发展成熟期及余声期三阶段,主要是在与情感说的交叉穿行中显示其历史轨迹的,其内涵随几经变迁,但均突破了正统性理观视域,承载了对自由精神的允诺,因而成为晚明最具创意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性灵;情感;虚灵;浑情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142-04
“性灵”一语古已有之,并非明人的独创,但它通行于晚明,且成为最能代表晚明精神特质的—个文化批评概念,亦是毋庸质疑的事实。近十多年来对晚明性灵说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逐步推进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有些研究者不甚顾及渊源及语境,往往不加分辨地将性灵与另一邻近性概念“情感”混为一谈,这与性灵说固有的学术与概念基础难以相符,也与性灵说之发生与变异的情况有很大出入。另有一些研究者离开确切的概念把握而将各种与心灵自主有关的创作现象都纳入到性灵的解说中,从而导致了对性灵解释的泛化。基于这些不足,本文意在对性灵作一较为全面的紧扣概念的梳理,以便更为准确地清理和把握其概念内涵发生与变异的历史轨迹。
“性灵”一语在后七子成员如屠隆、李维桢、王世懋、王世贞的文章中被较多使用,可以看作其作为一个批评性术语已正式成立,但性灵并未成为其批评思想的核心观点,因而仅是预示了从前七子主情说而至公安派性灵说之间的一个文学批评运行轨迹。对于这一问题,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章节即有敏锐的阐发,郭先生的最主要观点是后七子阶段所提出的“神韵”说等,意味着七子派复古主义开始从其前期的格调说而向晚明性灵说转换,比如他例举的谢榛、胡应麟、王世懋、王世贞等,悉有相似的表现。郭先生这一见地精辟地指出了后七子在引入自得、逗变、神化等基本要素之后对前七子诗学理论所做的转化,而这些转化又正好能与后来出现的公安派文学思想连成一片,因此而构成了由复古派向性灵派的过渡。但一般学术界论述性灵说,主要是以三袁等公安派的思想为主,这有失简单片面。实际上,公安之前唐宋派之唐顺之实已揭橥性灵的关键意蕴,可视为性灵说之潜蕴期,而公安以后又有竟陵也主于性灵之说,成为在某种意义上的性灵派之承继者。故对性灵概念的考察必须顾及这个整体的状况,方能确实把握其丰富内涵。
在性灵这一概念的含义中,“性”即指心性本体,或云始源本体,无疑具有本原性的基础地位。当然,这个“性”的呈示不是漫无边际的,而补充入“灵”的概念,正是要对“性”的特征作出一个方向上的基本限定或确定。这个补充显然与传统儒学对“性”所做的规定有很大的差别,而主要与儒学与理学的变体即心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汲取了当时繁兴的其他心性之学如佛教和道教的理论资源。关于这些,在学者的讨论中已有很充分的反映。故性灵说首先是一种生命学说、心性学说,而当其由生命的向度向文学投射或渗入,方转化为一种文学批评言语。
一
根据上述对“性灵”概念的基本理解,我们可以判知,“性灵”这一概念与唐宋派唐顺之的“精神”、“神明”等概念在学脉上是一线相承的,二者最终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心性主体,并以之与非本体性的“情”相区别。
唐宋派思想的发轫最初是直接针对前七子而来的,其中包括对前七子的主情论及他们耽于文艺与情绪发挥的情况。唐顺之由于前期深受前七子的影响,因此,他对前七子思想的反思多以自身的情况来说明。在《寄黄士尚》一信中,唐顺之有云:
自儒者不知反身之义,其高者则激昂于文章气节之域,而其下者则遂沉酣于蚁膻鼠腐之间……张舜举言兄自戍辽以来,作诗几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岂将以是自鸣其习坎心亨之乐耶?抑或者穷愁羁旅无聊之思而姑托以自遣耶?抑以写其江湖之忧而致其去国缱绻不忘之爱,如古《离骚》之作耶?其无亦自拟于铙歌鼓吹、《辽东》、《都护》之曲,而与塞垣横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讴吟耶?不然,则枝叶无用之词,其足以溺心而沮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课—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谓反身,而又奚取于枝叶无用之词耶?弟近来深觉往时意气用事,脚跟不实之病,方欲洗涤心源,从独知处着工夫,待其久而有得……一洗其蚁膻鼠腐、争势竞利之陋,而还其青天白日、不欲不为之初心。”
很显然,唐顺之的论述直接从生命论切入,将是否反身关心自己的心性状态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并从这一视角出发讨论文学问题。唐氏在文中一气排比数落下来的那些文学事象恰是前七子复古主义诗学所推崇的。唐氏对这些诗情则取贬抑态度,论其原因,他认为一是无用,二是溺心,而这对于心性的培育是有害无益的,故唐顺之希望对方转换对文学的沉浸,反顾自心的修行,从而达至所谓“还其青天白日、不欲不为之初心”,此即他另处所谓的心性“本体”。在唐顺之看来,这个心体至为清晰的一个特征,即“无欲”。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学术上的主静与妙用观,他认为文学应反映无欲之本体的“妙用”,妙用不限于心体的自我闭固,而是一种洗涤心源之后的重新面对世界,但面对世界的方式已与过去大不一样,因为它是扎根于本体的一种发露,为本体所带动,并呈现出本体的光色;又由于去除了欲念、情欲、习气等的沾滞,发露必然不受物累,无所羁绊,率性自由。从文学向度看,妙用之说,既可通向于对复古模仿的批评,又可通向于对情气之用的超逸。这个“妙用”、“神明”的概念,在唐氏的言述中更多地表述为“精神”。唐氏所谓“精神”是心性本体的一种更为凝神化的说法,其意义通于修身与文辞二端,并具有超尘脱俗、独立物表、精光发露、生机洒落等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传统儒学规定的伦理心性,并与各种义理解释不相容,是一种“生”之状态下的自然灵明。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唐顺之没使用“性灵”概念,但却已经蕴有了性灵说最基本的若干意义,因而它也规定出了未来性灵说的一些意义,故此可将唐顺之的这个“精神”说看作是后来性灵说的一个潜蕴期,同时也是心性之学影响文学的第一个观念性成果。
二
唐顺之的心性论具有反拨传统理学的意向,即从对规定性义理的尊崇而转向对人心、人性,亦即人之生命主体状态的集中眷注,并由此开启并构成了中晚明文学思想的基调。但晚明时期性灵概念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其内涵界定并非都承唐顺之而来,学界于此多有笼统混淆之处,故特予以辨析。
对于性灵说,袁震字、刘明今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中有很好的阐述:“当时援佛入儒已成为士大夫时髦的追求。禅学与心学在许多方面很接近,如禅学所提倡的‘顿悟正是要求在心灵上对客观世界作出解脱,其追求的也是一种空灵澄净的本心……‘郁郁黄花,无非盘若,与心学以清虚灵明释良知其
意相通。当时心学与禅学流行,屠隆与公安三袁诸人或好心学,或好参禅,因而他们在文学批评中所倡导的性灵说也自必摆脱不了虚灵观念的影响。”论述建立了性灵说与禅学和心学的明确关系,确为切中肯綮之论。但论述将公安三袁与屠隆相提并论,均置于虚灵式性灵说范畴中,却不免似是而非。据考辨,晚明时期的“性灵”说,其内涵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虚灵为中心的去情论的性灵说,主要体现在屠隆的思想中,二可称为浑情式的性灵说,主要体现在袁宏道的思想中。下分而述之。
在《贝叶斋稿序》中,屠隆说:“诗道大都与禅家之言通矣。夫禅者明寂照之理,修止观之义,言必寂而后照。必止而后观也。兀然枯坐,固然冥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住而不住,不住而住……余闻惟寅筑贝叶斋,日跏趺蒲团之上,而诵西方圣人书,与衲子伍,则惟寅之性灵见解如何哉!”可见,屠隆所言“性灵”,既与道教相关,也与佛教相关,突出的是性灵概念中的虚灵特点,契合于唐顺之所言“精神”、“神明”的内涵。据此论诗,屠隆强调的是性灵概念中的虚灵之义。如他认为诗道与禅理相通,“言必寂而后照,心必止而后观”,如此言诗,自必偏于清空一途。在论创作之境时,他说:“方其凝神此道,万境俱失;及其忽而悟解,万境俱冥,则诗道几成矣。”所谓凝神的状态是“万境俱失”,悟解的结果又是“万境俱冥”,都是空幻虚灵的。
虚灵式性灵说的产生与三教在晚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其时知识界、尤其是文学之士对世俗儒学与世俗风俗所做的一种精神对抗,及通过对性道之学的改造和重新命名的工作,以寄予其自由与脱俗的情怀。但是这种以反世俗为起点架设起来的理念,并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时代所提出的—些尖锐问题,比如情的发现、世俗化进程的展开等。实际上,虚灵式性灵说反映的只是一个有限群体的想象性解脱,其所提供的关于自由的承诺也只限于精神上的解脱,而无法满足那已被人们认识到的身心合一的——因此合情、性于一的——快乐与自由。就此而言,排除或有意忽略隋感存在与价值的虚灵说,在面对晚明社会文化心理固有的结构性矛盾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采取了回避与退避的方式,但却反而与业以发生的现实合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妥协的紧张。不管怎样说,这不是唯一的应答与处理晚明社会变化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沿着这条思路往前走,就出现了一种更有融摄性的补救模式,即泽隋式的性灵说。浑情式的性灵说也还是一种性灵说,因它并未遗弃以心性为本体的基本原则,它只是在不离性的基础上,使虚灵与情识之间达到一种意识上的化合,使情感论能够在一种新的言说系统中被认定下来。袁宏道的性灵说即突出体现了情、性浑成的意蕴内涵。
袁宏道的性灵说受到李贽思想的明显影响。这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二人思维方式的承继上。就李贽而言,其所使用的一种禅学取消分辨性的思维、以不即不离说法的方式,却对那种以虚无为执定、以离世去俗为言说准则、以清脱自高为价值标榜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观念,其中自然包括虚空式性灵论解说,均形成了一种境界上的超越,从而在将情浑融到心体的不做分辨的发用与任运中,开启了向浑情式性灵说过渡的门户。
袁宏道亦擅长运用取消分辨性的致思方式,他常借此种思维方式谈论对心性、情感的理解。《龚惟长先生》一文谈到他所主张的自适论所云“五乐”: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谐,浊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生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文中推赏者包含情色性内容,从而与理学、心学心性论的去情欲针锋相对。但仔细体会其文意,则袁宏道所言自适论,又不是简单地执情与滞欲,而是表现为对情欲、欲望的一种运用,透过展示的表象,其内里依然有一种起着调控或使动作用的意识或主体。它不可窥见,但却驱动着这些人生景象登台亮相,朝着一个指定方向趋奔,这一主体即“性灵”,它不离于色相,也不沾着于色相,甚至是内运于此色相,但叉不让此色相固定为可耽溺的挂碍之物,故而这看似一种情的外演,却内在地是性体的沤沫。于此可见,同样是性灵论者,然袁宏道所言之性灵与屠隆所言之性灵,其间区别已非毫厘计。尽管袁宏道和屠隆对性灵说的阐释有明显差异,然于二人观点中其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相通之处,即其内均包含有一自适与自由的目标,当然这不是世俗所理解的那种自由,而是心性论言说场域中的自由。由于均以心性论为共同的起点,因此学界往往将他们笼统地归入“师心”一派之中,这与以情感论为起点的思维模式是有区别的。当然,在对待世俗化感情的问题上,袁宏道的观点显然与唐顺之和屠隆均有重大差异。袁宏道浑情式性灵观的提出,使其能在不离性的基础上将人间情欲包容到肯定性的关系中,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性灵论意义的涵盖范围。但因其始终不离性,故其浑情说又不同于前七子那种单一突现的主情论,因为说到底,浑情说还是主性论的。相较之下,袁宏道的浑情论在推动情的解放时比观念上的主情论走得更远与更深。由于取消了分辨与界限,袁宏道所言浑情说淘洗掉了前七子时代在情的理解中所带来的那种根植于历史社会向度上的凝重感,而将之推广到了与世俗情欲相关的一切对象上,甚至容纳了所谓“秽”、“鄙”、“贪”、“嗔”等为旧伦理学说所摈弃的情欲性内容,从而使欲望的指向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拓展。可以这样说,袁宏道更偏向于从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看待情,注重将之引向个体自适的本体论解释,这是切合晚明时代士人精神之基本貌相的。
三
性灵说在明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与包括文学在内的晚明思想文化之转折相步趋的,就文学观念而言,竟陵派的主张最有代表性,集中体现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情感与心性之间的纠葛是如何在主情论与浑情论大盛其势后而急剧地转变,因而对我们理解性灵内涵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至佳的视角。
竟陵钟惺、谭元春用以标识其诗学主张的最重要文献,即其二人所编《诗归》一书,该书含诗、序、评三部分,三者之间具有内在思路上的统一性。钟惺为《诗归》所撰一序,可谓是对竟陵思想的最集中阐释,含有了这一流派思想的基本理论元素:
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尝试论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做诗者之意
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化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化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起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端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
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欲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文其所谓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人者之欣于一至。
考察钟惺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要通过选诗使后人能够接引古人之精神,“以古人为归也”,即以古诗为本,借此而领悟古人之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其诗论带有明显的复古主义意识,故钟惺在文中明确批评以矫正复古为名义出现的“必于古人之外自为一人之诗歌者”,其指涉对象显然是以心性论为归属的公安派。但竞陵派与七子派复古主义亦有很大的思想差异:钟惺使用“途径”一语来概述以前复古主义者的特征,依其语义分析,“途径”是一种可以直接依循的规则、风度等,因此是可以不断被重复与习得的,也正因此,它成了“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手口者”,竟陵派之复古则与之有异,即他们强调通过古诗所把握的是古人的“精神”,而不是形质一类的东西。故此,竟陵派虽提出了尊古与师古的口号,但与前后七子之复古还是蹊径有异的,而终归于“精神”或“性灵”无疑表明了其最后所驻足的还是师心派的立场。进而,既然诗歌的形质不存在参照的意义,那么竟陵派的看法自然会更接近唐顺之、袁宏道等师心派,即无须于自己的理论中探讨诗歌“成章”的问题,只要让自心直接向外流泻,就能构成一首好诗,这样,好诗与“真心”之间基本上可以划等号。
然细揆钟、谭关于“精神”与“性灵”的言说,则不仅因为其在外引入了习古一截,而且在其所贯人“精神”与“性灵”等相关词的含义中,均显示出与公安派的莫大差异。钟惺上解“精神”一段中,孤独、清幽、虚空是最为重要的几个义项。钟惺序谭氏诗集时,开首就紧扣诗集冠名之“简远”,并析其资禀云:“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可见竞陵派诗风与其个人性格及意识形态有直接的关系。但钟惺并没有将这些完全看作限于个体的表征,而是借一段叙论将之推为普遍化的公则,其言云:
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昧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之数者,独其心乎哉?市,至嚣也,而或云如水;朱门,至礼俗也,而或云如蓬户。乃简栖、遥集之夫,必不于市、于朱门。而古称名士风流,必与日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岂非贵心迹之并哉?夫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已远乎!
序论虽也涉及到谭氏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但其重心显然在于阐发一种诗之成长所需栖息的处境和心境,刻意展示出一种自觉内归的心理路向。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论述中所取用的一种对比,即逸与劳、净与秽、幽与杂、淡与浓、旷与拘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双方的不可兼容性与袁宏道所使用的混成法恰好相对,即将被公安派所抹杀的种种概念性差异重新分辨出来,以便能够“正确”地进行取舍。虽然未必将一切情都驱逐以尽,但这个清幽淡旷的境界显然很难容忍情欲的存在,或者说只有在去除情欲之后才有可能达到这一境界。
钟、谭的这些论诗主张在《诗归》的评点中有突出体现,他们诗评中的一个关键点即标举“精神”之“寂寞”。如钟惺有评语云:“……到此光景,才是精神真寂寞处,难言难言!……伯牙大悟,头立地成佛,毕竟从精神寂寞来。”考其措意,“寂寞”一语,实可向两个意义方向上展开,一是与大众相对的单一个体的灵魂境地,这点尤为谭氏所强调,以之为“真有性灵所在者,又被称为“孤怀”、“孤诣”。二是指一种清净、空旷、无欲的心理状态,这在钟惺评谭元春“本自孤迥”一节中有清晰的表达。可见,在对心性的认识上,竟陵诗论与唐宋派之间实可相通,当然,这一借助去情或销情的方式谋求心性超越的思路,一直贯穿于整个中晚明思想历程,而竟陵派之崛起可谓从文学的角度集中地表述了刘这一思想回复的要求。
上面对钟、谭诗学的考析显示了“性灵”内涵的再次变迁,与公安派试图不断地扩张心性的涵盖而,以至包容所有的世俗情态相比,竟陵派则不断地缩减自己的心态结构,将公安派业已包容在内的世俗内容清除出去,以保留心性的洁净与单纯。可见,竟陵派在其批评思想的运行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两个重大的拨转,并均是针对公安派的倾向而言的:一是拨转了被强化的自心崇拜,而之复古主义曾经提出的思路,即从古代文本中寻求认同;二是拨转了向情与情欲的无限制开放,而之虚灵派对情感论的抑制。
综上所论,晚明性灵说主要是在与情感说的交叉穿行中呈示其历史运行轨迹的,其概念内涵虽几经变迁,但却均已大大突破了正统性理观所能容忍的最大界限,括入了对自由精神的莫大允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性灵”一语成为晚明文学思想最具创意性的概念和最重要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