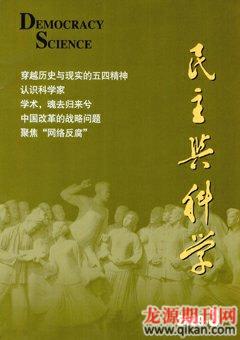“乱世之饭桶”张君劢
刘诚龙
谈及中国的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民国文人张君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06年,张君劢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研法律与政治学,从而结识了梁启超,与梁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1913年因避袁世凯的追杀,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一方面,梁启超的政治倾向引发了张氏的参政热情,另一方面,风起云涌的革命也无法使学者居身于政治之外。张氏曾言:“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劢所习者为政治学,在以往,这一学问应该是一种帝王术,但到了民国,这就是治国道了,在帝王已去、民主潮来的上世纪初,张君劢始终抱着宪政治国的理想,专研宪政,1923年,他在中华民国总统曹锟的“支持”下,满怀热情制定了一部《1923年宪法》,不到一年,曹氏倒台,这一部宪法也“人亡政息”,被永远地丢入了废纸堆;1946年,抗战胜利,蒋介石惺惺作态,要搞民主建国,所以再次邀请时为宪法专家与民盟领导的张君劢来给民国政府起草《宪法》,是为《1946年宪法》,这部宪法出是出台了,而且高挂在中华民国之上,可是也只是写在书上,贴在墙上,躺在文件柜上。什么叫宪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宪法,就是“限法”,就是为保障千万人的自由而限制一个人自由而制订的法律。以千万人对一个人,想来应该没问题,所谓人多力量大是也,然则,政治权力上的事情,远远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权多力量大,一个人只要拥有权力,那么他一人的力量比千万人的力量大多了。老蒋是军阀出身,怎么会愿意受千万人的挟持呢?他才不愿意受劳什子宪法的约束!张君劢认为既然已经国家有宪法了,那就应该“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收拾人心,集中人才”。这话千万人爱听,而老蒋不爱听,为防止张氏老是在那里哓哓不已,多嘴多舌,国民党把他给抓着软禁了。
制定宪法以保千万人的自由,结果连自己的自由都没保住,在张君劢的人生际遇里,这不是第一次。武昌起义后,二千年的帝制轰然坍台,各路神仙纷纷登台,抢占利益制高点,大家都拼选举,拼席位,拼天下,当时最有力量的,有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一党,有袁世凯同志的北洋一阀。张君劢抱持宪政欲予推销,在力量纷争中,谁更有力量?张君劢考量之下,准备将自己的才学卖向袁世凯,在张看来,袁世凯的军阀力量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将宪政卖给老袁可行性大一些。孙中山先生是从来没进入了帝制体制里的,而袁世凯却是品尝过帝制满汉全席滋味的:在帝制构架里,万民得向他来朝仪;宪政构架里,他得向万民朝仪,袁世凯会觉得哪个更爽?张君劢实在是所托非人。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独立,袁世凯却是一点应对也无,如此卖国,怎能叫张君劢容忍?他于是就在《少年中国》撰写《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痛快淋漓,一吐愤气,结果彻底得罪了袁世凯,性命有忧矣,于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以赴德留学之名去国外政治避难。
袁世凯一命呜呼,张君劢这个江东弟子,卷土重来,再以其学术良知与宪政理想奔走于政治舞台。在此期间,有一桩逸事,也可堪一嚼。“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民主座谈会,作为宪政专家的张君劢自然被邀去装潢门面,被戴上了参议员名号。一次,由汪精卫主持会议,会前有个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科目:与会人员全体站立,肃然,听人宣读“总理遗嘱”,时汪之心腹周佛海向胡适嘀咕了两句,胡适即刻站起来:“国民党开会,主席照例要念一遍总理遗嘱,在座客人也照例要站起来恭听,始能就座开会。”其他人也许视为寻常,不过是个形式么?不过是个惯例么?而在宪政专家张氏看来,这是让人没法容忍的,所以,张君劢马上就站起来说:“如果一定要有这个仪式,那么我就退出会议。”胡适跑到面前来做思想工作,张君劢原则面前绝不妥协,最后倒是汪精卫“机灵”,打破了这一僵局:“请各位就座,就开会了。”因为张氏这一次闹了一回,他的宪政也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在国民党内部还是恭敬如仪,但此后,至少在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的这一党例再也没施行了。
张君劢的硬气之举,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里,也不是好玩的。张君劢始终向统治者灌输民主理念,不待人见,在上世纪30年代,他创办了《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鼓吹”什么“人民言论自由”,要求“速议宪政,实行政党政治”,这就惹恼了国民党,不但来封杀他的思想,而且使出恶手段,来封杀他这个人,特务把他给绑架了,而绑架当中,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使其腿部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在民国这个乱世里,张君劢与国民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国民党几次主动约他“入伙”,他也几次自愿不自愿地选择了国民党。1946年,民主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为了摆出一种民主姿态,也拟召开国民大会,其他各党派洞穿了老蒋的把戏,而作为民建党党魁的张君劢却赶去做了民主盛会的点缀,还一丝不苟地给其起草《宪法》,可是呢,他感受到了,“蒋中正是过河拆桥的人,他有求于你的时候,可以满口答应,等到不需要你的时候,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老蒋就是这样,张君劢给他撑台参加国民大会,给他呼应支持打内战,最后却是,一脚把他踢开。待到1949年,他走投无路,只好仓皇地逃往他国,再也未曾回来。
张君劢因为1946年率其团队参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他被时人呼为张君卖。对这一卖,张氏是这样辩白与解释的,他被逐出民盟,另建民建新党:“这伙人跟我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府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些党员?”话说到这份上,有人理解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妥协,有人不领情,依然视之为其难堪的污点,也是的,逞一己之私固然不高尚,逞一党之私就光辉四射吗?其实,考察张之前半生,他一直都是在干卖的事情,他把他满腔的宪政理想打包,到处找买主,他把其理想卖给过袁世凯,卖给过曹锟总统,更卖给过国民党,仓仓皇皇,一路趔趄,看货的不是没有,真正买的有吗?这好像是自称为丧家狗的孔子,四处售卖其儒家理论,到头来,买他货物者只是几个学生,卖货所得只是几块束修。
民国时期学者教授,都无法独居小楼成一统,风云激荡的时代,不可能容许学者死守象牙塔,独善其身的,他们抱持爱国理想,总是奔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其理想托付他人,所托非人还是所托对人?不但得凭自己的眼光,有时也得凭运气,许多人可能没那好运,他们心里自然有比较浓厚的幻灭感,民国另一文人丁文江,有次搞了个学者文人小聚会,酒至半酣,他对胡适等学人讲:我们这些人啊,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话之前半部是自许,后半部是自嘲。这些人有能,那是没说的,在乱世固然是饭桶,难以舒展其才;在治世会不会成为能臣?很是难说,像张君劢这样专搞宪政的,在某些治世里,有机会成为能臣吗?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暗暗也可能将是独成眠的。像张君劢,搁大唐盛世,他搞民主宪政,这可动摇国本,篡夺帝位,纵或是圣明君主唐太宗,也可能不止对他搞绑架那么轻松而客气,也不止打折他一条腿那么简单放过他。
张君劢在民国那时期,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失败的人”,而众人对其评价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传奇的人,他参与创办民盟,却又违背民盟精神而被逐出民盟;他被国民党绑架与软禁过,却也曾被国民党奉为座上宾;他被周恩来送过“民主之寿”的牌匾,却也因为支持内战,被作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被通缉;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帮凶,也有人说他是共产党的走狗。政治风云变换,其头上的帽子也不断换新,张氏命途有如风箱老鼠,半生行状,堪怜。倒是其后来,因为国共两党都不待见他,他出走异乡,专事学问,治政是饭桶,治学可是能人,学问大家的帽子戴在头上,谁也没什么异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