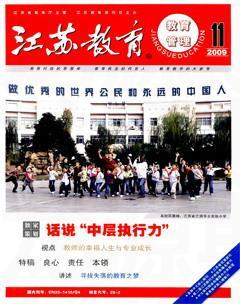寻找失落的教育之梦
李镇西
一
我喜欢和学生一起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嬉戏玩耍。
最初,我这样做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教育意义”,而纯粹是出于自己爱玩的天性。对大自然的共同爱好,能够使我和学生的心更紧密地贴在一起。回想从教以来。我最感到快乐的时候就是学生不把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二十几年来,我的学生就是这样给我以少年的欢乐和青春的激情。
自然环境的教育功能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功能庸俗化。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教育者有一种认识误区,即总是希望每一次野外活动都应有“教育意义”——比如“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呀、“感受祖国山河的美丽”呀,“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呀。等等,而且这样的郊游,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往往还承担着写作文的“重任”。如此一来,对自然美的感受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其实,不用那么多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自然的接近、对自然美的感受就是教育。
不要误以为我反对在郊游活动中有目的地进行某种教育,我反对的是每一次对大自然的亲近都带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外在的“教育意义”,因为大自然本来就是一本最博大精深的书。我竭力要做到的是,让孩子们在没有打开书本去按音节读第一个词之前,先读几页世界上最美妙的书——大自然这本书。……到田野、到公园去吧,要从源泉中汲取思想,那溶有生命活力的水会使你的学生成为聪慧的探索者。成为寻求真知、勤于治学的人,成为诗人。我千百次地说,缺少了诗意和美感的涌动。孩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智力发展。儿童思想的本性就要求有诗的创作。美与活跃的思想犹如阳光与花朵一般,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诗的创作始于目睹美。大自然的美能锐化知觉,激发创造性思维,使言语为个人体验所充实。”(苏霍姆林斯基:《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小桥流水的幽雅情趣还是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无论是朝阳初升时小草上的一颗露珠还是暮色降临时原野上的一缕炊烟,都能使我和我的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冰心:《繁星》)
二
我的右手手掌上有一条醒目的伤疤。这条伤疤埋藏着一个惊险而又甜蜜的故事。
1989年1月25日,在学校刚放寒假的时候,我率领高90级一班的杨嵩、王英浩、沈建、郑洁等学生向蛾眉山进发了。
多次游峨眉山,我和学生们对山上景色已十分熟悉,所以一路上,大家谈论说笑多是风景以外的话题。一过息心所,山路上积雪渐多。石阶上、树上和草丛中,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积雪,使眼前的一切都勾勒着细细的银边。很少见雪的学生们,见到哪怕是一丝雪的踪迹,都要兴奋地互相通报:“呀!雪!”“看,多美!”
山路由一级一级的石阶砌成,每一块石阶上面都积着雪,而石阶侧面则没有雪,这样,由近往远看去,蜿蜒的山路黑白相间,宛如一排钢琴的琴键;而我们走在上面,发出“沙沙”的脚步声,就是在演奏着柔和的《峨眉山冬之曲》!
再往上走,积雪由星星点点变成了茫茫一片,而我们已经步履维艰:大雪几乎把所有的山路覆盖。于是,我们只好从路边的农民手中买来为登山特制的铁钉鞋,把它套在脚上。这种鞋,实际上是铁爪,一走路,铁钉就刺进雪地,自然就不会滑了。
解除了脚下之忧,我们就可以优哉游哉地欣赏峨眉山冬天的奇景了:雪早已停了,没有风,整个山谷静静的,静静的,偶尔一只不知什么名字的鸟儿从某一棵树上飞起,枝头的积雪纷纷落下,传来轻柔的“沙沙”声。眼前的峨眉山。简直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玉雕!路旁的草丛,成了玲珑剔透的水晶珊瑚;高大的树木,披上了厚厚一层棉絮,随着树叶的不同形状,枝头的积雪也呈现出不同的奇特造型:有的像胖乎乎的弥勒佛,有的像毛茸茸的狮子狗,有的像水晶球,有的像玉扇……远近的山峰都在积雪的覆盖下呈现出一派庄严肃穆的洁白。
此时的山路,“钢琴琴键”已变成了儿童乐园里的“滑梯”。在洗象池,本来有一段石阶路又直又长;现在,在厚雪的覆盖下,这条路成了光滑无比的陡坡。我们一行人走到这里,觉得实在不应该放弃对这天然滑梯的享受。于是,我们找来了一个破筲箕准备坐在里面,从上面滑下。坐在筲箕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身下的筲箕平稳而急速地下滑,耳边的风声呼呼地响着,眼前的树木飞快地掠过,整个感觉像飞翔又像在下沉,像驾驶冲浪的游艇,又像骑上下山的猛虎……
一时间,洗象池一带热闹非凡。我和学生们的欢呼声在山谷间回荡,树上被震落的积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越往上走,景色越壮观,开阔地带渐渐多了起来。在金顶,一片积雪齐膝的空旷地上,我和学生兴奋地扑在地上打滚。我们还睡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摆成“一班”的造型(因为我们是高90级一班),我们还摆了一个“文”字(因为我们是文科班)。在摆“文”字的时候,学生一致请我当“文”字上面那一点,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儿”。
这两张雪地摆字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每看一次,我就忍不住发笑:由李崇洪摆的那个“一班”的“一”字,多有“笔锋”啊!当时,因为他个子最高,我们推举他摆“一”,他欣然同意,而且睡在地上时还特地把脚尖微微翘起,说“这样显得有笔锋”!
可是,照完相之后,仿佛有人统一指挥似的,学生们突然向我冲来,扭胳膊的扭胳膊,按腿的按腿,硬是把我死死地压在了雪地上!就这样,我身上的雪越堆越多,也越堆越厚。渐渐地,脖子没有了,鼻子没有了,眼睛没有了……最后,我硬是被男生们“活埋”了!
突然,沈建的惊呼使所有人的动作都凝固了:“血!血!”我一看,果然,一滴一滴殷红的血,在雪地上格外鲜艳夺目。原来我的右手手掌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正从里面源源不断地往外流!可是,我竟一点儿都不觉得疼。
由于峨眉山气温很低,我的伤口包扎也很及时,因此,伤口没有发炎。回到家里,我赶紧到医院处理了一下,一个星期以后,伤口便痊愈了。只是,从此以后,我的右手掌多了一根发亮的“别针”。
现在,当年在峨眉山对我“行凶”的“歹徒”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事业有成,但天各一方,大家见面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但每次他们和我通电话时,都不禁会怀着奢望地说:
“什么时候,能再一起冬游峨眉山呢?”
三
在苏州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曾骑自行车去了用直。
当刚走进用直古镇的瞬间,我情不自禁产生了一种幻觉,我恍惚走进了二三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在古镇口,扑入我眼帘的,是直直而来的一条幽幽的小河,小河的
一边是临河而居的住家户的一格一格的窗子,小河的另一边是石柱砌成的护栏,护栏后是窄窄的街道,三三两两的游客便在这弥散着纯朴气息的石板路上悠闲地看着走着。我感兴趣的还是小河,小河被岸边枝繁叶茂的大树的浓阴包围着,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斑斑点点地洒在河面上。河面上,一条条小船载着游客悠悠地晃动着前进。弯弯的小河连同这悠悠的小船。把我的视线牵引到古镇的深处,可小河太窄,而河边的树木又参差掩映,远处好像有小桥,有飞檐,有酒旗……但我都看不清。而古镇因此对我来说便又添了几分诱惑。
其实,这个古镇对我最大的诱惑,来自一位历史老人。我知道,在用直叶圣陶先生曾付出过自己的青春,获得过文学营养,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文学家和教育家的叶圣陶是从一个叫做角直的古镇走出来的。
我在叶圣陶墓前沉思。从我参加语文教学的第一天起,叶圣陶先生就是我心中的一座人格与事业的丰碑。在我的人生途中,每一成功,每一失败,我常常会以叶圣陶先生的言与行来对照自己,反思,反省。而现在,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可以向他叙说自己了。
我走进“叶圣陶纪念馆”,参观叶圣陶的生平事迹展。纪念馆里基本上没有与叶老生平事迹有关的实物,主要是以图片为主;但在参观的整个过程中,我总觉得活生生的先生就在我身旁,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音容笑貌。
我被先生的一篇短文吸引了,并忍不住拿出笔将其全文抄了下来——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不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是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达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我的想法是否妥当。请广大语文老师指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精髓过去、现在都影响着我的语文教育实践。
参观纪念馆的人很少。偶尔有一拨游客。也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更多的时候,纪念馆里就只有我和叶圣陶先生。展厅很宁静,很祥和,阳光透过窗户斜照着我们,我久久地沐浴于这样的氛围中不愿离去,以净化自己的心灵……
从纪念馆出来。对我而言,用直古镇还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这就是万盛米行。十几年前,我就给学生讲过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这篇小说的开头就是:“万盛米行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
我刚过一座小桥,远远就看见河边的一堵白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米”字,我知道,万盛米行到了。走近一看,它是一个三开间的店铺,面对河埠。走近店铺,迎面是高高的售粮柜台,上挂“万商云集”广告牌。店铺后是宽敞的石板大院,两廊陈列着稻作农具、加工谷米的各式器具,集江南农具之大成。店铺和院子都十分清净,完全没有《多收了三五斗》里所描写的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不过,在院子一侧的墙壁上,朱红正楷大字展示着《多收了三五斗》的全文。在这样一个特定场合,读这篇自己十分熟悉的小说,我有一种置身于那些“毡帽朋友”之中的感觉。
离开万盛米行,我信步于用直古镇的小街。我想,当年的叶圣陶先生也一定这样信步过。走着,看着,感受着。我觉得我是在进入一页历史,那里有一个丹心映照汗青的老人……
四
旅游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梦的过程。
在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我追寻着一个教育的梦。
我第一次知道春晖中学,是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春晖的一月》和《白马湖》,知道了在浙江上虞的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方。有这么一所美丽的乡村中学,在那里曾经出现过一道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辉煌景观。于是,多次向往有一天能去春晖中学看看。
2002年秋天,我终于来到了春晖。比起当年,校园当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学校仅存的教师宿舍楼、苏春门等几处老建筑中。我还是可以依稀见到春晖旧日的风韵。我走进苏春门长廊,想象着当年朱自清、丰子恺们一定经常在这里散步吧:我情不自禁用手抚摸着那一根根色彩斑驳但依然整齐屹立的木柱,心想朱自清一定也这样抚摸过——这样想着,便感觉到木柱上分明还留着朱自清手掌的余温甚至指纹;我闭上眼睛,就恍然觉得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小路边的山脚下,静静矗立着一排平房。在我看来,这一排朴素的房子。是春晖中学乃至白马湖的灵魂所在。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路边山坡上几间屋子,校长介绍说这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晚年一度居住过的房子。屋子是建在夯实的坡基上面的,我们拾级而上,却没有能够进入房内,因为门锁着而掌管钥匙的人又一时找不着。但我站在石阶上,看着静静矗立的“晚晴山房”,仍能感受到弘一法师的气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由李叔同填词创作的《送别》又在我耳畔响起。此刻正是傍晚,眼前恰好是校园的长亭、山坡下的古道,还有路边的芳草和拂柳以及远方山梁上的夕阳,我感到我正置身于《送别》的意境中。
走过晚晴山房。是夏丐尊的故居“平屋”。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时。朋友指着那书桌告诉我:“夏丐尊就是在这张桌子前翻译完成的《爱的教育》。”我心中一震!我珍爱的《爱的教育》就是在这里翻译的?我第一次知道夏丐尊的名字,是读他翻译的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也是我从教以来给我的每一个学生推荐的必读书,它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教育。想不到,现在我就来到翻译这本书的桌子前,这普通而且陈旧的木桌顿然在我眼中变得神圣起来,我坐在书桌前。久久不愿离去……
紧邻“平屋”,就是朱自清先生的故居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一直把朱自清当作心中的偶像。屋内没有更多的陈设。大都是图文资料,从中我了解到作为中学语文老师的朱自清的一些教学思想。据说先生的代表作《荷塘月色》也是取材并孕育于此的。小屋的门前,原来是一条煤渣小路。先生天天踏着它往来于教室与宿舍之间。后来,先生正是从这小屋走出,走过小路,走到北京、走进清华大学中文系,走向他学术的高峰和人生的辉煌
过了朱自清先生的故居,便是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在几间屋子内,墙上所挂全是丰先生创作的漫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丰子恺被公认为中国“漫画”第一人,而他一生中大多数漫画,包括许多代表作,都是在这“小杨柳屋”里创作完成的。我细细品味着那一幅幅线条简洁、意境优美或涵义隽永的漫画。不止是一种享受,更感到一种思想的共鸣——尤其那一幅幅讽刺非人教育的漫画,不也是对今天应试教育的鞭挞吗?
参观完几位大师的故居,倘徉在故居前的小路上。白马湖水再次映入眼帘。一轮夕阳。在软软的湖水中浸泡着,如喝了喜酒的新郎,醉得微微晃荡。而那绿树掩映的春晖校园便在湖面飘浮着,也在微微晃荡。此情此景,让人不得不遐想:80年前,青春勃发、风华正茂的朱自清、丰子恺们,在这小路上,在这湖中央,或开怀畅谈,或纵情狂饮,青春的歌声和笑声回荡于这湖光山色之间
漫步于白马湖畔,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素质教育之梦,是早已在春晖校园内出现过的真实的景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道景观渐渐失落了,以至于它成了我们今天向往的一个“梦”。
只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拾起这个“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