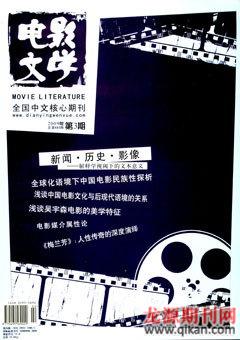爱,美丽而又忧伤
李启军 胡 牧
[摘耍]近年来,学者对越南电影界的代表人物陈英雄电影的镜像特征、人物特征乃至代表性的作品都做了研究。本文从相同地域文化背景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越南影片《青木瓜之味》与中国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影像风格和女性形象进行整体比较,在影像与女性形象之间的隐喻关系、女性的主体性表达、女性存在的真实状况等方面探讨女性和影片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爱,青木瓜之味;我的父亲母亲;形象比较;女性
陈英雄是越南电影界的代表人物。学者们对陈英雄电影的镜像特征、人物特征乃至代表性的作品都做了研究。张艺谋是中国影坛的“教父”。张艺谋导演由于不断追求影片造型、题材等方面的创新而富有先锋性。本文在学人们对陈英雄、张艺谋电影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图从影像风格与它的深层喻指、女性主义的理论视阈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这两部电影。
一、影像的美学意蕴与深层喻指
1悦目的场景呈现
越南陈英雄的《青木瓜之味》较多地使用了长镜头,呈现出纪实风格。长镜头对瓷花瓶、青木瓜等静物的展现,使影片具有一种绘画式电影的风格,唯美而古典。与《青》展现出来的情绪化风格相应的是,该片运用了“重复”的艺术手法,以进行情感上的反复渲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景的重复,如青木瓜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了五次,其中有两次(分别是梅小时候和她长大后)用手触摸青木瓜籽的镜头,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女性的性别特质就像青木瓜一样晶莹剔透,其效果是将梅的温婉气质表达得含蓄隽永、诗意流连;二是音乐和音响的重复,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连贯”,伴随着影片舒缓节奏的是动物的叫声和钢琴乐曲等声音,它们略带寂寥和柔缓的旋律,充溢叙事流程,传递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淡淡意绪,这些元素既直接参与了影片的叙事,又对影片情感基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三是长镜头的多次运用,体现了叙事节奏的重复风格。比如梅切青木瓜的长镜头、梅在屋里行走时的长镜头(伴随知了叫声和低低的音乐声)等,纪实般地反映出梅的真实生活状况和女性情态。
如果说陈英雄的《青木瓜之味》(以下简称《青》)还主要是一种线性叙事的话,那么,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以下简称《我》)则由“我”与“母亲”、“村长”与“母亲”等人意见的冲突开始切换到回忆性的场面,两种时态在叙事中相互交叉。在观影中我们不可忽视两片叙事方式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问题。这里有两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索:《青》为什么选取“梅”的那一段人生,《我》为什么倒叙?为什么重点在倒叙部分,而又要写她的晚年?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陈英雄是为了把握住一个女人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段人生,即在正式获得爱情之前的那段成长岁月。“梅”就是在这段成长岁月中尽显其东方女性的特质和在生活中的真实位置的。《我》之所以要用倒叙。是因为:第一,设置叙事视点的需要。在叙事视点问题上,《青》中是“梅”以主观视点融入主人家的生活场景。而《我》则是以“我”的第三人称视角再追忆“我”的父亲母亲之间淳朴的乡村爱情故事。在两部影片中,对于女主人公(梅和“母亲”)来说,凸现的不是爱情给女性带来的变化和苦涩,而是女性的心愿和爱情本身带给女性的生命质感和情感抚慰。第二,显示爱是一个女人的全部的现状,影片正是通过先呈现“母亲”的爱情缺失状态及“母亲”的反应来加强这种印象的。追忆意味着缺席,意味着爱情这个唯一寄托的缺失。第三,与“母亲”年轻时的性格形成照应。
《我》片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要算该片的影像造型和构图。影片中那充满山野气息的山路、山林、山坡、山村,那给人无限希望和憧憬的翻滚麦浪,还有那老师送学生回家的质朴而温馨的画面,充分体现了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开创的“影像美学”的艺术风格。这些视觉奇观的呈现传达出“我母亲”的浓郁情感,仿佛更是具有正在成熟的女性主体的生命和灵气,更凝聚着“我母亲”性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本体的冲动,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天人合一的优美乡村在带来视觉美感的同时,也预示了叙事发展的趋势。同时,影片中红色呈现出的暖色调是人物情绪的隐喻以及人物在心灵和行动上的情绪色彩,充满着一种饱和的内在力量和外在的生命热力。景与人相得益彰。影像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母亲”是一个敢于追求爱和自身幸福的女性。
2女性的视点:“观看”与“凝视”
长大后的“梅”用水洗脸、照镜子、抹口红等镜头,可谓细腻舒缓,这些镜头说明女性正如拉康所说的进入了镜像阶段。在生活中,女人对镜子的迷恋远胜于男子,女子比男子更像是一种镜恋动物,而镜像阶段正是拉康所谓的“主体”形成过程,在自我与他人二项对立之外,出现了“主体”的“镜像阶段”,这是因为主体人生处于该阶段存在某种匮乏和缺失,而“主体”一旦进入“镜像阶段”,就完成了对匮乏的想象性解决及欲望的产生。女子迷恋镜子,一方面是迷恋于自己青春的容颜,带有一种“自恋”倾向;另一方面是想如何更好地打扮自己,使自己更美。正如“女为悦己者容”一样。这样一来,女子在镜像阶段,开始了一个自恋/情感始发的阶段。接下来,是“欲望主体”利用眼睛“凝视”(gaze)的过程。“凝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看”(look)。主体在凝视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梅对浩仁、“母亲”对“父亲”的凝视和观看就是一种对爱情的投射,是一种使观众在想象中获得的在场体验和抚慰。这两部影片在主体的凝视中所表征的正是爱的缺失。在主体逐步接近并获得爱的过程中,爱尚未到来,这就是一种缺失。换句话说,主体欲望的对象既在主体视野里又尚未为主体所拥有。
另一方面,《青》片于“梅”的动作眼神的细致展现和氛围的营造中显示出古典,婉约的东方女性含蓄、内敛、柔美的独特气质。陈英雄追求意境,淡化情节,回避冲突,有意使梅的女性气质与爱恋情感这两层含义带上朦胧、隐晦色彩。《青》片只可隐约看出“梅”内心深处对浩仁的暗恋。《青》片是一种非常规叙事,影片中知了的声音和隐约旋律充溢了叙事过程,让人感受到叙事的滞缓。影片多次展示“梅”的近镜头,这些近镜头/特写镜头贯穿全片,在青木瓜的韵味和东方女性的气质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如果说对于中国导演来说,很容易从初恋想到未熟的梅子那种青涩的话,那么对于越南导演陈英雄来说,渐渐成长起来的女子以及她们身上渐渐生长起来的那份情愫就像木瓜的琼浆一滴一滴地缓缓下坠的过程那样诗意流连、意味深长。在“梅”的近镜头与青木瓜的空镜头这两者的互相映衬中,凸显出了远在法国的陈英雄欢想中的越南女性所特有的那种温婉气质。
西方著名的现代电影理论大师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电影的实质在于满足观众的欲望,因而影片结构应当间接地反映无意识欲望的结构。这个“无意识欲望”对于《青》、《我》两片来说,就是导演的女性观。女人就是女人,进退两难,她们吁求解放的呼声很难引起男性的广泛
和根本的认同,她们在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世界里无处逃逸。《青》片有力支撑了我们的这一层分析。浩仁的未婚妻作为一个念过书的女人,按理说与浩仁层次相当,他们在爱情上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但《青》片并没按照这个情理叙事。作为有着音乐家优雅,高贵气质的浩仁偏偏爱上了一无所有的女佣“梅”,也许,这是因为浩仁喜欢上了“梅”那种美丽、顺从、柔弱、勤快的传统气质,而“未婚妻”在拥有现代女性所拥有的知识的同时丧失了传统女性所具备的特征。这说明在陈英雄的内心里,他把自我投射到浩仁身上,浩仁成为一个符号,他沉静、优雅、高贵,一如导演自己。由于《青》片是陈英雄的处女作,留有他很深的故国民族记忆,他在影片中追求的是越南民族生活的独特韵味,而这种民族生活的深刻印象,尤其深烙在了他对具有故国民族韵味的青春女性的记忆中了。这点与张艺谋不谋而合,但两位导演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又各有侧重。
从张艺谋所拍电影来看,张艺谋心仪的女性既有传统女性的特质又有一种反叛的生命热力与冲动。这在他以往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中的女主角显露无遗。在《我》片中,“母亲”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也同样体现了一种反叛精神,体现出一种性格的“倔强”。影片一开始,“母亲”执意要把“父亲”抬回来的态度隐喻了无形而巨大的“观念”的力量对女性命运的衬托。与《红高粱》中“我奶奶”传奇式、反叛式的爱情不同,《我》片表明了“传统”力量在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性意味。《我》片黑白与彩色的对比摄影,用色彩反差来刺激感官,流露出真实情感,黑白作为一种暗色调,本身带给人的感受是压抑与悲伤的。而彩色中的红色、金黄色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向上的,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我母亲”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想象(“梅”也如此)——古老、传统而又纯朴。“母亲”形象因其符号性契合了西方人的期待视阈。执导《青》的陈英雄尽管是一个出国多年的导演,但他的“东方血脉”仍然没有淡出他的文化视阀,两片中的女性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还不如说她们是两位男性导演眼中的女性符号。
3观照方法: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
《青》片和《我》片在观照方式上各有特色。《青》片选取一个庭院,采取的是细致显示对象的焦点透视。而《我》片则是采取仰观俯察、远近结合的散点透视。陈英雄长期在法国生活和学习电影,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越南导演,《青》片的拍摄风格,一方面明显采用了西方人焦点透视的观照方式,一方面又颇具越南的地方韵味。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木瓜树上悬着的一个个青木瓜的静态镜头与梅摘取时的表情特写,都将梅的独特气质与青木瓜之间的隐喻联系显示出来,独具越南民族审美情韵。以及那影片中的长镜头长久地跟拍梅,跟拍树下的金色蚂蚁、出水的青蛙和蟾蜍、庭院里的花树等,以及梅纯真、满足的微笑等,无不展现出越南女孩“梅”身上的童稚、纯真、善良、美好心性。同样,《我》片中“母亲”的近镜头与母亲挑水时的远景相互切换,相得益彰。山林画面的起伏、绚丽、深远,在“母亲”的奔跑中不断变换景点,体现出中国人“游目”的取景方式和习惯,使大自然优美和谐的审美境界同女明星本身的符号意味和召唤魅力结合起来,在俯仰远近、物我相谐的审美境界中获得了青春女性的“自我”,反映出生理和心理走向成熟的中国青春女孩的特有神韵:清纯、自然、真挚、忘我。
二、“梅”和“我的母亲”:女性主人公与女性主体
“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这个质朴的乡村爱情故事可以视为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关于女性的自我寓言。从“我父亲”来到三合屯时,在舒缓的音乐下,呈“我母亲”边奔跑边转头的镜头,是“我母亲”用充满渴望和喜悦的眼神欣赏“我父亲”时的兴奋状态,然后切“母亲”脸部的特写镜头。这喻示“我父亲”的到来注定要改变“我母亲”的生活。《我》与《青》两片中女性特写镜头的反复出现,除引起观众的注意力外,也传达出女性内心深处对“爱”的萌动和渴望。东方式的影视女明星显示了东方式的女性类型。两片对好莱坞“明星制”的认同也昭示着女性也可作为男性视觉的盛宴以及对“影视明星是象征性的偶像符号”的旁证,这就可以从中传达出某种深层寓意,再一次证实了女性(包括女明星、女主人公)的被观赏地位;其次,女性特写镜头的反复出现还有利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两片中,无论是《青》片中的跟拍镜头,空镜头、青木瓜的喻示还是《我》片中的远景镜头、空镜头、景物的选取、气氛的烘托等,都是为塑造女性服务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除了推动叙事情节外,就是烘托人物某一方面的特质。尤其是女性在影片中的动作、语言、眼神,特别是在近景、特写镜头中的表情、神态,就成为影片塑造女性形象的十分重要的手段。紧接着,我们就要来分析影片中张艺谋和陈英雄两位导演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
再就叙事视点而言,在《我》片中,整个故事是出自作为儿子的“我”的视角(第一人称自知叙事或全知视角)。而故事是在“我”回家奔丧过程中看见“母亲”对“父亲”难以割舍的场景。这时,整个叙事来了一个大“闪回”——“我”对“父亲”“母亲”恋爱故事的回忆。前文已提及,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也是一个在美丽背景下呈现女性命运的故事。作为男性的“我”充当了第一人称叙事人,决定了有关“母亲”的叙事出自男性视点。正是在选样的视点影响下,我们可以将该片理解为古老的乡村爱情故事:纯洁而美丽。同时,影片潜含着一个男人(“父亲”)对“母亲”的意义(一种吸引和召唤)。为什么说是吸引和召唤呢?因为我们不可忽视影片中这样一个事实,即两部片子中的男性在传统社会中认同的地位(身份和文化层次)都高于女性,正因为这样,才构成吸引女性的一部分原因。“我的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父亲”的到来和因故离开都牵引着“母亲”的心,一是“母亲”的“凝视”和“奔跑”将她的生命呈现为匮乏和缺失的状态。那条通往县城的“路”见证了“母亲”痴情的等待和焦灼的神情。银幕上那点染着红色的山坡、山林以及“母亲”身上穿的红棉袄无一不昭示“母亲”的精神世界。
《青》片则采取了次知视角,即叙事人等于故事中的主人公(“梅”),这样一来,叙事人/主人公的个性就会得到鲜明展现。可以说,《我》和《青》两片都用一种“爱”的自然而然、纯洁美好,缓慢呈现并支撑了女性主体的美好幻觉和行动意义,“男性”作为缺席的所在最后让一份含蓄深沉的爱情有了美满结局。可见,陈英雄、张艺谋都是深谙东方民族情感呈现/表达方式的导演。两片主人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朦胧期待之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是在故事最后才实现。紧接着,我们如果结合这两部影片来谈女性在爱情中的主体性的话,那么可以发现两点,一是女性的勤劳、聪明能干很符合传统观点对理想的东方女性的话语界定和
期待,二是女性主动迎合男性欲望的目光,以期引起对方注意,女性的主体性凸显。从这两方面来看,《青》片中所塑造的“梅”、《我》片中所塑造的“我的母亲”两个青春女性形象,正可以看作越南导演陈英雄和中国导演张艺谋自我生活中某种“缺憾和匮乏”的艺术化补偿。我们进而发现,《青》片和《我》中存在着较明显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起码,在两位导演的潜意识中,都是顽强地固守着一个越南男人对越南女孩和一个中国男人对中国女孩的传统观念的,或者极端一点地说,他们都是未能放弃越南式和中国式男权思想观念的导演。
比较两片,《青》片在影像上虽然呈现了男女最终将完美结合的结局,但不可忽视的是,男性始终是决定女性“幸福”的一个重要参数。男性的主体性较之于女性更为明显。男性在生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男性搞艺术,女性做家务。陈英雄在表达女性的民族韵味时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女性赏玩的态度,他在片中始终没有让“梅”的情欲得到伸展和释放,“梅”在面对浩仁时低头且不断退步的镜头将这层含义表露无遗。再有,我们不可忽视片中“花瓶”这一意象。它在剧中是有隐喻意义的。可以说“花瓶”是女性的象征。供人赏玩且易破碎。“梅”擦拭“花瓶”时不慎将之打碎,浩仁的未婚妻发泄时也将“花瓶”打碎,这些情节都从深层隐喻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宿命。未婚妻在发现自己所爱的浩仁爱的是“梅”时,她除了摔打花瓶等器物,扇了“梅”一记耳光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她只有退让离去,或像少奶奶那样默默承受和担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所以我们可以说,《青》片中的男权思想比《我》片似乎更重一些。除上面提及的以外,少爷的移情别恋、浩仁的高贵气质(音乐家身份)等情节都充分显示:女性是被排除在男性“中心”之外的“他者”。
而张艺谋与之不同的是,他有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雄心,他惯于在影像创新中展示异彩纷呈的“视觉奇观”,他的电影总有一股浓浓的乡土味,我们把它叫做文化乡愁,他又有一种从这些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中挖掘传统底蕴的寻根意识,但是,他的这种寻根毕竟是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而且是走向了大都市的人的寻根。因此,他的电影在彰显民族韵味的时候往往又蕴含着对民族传统中落后一面的批判。我们发现,《我》片中的男性(“父亲”)并没有浩仁的那种贵族血统、贵族气质,但他是县城来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在文化上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看作男性优越于女性的象征。这对于“我母亲”来说很重要。“父亲”最吸引“母亲”的地方就是他是县里来的“先生”。“母亲”一辈子如一日地喜欢听“父亲”教书的声音,也许这不仅是父亲作为男人的魅力,也是现代文明的魅力。虽然“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地位上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但是这里,平等中有不平等。有知识和没知识,在象征的意义上把父亲和母亲分别安置在了现代与前现代、文明与愚昧、男性与女性两种对立的文化境地中了。《我》片之所以大量展呈“母亲”远远地欣赏“父亲”的镜头,反映出的不仅是女性对男性主动的爱和爱的热烈。而且象征着落后乡村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向往、没有文化的女人对有文化的男人的倾慕。“父亲”俘获了“母亲”的心,也意味着文明对愚昧的征服、男人对女人的征服。“父亲”去世后,“母亲”极度伤心,执拗地要走老路把“父亲”抬回来的民俗行为,似乎昭示着“母亲”一如既往地传统和固执,然而,这里更重要的还是表达“母亲”对“父亲”给乡村送来知识的行为的尊重。这里有一个细节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将“父亲”抬回来的都是“父亲”的学生,而且不少还是已经走出了乡村在城里工作甚至做官了的学生。在这个纯朴的爱情故事中,过去与现在时态的交叉,不过是为“我母亲”情感的变化提供一种技术性的叙事因素,突出“父亲”对“我母亲”的重要性。女性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被简化来服从这种“影像美学”的需要。而“父亲”对“母亲”(女性)的要求和期待则丝毫没得到表现,“父亲”在被打成右派期间偷跑回来看母亲,也是因为知道了“母亲”的思念成疾,也就是说仅仅是为了安慰“母亲”。所以,张艺谋在片中隐匿了男性的欲望和权力。然而,欲盖弥彰,正是这有意的隐匿彰显出了男性的欲望和权力。我们也可以把“我母亲”织布做饭的行为看作是附着于男性的一个表现,陪伴“我的父亲”更是似乎成了“我的母亲”的宿命。她们对男权文化是一种麻木或者说是宿命的认同。女性奉献于家庭,男人奉献干事业,似乎顺理成章。这里导演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暗含了一种男女性别的隐喻·二是认为女性迎合男性欲望目光/审美趣味的是还原女性特质。每个镜头都呈现了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与形象,一种美丽而又叫人忧伤的幻境与形象。
《青》、《我》两片将女性生活化、传统化(坚守厨房等)的策略,实际上一方面将男性传统价值观念移注到女性身上,另一方面又剥夺了女性在更高价值系统(比如事业、创造等)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从而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陪衬和助手,甚至仅仅作为男性的欲望客体而存在。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女性为核心人物的电影并不一定保证该女性的主体地位。如《青》片中的“梅”简直是沉默的羔羊,她根本没有主动的“说话权”,而《我》片中的“我的母亲”也基本没有摆脱作为男人附庸的命运。我们在此想提出判断一部电影是否重视了女性的自由主体性是具有一定标准的。一是题材标准;二是导演文化身份标准。在反映女性生存状况的电影的文化特征方面,题材选择是很重要的。但仅有题材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导演的性别立场、文化身份问题。后者往往决定前者。因为,后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前者,而且还包括在题材选择上的性别话语立场。叙事的倾向意味着权力的倾向,两者是顺化关系。《青》片保持了影片的越南化,而且是越南化的男权中心主义,《我》片保持了影片的中国化,而且是中国化的男权中心主义。尽管陈英雄深受法国文化熏染,但却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法国电影,《青》片的题材、场景、人物蕴含特征等都足以说明它的越南特征。《青》是陈英雄明显带着越南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立场来拍摄的。而《我》片中那红棉袄、青瓷碗、土炕头等也凸现出了张艺谋身上中国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立场。两部影片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契合了两国观众尤其是两国男性观众的审美习惯和观影心理,符合两国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对具有特殊民族气质的美丽、温柔女性的想象和认同。
三、结语
本文从两部片子影像和叙事风格出发,深入比较两部片子中的女性形象,尽量挖掘影响影片本体的东西和民族文化深处的东西。两部片子中的女性都有着各自民族女性温顺、勤劳、智慧的特质。我们通过上文对两部影片影像风格、观照方式的分析可以判断,陈英雄、张艺谋两位导演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美是一种去修饰化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女性外表和内在的美用大自然之物的美来象征,来衬托。但是,由于越南与中国的地域差异。他们寻找到的象征意象是极为不同的。比如,出身、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张艺谋很难会想到木瓜树和青木瓜的意象,出身炎热越南的陈英雄也很难想到红棉袄的意象。“厨房”这一作为东方女性“性别化”和符号化的阵地,在陈英雄和张艺谋的影片中,仍然各有自己不同的处理,呈现出各自别具一格的意味。当然,两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总体上都属于具有越南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男性导演,对分别具有越南和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善良、美丽有如“天使”般的女性的想象和镜像化再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徐坤的小说《厨房》对女性存在状况的打探,也让我们想起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的女性立场的宣言。然而,遗憾的是,两部片子对女性的立场和意识暗合的是前者,而不是舒婷的宣言。尽管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都是男人对女人的歪曲性的想象,但是“天使”毕竟是男人们寄希望于女人们的一面,“妖妇”毕竟是男人们痛恨女人们的一面,所以,影视观众们,尤其是男性影视观众们,可能并不以陈英雄和张艺谋的歪曲为歪曲,还可能会大加赞赏之。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