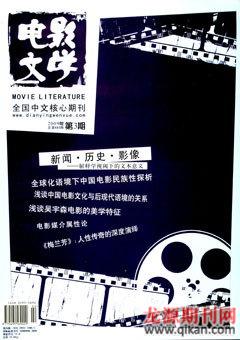浅谈中国电影文化与后现代语境的关系
杨 杰
[摘要]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文化是一种对世界的意义深感不信任的文化。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也是产生后现代文化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的娱乐性商业电影中,后现代性却是和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传媒手段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语言阶段、文字阶段、印刷阶段和电子传媒阶段。本文从后现代语境、电影的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几个方面阐述了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电影文化
一、后现代语境
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也是产生后现代文化的社会背景。人类传媒手段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语言阶段、文字阶段、印刷阶段和电子传媒阶段。电子传媒的重要特点就是用图像符号替代了非具象性的符号,由于它用具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消除了人们的知觉与符号之间的距离,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消除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电子传媒的这一“优势”使它不仅替代了印刷媒介的权威地位,而且迅速地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人们越来越满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外来信息,越来越迷恋于直观的复制形象而不愿意进行个人的阅读或思辨,越来越关注流动的现象而不是恒定的主体,于是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恩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中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他人引”的社会,传媒滋生了一种“从众心理”,因而后现代文化也是一种大家公有、共享的高度平面化的文化。
后现代性文化是后现代文化的主体,也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市场的主要商品,因而它必须满足消费者直接的实用目的,必须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来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这是一种平面性的文化,它既不需要通过对现实境遇的揭示来唤起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觉悟,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的期望来引发人们的实践热情,任何深度的出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往往有可能扩展文化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影响到它的商业价值。而后现代语境,正如利奥塔德所说,则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它用价值颠倒、视点位移、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一切恒定的常规、秩序,来表明它自身的不确定性,它用反讽和玩笑来揭示所有既成的对世界的解释的人为性和虚假性,但它却并不想用新的阐释系统来取而代之,它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自由的流浪者,没有家园的快乐的单身汉。
二、后现代性:电影游戏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影厂走向了企业化,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不得不意识到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需要获得经济效益的工业产品,因而他们只能忍痛割爱、委曲求全,暂时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艺术个性,勉为其难地拍摄所谓的娱乐片。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关于电影的“娱乐性”的讨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的电影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五代”导演的中坚之一的田壮壮在他的《摇滚青年》中率先宣布:“怎么开心怎么来”,当年“为下一个世纪的观众拍电影”的豪言壮语变成了一种堂·吉珂德式的笑话,电影不再追求“第五代电影”那样的个人风格,也不再迷恋于那种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而是要让尽可能多的观众感到愉悦、畅快,电影不再是一种美学创造,而是一种能满足大众无意识梦想的“实用”消费品。于是,“第五代”电影人纷纷改弦易辙,田壮壮拍摄了充满一种浪漫情怀的青春影片《摇滚青年》,张艺谋拍摄了反劫机的惊险片《猎豹突击队》,何群则从《西行囚车》到《烈火金刚》,直到《消失的女人》,一直在乐此不疲地拍摄着商业性的情节片。娱乐性影片很快成为数量上的主体。而这种电影观念的转变还并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受到商品逻辑的支配,而且也因为人们对所谓的美学深度已经深感怀疑,当人们把这种深度嘲笑为故作深沉时,他们为那种后现代的平面已经开辟了道路,于是,电影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电影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它也割断了与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文本。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对世界的意义深感不信任的文化。但在中国的娱乐性商业电影中,后现代性却是和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西方商业电影是以对主流观念的一种有限的偏离来释放观众的弑父情绪的话,那么中国电影则是通过对主流观念的有意识的认同来淡化它的精神分析功能。从1989年的《龙年警官》开始,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而被采用。《焦裕禄》成功地将一个共产党人塑造成为了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忍辱负重的传统人格,使这一策略的潜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是,任何主流观念都意味着对想象界的一种抑制和规范,都企图为那个展示着快乐原则的电影游戏赋予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而这与商业电影的运作机制并非没有矛盾。蹒跚在商业化和主流化双重轨道上,这种“一仆三主”的现象,也许正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后现代特征。
三、后现代主义:游戏电影
后现代性文化是商品经济的直接现实,它通过文化游戏来牟取暴利。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话语表述,它通过游戏来拆解深度和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只是一种舶来品,它的滋生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新时期刚开始,不到十年,人文主义旗帜就在商品经济的沧海横流中风雨飘摇。价值观念的频繁位移,暴露出了所谓“永恒”真理的“永恒”性只不过是对其“暂时”性的一种策略性掩饰,任何关于世界的认识和阐释,都是人为的,都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动机。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本原的世界,而是一个被符号化的意义化的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觉知,后现代主义对神圣性、秩序、常规、传统,甚至一切概念、符号都深感怀疑,它不仅怀疑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怀疑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甚至也怀疑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和形而上的追问,我们不能走得太远,这样会致使我们去猜测。于是,对深度的拆解、消解,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
这种后现代主义观念在苏童、余华。池莉、方方的小说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述,而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表达则不得不更加隐晦,更加具有某种策略性:它必须意识到它对深度的拆解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和一定的限制中进行。因此,中国几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电影,但中国电影中却已经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性特征。
这种特征最突出地表现为它常常通过否定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网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来与这种状况对立,它把这张网看做是某种偶然性的产物。它对为现状提供永恒性解释持怀疑态度。它否定正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概念、否定以对善与恶的机械划分或以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为基础的对于世界的解释。1987年,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最早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作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解释。周小文在《疯狂的代价》中用小女孩那无所谓的泡泡吹破了姐姐孜孜不倦的复仇行为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一批城市幽默喜剧,如《大撒把》、《上一当》、《站直罗,别趴下》等影片,对种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和历史观念作了调侃式的嘲讽。而《三毛从军记》则大量采用了反讽、戏拟、类型混杂、滑稽模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手法,不仅对历史、战争、英雄作了重新解释,而且也对电影作了重新解释,从而暴露了这些解释的“非必然性”和其意义的“非真实性”。
后现代文化所受到的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它的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千篇一律的“复制性”。本杰明指出,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于精神的复制,“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的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言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在我们突然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时,我们是否还有从容处理的能力和意识?当我们放声讥笑着普罗米修斯之后,还会有谁再愿去盗来圣火?当后现代文化在商品经济的大潮裹挟之下横扫着我们的电影和整个社会时,保持几分清醒和冷静也许并非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