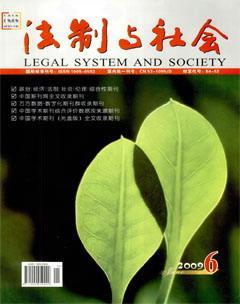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马骏逸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主要通过股权的买卖来实现,狭义的股权转让仅指股权买卖行为,而广义的股权转让则还包括赠与、继承、互易、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公司收购等特殊形式。本文仅讨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问题,针对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138-01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法律规定或约定而享有的于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 。股东优先购买权属于先买权的一种,对于权利人而言,只是购买机会上的一种优先待遇,而非购买条件上的优惠;对于义务人而言,只是自由选择出让对象的权利受限,而不承受实质上的交易损失。具体
分析如下:
一、“同等条件”的确定
《公司法》第72条第3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但对“同等条件”应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未作明确。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立法中的漏洞,因为《公司法》第72条第2款明确要求拟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这是《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过程中拟出让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仅有的一处规定。可见,向其他股东书面通知股权转让事项是启动股东同意程序的第一步骤,也是其他股东了解第三人受让条件的唯一法定途径。而该款中的“股权转让事项”既是其他股东进行股东同意程序表决的基础,也是其他股东确定其是否要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故“股权转让事项”与“同等条件”应指向同一内容,即拟出让股东与第三人已达成一致的股权转让的全部条件,一般应当包括“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及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以及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 。
二、在股东同意程序中同意转让的股东能否享有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第72条第3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此处的“其他股东”单从文义解释,是指除拟出让股东以外的公司股东;再辅以体系解释的方法,联系第72条其他各款中“其他股东”的涵义,亦作此解。异议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自无疑义,问题是“其他股东”中的同意股东能否主张优先购买权。有观点认为,“如果赋予已经同意转让的股东以优先购买权,那么有违于法律本旨,无异于允许股东反复无常,有害于交易快速便捷地进行” ;还有观点认为,“在转让方征求意见时已经表示同意转让的股东,其同意即意味着对购买权的放弃,如果股东在表示同意后又主张优先购买权,不仅违反诚实信用,而且对受让人也有失公平,不利于加速流转和维护交易安全” 。
三、拟出让股东是否必须向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转让股权
作为商事交易的主体,股权转让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同样享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但由于受到公司法的特别规制,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根据《公司法》第72条第3款的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笔者分析,在股东同意程序已获通过的情况下,如有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拟出让股东实际要面临以下三种选择:一是仍坚持要求股权对外转让,由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二是放弃股权出让,继续持股;三是放弃股权对外转让,同意将股权对内转让。第一种情况,其他股东愿意在同等条件下受让股权,而拟出让股东又坚持要求出让,那么拟出让股东就只能向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转让股权。对于第二种情况,拟出让股东在其他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宣告放弃股权转让,当然有权继续持股。因为,“股权转让行为是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必须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双方就转让的出资、数量、价格和交付期限等主要条款达成协议才能成立” 。即使是其他股东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也是以拟出让股东作出“坚持要求股权对外转让”的选择为前提的。毫无疑问,在股权转让问题上拟出让股东的意志是不可或缺的,相关法律后果的产生至少也是法定与意定相结合的产物。法律只是部分地限制了拟出让股东选择出让对象的自由,而未剥夺拟出让股东选择是否出让股权的自由。拟出让股东愿意向第三人出让股权并不意味着其也愿意以“同等条件”向其他股东出让股权。总之,笔者认为,并非只要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拟出让股东就必须向其转让股权。
四、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
《公司法》对股东同意程序规定了答复期限,该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公司法》也就强制执行所致股权转让中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规定了行使期限,《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偏偏是对一般股权对外转让中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现行《公司法》未作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笔者认为,在公司实践中,这种期限的模糊性将造成优先购买权在程序上的不确定性,从而损害拟出让股东、其他股东或拟受让第三人的商机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立法缺失虽可通过法官的审判解释予以弥补,“遵循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原则,合理地平衡股权出让方、受让方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但易导致司法尺度的不可预见性。例如,一审法官认为“三十日”为优先购买权的合理行使期限,当事人或二审法官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二十九日”或“三十一日”就不合理;况且,法官的判断是事后裁量,当事人在事先又如何得知,将此类期限问题交给法官去自由裁量将使得大量的股权转让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显然不符合法律的经济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