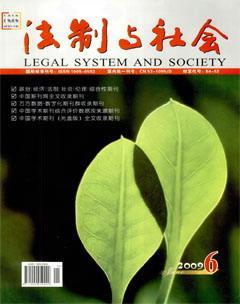浅议中西法文化的比较
陈柳翀
摘要中国和西方由于在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状况、传统伦理思想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在法文化上向来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差异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15-02
“西法东渐”是中国当代法制建设一个尤为醒目的变革趋势。由于法制现代化必然要涉及社会文化及其精神价值基础的变迁,适当借鉴域外先进的法制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法制文明成果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囫囵吞枣,而应取齐精华,去其糟粕。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究中西法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就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认识和了解这种差异,就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进程中,有针对性地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文明成果,自觉吸纳人类社会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培育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制文明。
一、人治与法治
(一)中国古代法文化:人治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国家政治主要应依赖贤人,其次才是法律。荀子曰“君子者,法之原也”便是典型。意即治国的根本,第一位的是贤人,法律是第二位的。贤人何以比法律更重要?儒家以为:一是法要贤人来制定;二是法要贤人来执行。贤人在执行中会使不善之法以纠正,而善法如让小人去执行, 只会祸害无穷。①但以法家为代表,包括汉以后的某些先人,则认为法律比贤人更重要。一为贤人难得,而法律唾手可得。韩非认为,象尧舜这样的贤明君子,千世才出一个。世上更多的是智慧平平之君。他们如掌握了法律这武器,一定治得好天下。二为贤智虽好,却无强制力,只有法律或刑罚才能立竿见影令人服从。在经历了春秋时期政治保守派(儒家)“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的观点与政治革新派(法家)“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观念的大碰撞之后,终于在西汉中期确立了由儒家学派提出的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思想,即“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通过以上先秦“任人”、“任法”两派争论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两派貌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其骨子里却都承认贤人的绝对价值要大于法律,即使是提倡"以法治国"的法家也只是将法律作为其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人治主义”,强调以“礼”、“德”为主教化人的思想,法律只是作为训化臣民的辅助工具,用来惩戒那些违反礼教、道德的行为,而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大臣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二)西方古代法文化:法治
在西方,从最早希腊城邦时代的理想主义法哲学代表人柏拉图开始,“依法治国”便成了西方法律哲学的主导思想。尽管早期的柏拉图主张最好的政体是“哲学王”统治的以人为主的政体, 但在其后期的思想转折性著作《法律》一书中,受两次西西里之行影响的柏拉图已用“法律主治”的思想取代了其一直推崇的“哲学王之治”思想。柏拉图指出,“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是新理想国最重要的特征。这事关城邦生死存亡,因为当国家不依靠'哲学王'而依靠法律来统治时,一旦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以法治国就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统治者(一人或集团)可不受法律制约,甚至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柏拉图《法律》中的法治观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不在于它的具体构想,而在于它的主要精神。随后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治国优于一人治国”思想,洛克《政府论》中的“立法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法律权威至上”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法律公意说”思想等等,都在英、美等国的宪法规范和宪政实践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体现。②
二、中西法文化差异的缘由
(一)“重农抑商”与“重商政策”
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主要成型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小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是土地,而封建统治者在牢牢控制土地的同时,也牢牢控制 着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经济形态和经济关系决定了:(1)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长期采取“ 重本抑末”、“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在法制上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2)由于受狭隘的封建经济关系束缚,个人只有依附这种关系才能够生存,因此个人不具有独立发展的条件,也就不可能生成自由自主的主体权利意识。(3)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小农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广泛的联系,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并且“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③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就存在着普遍的皇权崇拜和严重的贱民意识。(4)与自然经济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相适应,人们习惯于把家庭和家族内部的首属关系泛化为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个人都是带着主仆的社会规定性而发生联系,并严守各自的身份与等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普遍平等的权利可言。
西方国家很早就以交易行为为基础产生了商品经济,很早就出现了商人阶层和商人社会,并产生了“ 罗马法”。商品经济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培育了西方的法文化,并使其产生以下法律思想因素:(1)主体权利意识。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打破人的依赖关系,超经济的剥削和奴役关系不再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人们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人身自由,成为自主的市场竞争者,并在其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主体权利。(2)契约自由意识。市场经济的力量,冲破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个人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有买卖和契约行为的自由。(3)平等和民主意识。商品交换需要买卖双方奉行自愿和平等原则,并且非协商一致交换不能实现,商品的生产者和交换者不是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而是根据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决定其行为,因此商品经济总是以人的独立和平等为前提。④所以,西方法文化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影响,生成了主体权利意识、契约自由意识、平等和民主意识等,具有极力维护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
(二)社会结构:封闭与开放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国家起源方式影响,长期主要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亲亲、尊尊意识去维系的。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又利用儒家文化,通过明亲疏贵贱、别父子夫妇的纲常礼教,把人们进一步置于宗法等级秩序和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又建构了极端专制的封建法统,以家族宗法为依托,以官僚法制为支撑,极力维护着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体系和结构。首先,通过家族宗法以及邻里的连带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的连坐等措施,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其次,通过官僚法制,加强对官吏的控制,把封建专制统治落实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封建皇帝集国家权力于一身,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行政管理者和司法审判者。在这种封建法统和法文化精神的调节下,宗法亲情关系被演绎成为人性的桎梏,使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法律和诉讼不是保障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手段,而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和封建专制体系,对人们实施惩罚的工具;国家的管理任由封建帝王及其统治集团操控,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也促使传统中国也因此成为典型的“人治”社会。
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形成较为开放的社会结构,因此相对来说,家族血缘关系并不十分重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城邦之间,更多地是表现为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以个人自主、平等为前提,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的主体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增强。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这时西方在追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充斥整个社会,并进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即要求建立起一种能够保持社会有机制衡的政治法律制度,以避免公共权力为专制独裁利用,避免专制势力粗暴干涉平等的自由竞争。⑤本着这一精神,近代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并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原则。近代西方的法文化,之所以能够极大地促进和保障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使西方形成了能够推动社会平稳发展、保证最大限度减少内乱的权力制衡和调节机制,这种机制围绕着民主和法治展开,并促成了西方社会的“ 法治”化。
(三)“法伦理”与“法理性”
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自然的本质或灵魂,不是理性而是伦理,是宗法伦理。中国人要“法自然”,就是要效法自然中所体现的“伦理”,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或恢复、加强人间的以伦理秩序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⑥而传统的伦理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伦理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违反人的本性,即要受到处罚。所以,中国传统的法治都是围绕着“人-伦理”而展开,伦理高于法律,伦理既是法律。
而西方以“理性”为准则,他们认为,“自然法”基于人类的自然状态而自生,无须人民制定;“人定法”是人们有意制定的。自然法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的制定标准和依据,人定法是自然法的实现。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约定,有善恶之分。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便是恶法。显然,这种自然法是超脱了伦理界限的,这种自然理性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据此识辨真伪、善恶。⑦正因如此,人民很少讲人定法律神化,而是经常讲到“自然正义”、“自然平等”并反对君主暴政。
(四)地理位置:大陆与海洋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较为封闭,使得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缺乏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客观条件,法文化的发展十分缓慢。最终形成了很强的思想惰性,容易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对外来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有着顽固的拒斥心理。虽然历史上中国也经历了很多次的朝代更迭、战乱中兴以及变法图强,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一直到晚清,大一统的专制格局就从未改变。无论何朝何代,人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诉求,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都是高度一致。与之相应,中国的传统法文化也是迟滞不前,例如在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社会普遍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习惯,都是惊人的雷同。这种僵化的文化模式和因循的思想特性,也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学习、尝试和建立新的法律制度的每一步上,都显得步履蹒跚。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海洋地理特征,带来频繁的航海贸易,也带来了广泛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从而为西方法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作为西方法文化源头的古希腊和罗马,分别位于濒临地中海的两个半岛上,频繁的海上贸易,使它们很早就成为开放型的社会。而作为欧洲“ 普通法系”发源地的英国,与“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之间,也仅仅相隔一道很早就可以通航的英吉利海峡。西方的海洋地理环境,以及它在历史上经历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动荡,导致了西方各种源流的文化之间,产生了广泛地交流、碰撞与融合。在各种文化的长期交锋中,旧的、落后的因素被扬弃和改造,新的、先进的因素被保留和发展,于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就形成了相互的影响和补充,从而就推动了西方各国文化的不断进步。这一文化上的交融与发展过程,自然也将西方的法文化包括在内。
三、重构当代法观念
中国社会从未摒弃过“人治”思想。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尽人意,并不能一味归咎于“人治”思想的严重,从如今西方“法治”国家开始不断吸收我国传统“人治”思想中可以看出,“人治”经历了无数朝代,见证了无数兴衰,是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的。因此,我认为中国法观念的具体行动中,至少要实现以下几大转变:首先,在社会关系上,要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彻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身份关系,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中契约自由的精髓,使之不仅体现于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而且体现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其次,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中,要实现从“国家本位”、“权力本位”到“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积极倡导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即可为之,国家权力不予干涉。再次,在治国方略上,我们既不能象儒家那样将人类道德、历史责任感提到空前伟大的高度,以“人治”论,也不能唯西方“法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