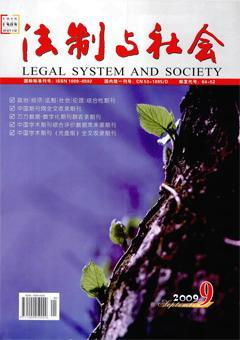试论健康权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赵彤彤 杨智红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诸多危害人们健康的事件,艾滋病、疯牛病到肆虐的非典型肺炎和最近在全世界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吸毒的泛滥、自杀率增加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说明健康这一伴随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要求,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的生活方式,而在普遍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标准,人的健康问题自然倍受关注。人们健康意识在不断的加强,对健康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用保障人权最有效的手段――法律来保护人的健康以及健康权问题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当今重视的热点话题。
一、健康权的含义
作为一项权利,健康权在中国学界一直没有权威统一定义,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公认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国际法层面上对健康权的表述,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章程首次这样确认健康权“获得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的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
我国民法学者关于健康权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3种:(1)认为“健康权者,不为他人妨害,而就自己之健康,享受利益之权利也”。(2)认为健康权是“以保持身体内部机能之完全性为内容的权利。”(3)认为“健康权是公民以其身体的生理机能的完善性和保持持续、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为内容的权利”。认为健康权应是与生命权、身体权并列的一种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有生命健康权,在民法学中曾将生命权与健康权作为一项权利,近年来,学者逐渐认识到生命健康权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统称,健康权是一种独立权利已成定说。将健康权定义为“独立的人格权,即公民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它包括健康维护权、劳动能力保持权和健康利益支配权。”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民法学上对健康权的一般定义。至于公民的健康权包含哪些具体的权利,民法界学者对此观点不一。《民法通则》第119条仅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造成死亡”的民事责任,显然没有将心理健康权包括在健康权中加以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的心理健康也往往被忽视。我们认为,健康权应包括生理健康权和心理健康权两项具体的人格权利。
健康权概念在不同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健康权范围不能过于广泛,那种认为健康权“指自然人以其生理机能运作和完善发挥,以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健康权包括自由和权利两个方面,其中包括自身健康免于干涉的自由,也包括获得卫生保健以及健康所需要的安全的商品、清洁的水源和信息等权利。”是不够合理的。因为健康权的范围界定得过宽,会导致法律保护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健康权的法律保护也就子虚乌有。认为健康权就是“保有健康的权利”的观念,也过于宽泛。试想,一切侵害或者影响公民健康的因素均包括在健康权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人就没有生病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死亡的可能,这显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何况,食物的供给以及适当的住房可以在食物权以及住房权中分别得到保障。笔者研究健康权的概念是强调人维持健康所需的一系列基本的健康服务。因而,笔者比较同意蔡维生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健康权定义的看法,即所谓健康权是指公民享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和要求国家为公民实现健康提供必要保健条件的权利,对此权利的实现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可见,健康权并不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一切事宜,是公民在躯体和精神正常运行的情况,获得国家健康保健的权利,国家应当成为健康权的主要义务主体,利用尽可能的资源为实现公民健康承担给予必要健康服务的责任。例如,主要传染病的免疫注射、孕期和儿童健康保健,包括计划生育等等。
二、 健康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有关健康权的国内法规定
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纲中的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宪法第26条对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与公民健康权有密切关系。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第42条对劳动保护权做出了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5条对医疗救助权做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可见,我国宪法第21条,从规范国家义务的形式,承认国家有责任保证公民的健康,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隐含权利的界定。
虽有以上规定条文,但是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确认健康权,而是以规范国家义务的方式来承认健康权在我国的存在。正如杨海坤教授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相比,就会发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规定的不全面或没有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达30项,其中包括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的权利,这些基本人权,应载入我国宪法。“我国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内容过于原则化,规范表述过于笼统和概括,以至于对某些公民权利在理解上产生分歧。”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在21条、26条、42条和45条有健康权相关的规定,但是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并没有规定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健康权,使得其程序性规范明显缺位。没有相应程序规定的权利是一种裸体的权利,只能流于宣言式口号效果,无法产生实际健康权的保障作用,这就为我国健康权的实施带来了隐患。
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民法的规定是从私权的健康权角度加以保护的。而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是宪法性权利,因而这个私权的健康权显然不能涵盖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内容。再者,从民法对权利的保护角度来看,民事诉讼采用的是典型的“不告不理”的诉讼机制,“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法律知识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诉讼困难),就难以得到民法保护。即使得到民法保护,那也是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得被侵害者得到补偿。损害补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在已经出现损害后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这对保护健康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显然不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其中第三章第一节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第六章第五节对于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直至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健康权保护的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以产生了健康损害后果,因此都是事后救济措施,重点是事后惩罚,而不是事前预防和保障。
除以上基本法之外,我国针对医疗卫生专门领域颁布的众多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今年刚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中,也没有几部法律中明确提出健康权的,即使存在个别法规中有健康权的界定,我们认为也是不合适的。如此重要的权利居然由如此阶层的法律来规定,不能不说是对健康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的默然和无视。
我国针对特定人群的权益保护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诸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颁布施行)中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卫生机构在老年人医疗保健方面的义务做出了规定。《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新修订)第二章对国家和社会在残疾人康复方面的义务做出了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新修订)、《母婴保护法》(1995年施行)等一些对特殊人群权益进行保护法律中,无一例外的都没有明确提出健康权的说法,而仅在保护人身权利或是社会保障权益中笼统提到。
我国专门应对突发事件包括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颁布实施),规定了国家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保障社会安全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保护公民健康权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突发事件应对法》虽然强调了“比例原则”,限制了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行为,但却没有明确即便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也不得侵犯的公民权利,所以,该法的“维权”色彩不强,在实践中很容易被理解成仅仅是政府有权采取紧急权力的法律,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二是各地相应的实施细则的制定还比较滞后,尽管《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原则比较清晰,但是,由于全国各地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的类型不太一样,所以,在突发事件应对实践中,有必要制定一系列针对本地具体情况的实施条例或规定。
总体来看,我国有关健康权的法律法规虽然覆盖了健康权所涉及的多个领域,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层次参差不齐,效力有高有低,较高级别的法律中,特别是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健康权。而一些明确规定健康权的法律法规不是健康权内容规定不全面就是效力级别较低,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此外,保障公民健康权也不是仅仅依据个别法律之功就能显现成效,这是一个综合运用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和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的一个联动工程,此外还需要国家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医疗硬件设施相配合。从立法角度考量,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明确作为基本人权的健康权的法律地位,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健康权,并补充相应程序行性规定;再依据宪法制定和完善其他法律法规。如果健康权不入宪,则永远改变不了健康权立法混乱,执行不力的现状。
(二)我国加入的有关健康权的公约
中国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2月28日对中国生效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其中第五条规定“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包括“享受公共卫生、医疗照顾、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的权利”。
中国于1997年10月27签署,2001年3月27日交存批准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
中国于1980年7月17日签署,12月4日对中国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其中第十二条规定“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保健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取得各种保健服务,包括有关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和“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给予免费服务,并保证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得到充分营养”。
中国于1990年8月29日签署,1992年4月2日对中国生效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康复设施。缔约国应努力确保没有任何儿童被剥夺获得这种保健服务的权利”并且“缔约国应致力充分实现这一权利,特别是应采取适当措施:(a)降低婴幼儿死亡率;(b)确保向所有儿童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和保健,强调发展初级保健;(c)消除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包括在初级保健范围内利用现有可得的技术和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和清洁饮水,要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危害;(d)确保母亲得到适当的产前和产后保健;(e)确保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父母和儿童介绍有关儿童卫生保健和营养、母乳喂养的益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防止意外事故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得到这方面的教育并帮助他们应用这种基本知识;(f)开展预防保健、对父母的指导及计划生育教育和服务”。
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法》、《国际卫生条例》、《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精神药物公约》以及确认“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阿拉木图宣言》等一系列的与健康权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宣言。
这里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国际公约或条约如何在我国适用的问题。我们知道,国际公约或条约并不能像国内法那样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直接依据或是作为执法者行使职权的依据。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经过转化或纳入程序。所谓转化,就将条约规定为相应的国内法形式,间接适用。而纳入,则是指将条约一般性地纳入国内法,在国内直接适用。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取决于国际公约或条约的性质和有关规定。
在我国,无论是宪法还是《立法法》等一般性法律都没有就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和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内的适用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两者在国内适用中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政策和态度。在实践中,一般都通过解释而一致起来,和谐起来。那么这些国际公约或条约与国内法相比,效力如何?根据《宪法》第64条第2款: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宪法》第67条第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宪法》第8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宪法》第89条第9项: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具有与国内一般法律同等的效力。第二,凡是由国务院缔结而不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条约,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即效力低于法律。那么我们利用国际公约或条约来保障健康权还有待国内法的承认和消化。
国家作为健康权的主要义务主体,应利用尽可能的资源为实现公民健康承担给予必要健康服务的责任。我们希望通过健康权入宪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一个完善的保障公民健康权的法律体系,充分实现公民的健康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