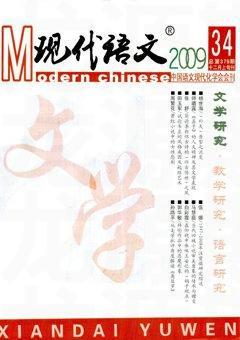在仰视中体味王安忆的“鸽子视点”
摘 要:王安忆在其小说《长恨歌》里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鸽子视点”,通过“鸽子”所处方位的高和远,见识的广和杂,入目的细与微,用情之深和切,透视出的却是作家深挚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鸽子视点 悲悯情怀 生命智慧
我们不妨先鉴赏一下《长恨歌》的开篇一段,看“鸽子”是以什么样的形象与气势进入读者的视野的: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划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这是比较锐利的一笔,带有揭开帷幕,划开夜与昼的意思。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色,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锈,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
小说一开篇就来了这么一句:“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显然,这是作家在给我们介绍“上海”这座城市了,可奇怪的是,她怎么一下子就把聚焦点滑向了对“上海弄堂”的扫视上?一个“站”、一个“至高点”,毫无疑问,作家已经把“看”的主体预先放置到了一个远离了凡俗视野的“至”高位置上——王安忆继而向我们推出的是一个有着“壮观”景象的“上海弄堂”,但实际上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的弄堂”并非如作家所言是“壮观”的,恰恰相反,它还有些逼窄、拥挤、破旧和杂乱,甚至因为四面八方都是个参差不齐、密不透风,常常还会令人感到有些压抑和窒息。可作家在这里用的显然不是沉溺于其中的“人”的眼光,人的眼里“上海的弄堂”首先是无法“壮观”起来的。其次,既然上海的弄堂如此的“壮观”,它就不能被形容为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了,而应该是舞台前耀眼夺目的一个主体形象的。显然,能把“街道”和“楼房”凝缩为“点和线”,把夜幕下的弄堂模糊成“波涛汹涌的暗”,并且把这“暗”还可以看成是“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的视域,它一定不是人的视域,退一步说,它即使是人的视域,也一定不会是一个肉眼凡胎的人所能达到的有限的视域。
鸽子就这样出场了,不是以身体、声音、影子等等的直接形式,而是以极为间接的姿态——只让它的视觉来参与对这个盛世里的大都会城市的审视和度量。
徐德明先生认为王安忆对扬州评话的传统叙事与西方现代派等手法进行了有效的吸纳与整合,然后在《长恨歌》中,她才设置了一个从上空俯视整个上海的“至高点”,他把这个至高点命名为“鸽子视点”。也就是说,站在这个“至高点”上俯视“上海”及“上海的弄堂”的,其实就是一群鸽子,一群成年栖息于城市屋顶、整天奔波于我们目力难及的天空之上的超凡脱俗的“鸽子”。他说,“鸽子在这里执行着一种介于人神之间的功能,它是王安忆作品中审视生命的智慧态度。这种民间叙事的智慧是一种包容一切的襟怀,颇有点观音式的普度众生的意味,写作的主体看得众生与一切事物分外的明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对众生平庸的而具体的生活的一种深切的体察和认同,一种充满兴味的呈现欲望,一种民间社会的叙述自觉。”[1]
简而言之,什么是“鸽子视点”?“鸽子视点”就是王安忆在其长篇小说《长恨歌》里所使用的一种叙事视点,因为她不是用人的眼光,而是借用了“鸽子”的眼光从高处鸟瞰着上海这座大城市,并表达着对人类苦难与罪恶的深切怜悯与关怀,故而徐德明才首次提出了“鸽子视点”这个概念。当然,这种视点并不新颖,也不是王安忆个人的一种首创,在我们古代文论里,它其实又叫“第三人称叙事”,或“全知全能视角”。王安忆只不过是将“俯瞰者”巧夺天工地置换了一下,使其由以往的“神”、“灵”或“全知全能的人”变成了一群鸽子,因此才使这种老手法无意间产生了起死回生的艺术新效果而已。
参照徐德明对“鸽子视点”内涵的界定,如果我们再结合整部《长恨歌》里作者对“鸽子”所寄予的一些象征意义,于是就会发现“鸽子视点”其实还是具备了以下一些特征的。
一、方位之高、远
包括鸽子所处位置的“高”、所波及范围的“远”,以及其所表现出的精神境界之“幽深”和“沉郁”,它不仅是人类不可企及的,也是它的同类所望尘莫及的。
实际上,鸽子以主角现身,以正面示人,是一直到了《长恨歌》第一章的第四节里。在这一节,作者以泼墨之势,意味深长地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深邃、博大的“鸽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鸽子是主宰,是这个城市里的“精灵”一样的东西。所以它被安排到了这个世界金字塔顶端的位置。而围绕着鸽子的存在,作者还为我们依次塑造出了以下这样几类陪衬的角色形象:其一是人类,作者称其为“两足兽”。在王安忆笔下,他们是“行动不自由”、“心也受拘禁”、“眼界狭小得可怜”,什么也不好奇,什么也看不见,已经变得相当麻木了的“睁眼瞎”、假面人。其二是麻雀形象。作为鸟里的俗流,弄堂的常客,与鸽子“灵”的身份相比,它们充其量只是些“肉”的动物。要是从它们两者的活动范围、追求目标来比对,鸽子属于天际,而麻雀则属于弄堂里的阳台或天井;如果说鸽子就是鸽子世界里智慧的象征,而它们则是鸽子世界里媚俗的、低贱的代名词。同时,鸽子还是人类的帮手,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而麻雀只懂得同流合污、一味地增添弄堂里的低级趣味。其三,是灰尘形象。作者写道:“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地飞舞,也是天地的主人。”寥寥数语,道出的其实是对“如蚁的生命”的赞叹与怜惜!否则,“灰尘”如何在作者的笔下却欢快地“飞舞”了起来!另外,称它们也是天地的主人,这里的“天地的主人”肯定是有别于“城市的精灵”的。作者就这么随手一写,灰尘的世界便从读者的眼前一闪而过。其四,是风筝的形象。“它们是对鸽子这样的鸟类的模拟”,因为它们不拥有生命,连麻雀也不如,但却有人类一样好高骛远的心。其五,是太阳的形象。“太阳从连绵的屋瓦上喷薄而出,金光四溅的。鸽子出巢了,翅膀白亮白亮。”显然,它是鸽群远航前的汽笛,是他们飞行时明亮的大背景与大舞台。
现在,我们把王安忆构建的这个庞大的“鸽子世界”里的等级次序由高到低、由大到小做一个排列,它们的顺序就依次成了这样的:鸽子、人类、麻雀、灰尘、风筝、太阳。除过太阳,鸽子是这个世界里的最明亮的色彩,作者称赞它为“这城市的精灵”、“唯一在俯瞰这城市的活物”、“它几乎是这城市里唯一的自然之子了”!说明的不就是它所处方位的高和远、所表现出的精神境界之深邃、之沉郁吗?
二、见识之广、杂
由于这些鸽子每天早出晚归,也由于它们的足迹遍及各处,因此它们的所到之广,所见之杂,也就远远超越了凡俗的脚力与眼力。而在《长恨歌》里,最能体现它们见识广、杂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们跑得究竟有多远,而在于它们对这个城市众多苦难的明察秋毫与洞若观火。因为它们是唯一俯瞰这城市的活物,作者写道:“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许多无头案,它们都是证人。它们眼里,收进了多少秘密呢?它们从千家万户窗口飞掠而过,窗户里的情景一幅接一幅,连在一起。虽是日常的情景,可因为多,也能堆积一个惊心动魄。”
又是“无头案”,又是“证人”的,简直是杀气腾腾、杀机四伏,而鸽子,却是这林林总总的血腥事件里的最勇敢的见证人!它穿云破雾,无所不到,它甚至能将“这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尽收眼底。人类当然不能,因为人类是当局者迷,而鸽子是旁观者清;人类的眼睛只在白天起作用,而鸽子不但在白天可以明察秋毫,即使在夜晚,也同样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人类只能看到热闹与喧哗的表面因素,而鸽子还能看到沉寂和死亡的因与果;人类只能看到寻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而鸽子——它们锐利的眼光还能捕捉到这水泥世界的沟壑裥绉里,那些特别的不同寻常的事情,即它们锐利的眼光还能“去伪存真,善于捕捉意义”。“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它们从千家万户的窗口飞掠而过,无需进入哪一家、某一户,但它们却能够洞穿每一家、每一户,谁家的恩爱与情意、谁家的仇怨与是非,谁家的贫困与孤苦,谁家的堕落与沉浮——于是都不再成为秘密,而让它尽收眼底。“一幅接一幅,连在一起。虽是日常的情景,可因为多,也能堆积一个惊心动魄。”
到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人类看什么都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情景”,而在鸽子心里堆积出来之后却是一个个“惊心动魄”。因为人类更乐于沉湎和迷恋的是琐碎又短暂的普通日子,所以他们只能感知到寻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而鸽子,它们锐利的眼光却善于“去伪存真,捕捉意义”。更令鸽子悲伤的是,它们无法从这“一幅接一幅”“连在一起”的日常生活里看到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因此猝然望去,窗户里的情与景,在鸽群的眼里,就像是太阳下骤起骤落的雨云,还有太阳的斑点,“躲也躲不开”,而它们的眼睛,都要被这些情景给灼伤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有泪流不出的样子”。也许这里的“惊心动魄”也就是伤情、困苦、灾难、恸哭吧!
三、入目之细、微
就拿作者对上海弄堂的那一段华丽描述来说,当“晨曦一点一点亮起来,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借助鸽子的眼,我们依次便看到,有薄薄的雾,带着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在晨雾里精致乖巧的模样;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是晒台,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像画上的衣衫;而晒台矮墙上的水泥已经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划都是那么的清晰。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接着,第一缕阳光在山墙上出现,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
远的近的、高的低的、实的虚的,上到晨曦、雾、灯、老虎天窗、屋披上的瓦、山墙上的阳光,下到木框窗扇、花盆里的月季花、墙上的裂缝、裂缝处脱落的水泥、甚至露出的锈红色的砖、砖上点点的绿苔,乃至于弄底的水泥地……凡目光所过之处,无一不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而在《长恨歌》里,作者围绕主人公王琦瑶,就用同等细致的笔墨给读者展示了无数属于小女人的小感觉、小情趣;小脾气、小心眼;小经验、小风波;小环境、小事件——这一个又一个的“小”,都无不以其细密之美、微观之态吸引着我们,它们密密实实、层层叠叠,最终组成了书中几乎所有小人物的命运碎片。“王琦瑶的一生是一个上海弄堂到处可见的普通女性极不起眼的一生,是由无数琐碎小事堆砌起来的女性人生图景。”[2]
评论界把王安忆的这种笔法也叫女红操作,“沉缅于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无缘”[3]。然而呈现了一个女性的韧性与执着。看似闲散繁复的叙述方式,不紧不慢的叙述节奏,不可思议地一点点、一段段、一层层、一片片地铺展着女人感性的世界,大到选美时如何的倾国倾城、“沪上淑媛”称号的多么的来之不易、豪华旖旎的爱丽斯公寓里半推半就的外室生活、平安里小诊所浮生若梦的苟且生活,小到时装的搭配、气质的养成、仪表的品味、烹调待客之手艺、歌舞的妙处、婚姻之道、爱情秘笈、扑克麻将的技巧、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的经验及成规、女人之间的小心眼、小战争等等,这种“女红”的操作虽繁琐、单调、平淡,最后却能做成一件精致美丽的产品,用李素珍老师的话来说,这种过程就像是在心平气和地拆解一件旧毛衣——女人的历史,然后再细心地东拉西扯、左右盘旋,编织成一件自己欣赏又梦想的毛衣——女人的现代。
四、用情之深、切
从“鸽子”一节里作者对这个小生命此起彼伏地咏叹中,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
“它们飞来飞去,其实是带有一些绝望的,那收进眼睑的形形色色,也都不免染上了悲观的色彩。”“它们是多么的傲慢,可也不是不近人情,否则它们怎么再是路远迢迢,也要泣血而归。它们是人类真正的朋友,不是结党营私的那种,而是了解的,同情的,体恤和爱的。”“它们心里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同情;有多少同情,就有多少信用。鸽群是这城市最情意绵绵的景象,也是上海弄堂的较为明丽的景象,在屋顶给鸽子修给巢,晨送暮迎,是这城市恋情的一种,是城市心的温柔乡。”“这城市里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都瞒不过它们的眼睛。当天空有鸽群惊飞而起,盘旋不去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猝然望去,就像是太阳下骤然聚起的雨云,还有太阳里的斑点。在这水泥世界的沟壑裥绉里,嵌着多少不忍卒目的情和景。看不见就看不见吧,鸽群却是躲也躲不了的。它们的眼睛,全是被这情景震惊的神色,有泪流不出的样子。天空下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有如蚁的生命在做挣扎。”“对人类从一而终的只有鸽子了,它们似要给这城市安慰似的,在天空飞翔。”“这城市像一个干渴的海似的,楼房是礁石林立,还是搁浅的船只,多少生灵在受苦啊。它们怎么能弃之而去。”“鸽子是这无神论的城市里神一般的东西,却也是谁都不信的神,它们的神迹只有他们知道,人们只知道它们无论多远都能泣血而归。”“这城市虽然有着各式庙宇和教堂,可庙宇是庙宇,教堂是教堂,人还是那弄堂里的人。人是那波涛连涌的弄堂里的小不点,随波逐流的,鸽哨是温柔的报警之声,朝朝夕夕在天空长鸣。”
如此种种,其间写尽了鸽子对人类的深情厚谊。
注释:
[1]徐德明:《历史与个人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杨经建:《9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的叙事表现风貌》,理论与创作,2000年,第6期。
[3]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白彩霞 兰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