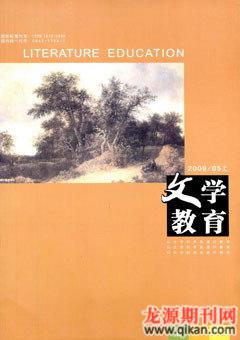王小波小说语言艺术探究
谭 华
王小波是九十年代文坛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这位“文坛外高手”用诗性的智慧经营的文字,为读者开启了寻常与奇异共存、幽默与理性共生的世界之门。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探寻作品语言的魅力所在。
一、寻常的语言文字
寻常性是王小波作品语言的特色之一。从使用词汇的角度看,进入王小波作品的绝大多数都是常用词汇。从家庭里用到世态物象,从生活用品到生产用具,从一般的口语词汇到特有的文革用语。无不具有寻常性的特点。生活中锅碗瓢盆,生产中的拔秧凳、小背篓如鱼贯似的在王小波所搭设的文字舞台上隆重登场。文革中的一些带有时代色彩的词语如插队、批斗、检讨、请假、喂猪、破鞋、队长、知青、军代表、人保组在九十年代无不已进入常用词汇之列,为人们所司空见惯。这些常用词汇的大量使用,拉近了读者与文革的距离,再现人们的文革记忆,还原时代的荒谬性。这些词语的使用也解构了历史的神圣与崇高。所以常用词汇是构成王小波小说语言的基石。文本中大量频繁使用的常用词汇,使文本语言告别雅化而呈现寻常的俗的特点。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时时可以寻着一些口语化的句子。这些看似寻常的口语却使人感到新鲜、怪诞与陌生。例如,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叠字这一现代汉语中特有的现象,《黄金时代》中写“我”在山后的小屋里等待陈清扬,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作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出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在此作者连续运用了4个叠音词。这些叠音词的使用体现了鲜明的口语化特色,符合现代汉语的特点。口语和书面语相比它更具有随意性。文本中频繁出现的体现着鲜明口语化特色的叠音词消解了书面语的正规性。王小波小说中出现的带有口语色彩的词语提升了作品的随机性和临场性功能,增加了文本的自由度。
很少使用冗长的修辞,很少使用复杂的句式,尽可能的使用标点符号,适当省略,化繁为简,语意简单明了,语气铿镪顿挫是王小波小说语言文字寻常性的另一表现。王小波在作品中很少使用冗长的修辞,即使使用修辞手法,他也能用最日常化的喻体。用最贴切的方法,将复杂的人生道理深入浅出的和盘托出。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我现在是这样理解ran—dom——我们不知为什么就来到人世的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眼前的事情,这一切纯属偶然。在我出世之前,完全可以不出世。在我遇上×海鹰之前,也可以不遇上×海鹰。与我有关的一切事。都是像掷骰子一样一把把掷出来的。”在这里。作家运用娱乐中的掷骰子,来比喻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其喻体寻常,比喻恰当、通俗。
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辱骂、粗话、色语等粗鄙的语言是小说语言文字寻常性的又一体现。王小波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俗语粗话,如:没良心的、装丫挺的、坏蛋、鬼子、坏分子、造大粪、直橛橛的、一杆大枪、磨屁股。这些口语化的词语就像狂欢节的台词,消解了伟大与崇高,打破了秩序与权威,还原了人类历史的本原,也发出了对文革历史最强烈的呐喊。这些口语化、粗鄙化词语的运用,使王小波小说的语言在寻常中带奇异。这些看似粗俗的文字却表现着王小波对人性中的真、善、美的赞许、追求。作品通篇力透纸背的是作者灼烈、原始的反抗。读后没有恶心的暖昧而有神清气爽的愉悦。这是小说语言的寻常与“有趣”所在。
平白如话,不堆砌华丽的词藻,甚至很少使用形容词,是王小波作品语言寻常性的又一重要表现。王小波虽然在小说中使用的都是常见的词语,但表露的感受却是鲜活的,甚至是怪异的。他表面平实的语言,于调侃中挟带严肃,又于鄙俗中央带纯正的教养。所以他的语言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例如:“陈清扬说,出斗争差时,人家总要揪着她头发让她往四下看,为此她把头发梳成两缕,分别用皮筋系住,这样人家一只手提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揪她的头发就特别方便。她就这样被人驾驶着看到了一切。一切都流进她心里。但是她什么都不理解。但是她很愉快,人家要她做的事她都做到了,剩下的事与她无关。她就这样在台上扮演了破鞋。”“这段文字平白如话,质朴无华,毫无刻意修辞,三言两语、简单明了、酣畅淋漓的写尽了主人公的无辜与无助。
王小波作品的语言既无刻意雕饰之痕,也无矫揉造作之态,明白入理,平白如话。他的作品的文字恰似许多野花,来自田野,却散发着奇异的芳香。
二、奇异的艺术效果
王小波作品的语言文字虽然寻常,但达到的效果却不同寻常。使作品收获奇异性效果的是反讽手法的运用。反讽使语意由寻常走向奇异,由熟悉走向陌生。
反讽(Irony)是叙事文学经常用到的一种修辞方法,反讽叙述存在着表面义与实质义的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浦安迪认为反讽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王小波的反讽语言在90年代小说中可谓别具一格。他在语言的表层鲜血淋漓地展示暴力与虐害,以狂欢的节奏排演性的表现膨胀与畸变。在他的作品中,性爱场面是展示反讽手法的一个主要场所。作品中的性爱场面大多呈现放纵与狂欢。双方性欲的释放实质是与文革对双方的压迫和摧残是“正反同体”的。代表作《黄金时代》里有一段这样的性爱描写:“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缠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从这段文字的表面,我们丝毫看不出性爱的享受者实质是文革的受害者。在狂欢的纱帐下掩藏着的恰是两个心灵上、身体上满是伤痕的受害者。作者没有直接揭开这血淋淋的伤疤给人看。而是用近似喜剧的形式展现悲剧的内容。这就构成了一种表象与实质的对立,让读者在会心微笑的背后隐隐感受冷峻与沉痛。这种叙述方式也赋予文本“黑色幽默”的特点。王小波的语言具有一种浪漫反讽的特色,他在慷慨陈词与浓墨重彩中总是包藏着冰寒彻骨的刀锋,用让·保罗的话来定义就是:“激情的热水浴后用反讽的凉水冲洗”。例如,《黄金时代》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段描写极其浪漫,作者在展现性爱活动的同时,特别安排了一只动物的出现,通过这只蜥蜴对性爱场面的窥视、被惊吓到消失来展示他们的肆无忌惮。作品中的“我和陈清扬”其实都是受虐者,陈清扬破鞋破摔并不是完全出于主观意愿,更多的是文革环境造成了她的畸形与裂变。所以这个场面具有表层与内里的双重性。在炙热的激情背后有冰冷的社会现实。作者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使文本如北方春天的湖面一般寻常而宁静,但宁静的湖面下却涌动着春天的潮水。反讽手法的运用使文本于寻常中产生了奇异的艺术效果。在作品中王小波还故意用一种遗忘姿态一览无遗地展示文革梦魇的残暴与伪善,可在漆黑的人性深渊却寻找记忆的谛视并敞开其真实和恐怖。王小波常用一种亵渎式的语言去冲刷爱与恨、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的边界,使那种庄严肃穆崩裂成荒诞的碎片,在赤裸状态中还原让人无法直面的生存镜像。王小波在作品还善于预设一个与他创作本意相反的叙述者,让这个叙述者盛装表演,而把真实的意图不动声色的隐藏在文本背后,使主人公滑稽的演出和观众的价值判断形成冲突,使文本在冷静的叙述下,在平实的文字架构中,制造出奇异的艺术效果。
纵观王小波作品的全部文字,都是寻常性的文字。但作者以其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断在作品中制造新鲜和怪诞。他的作品语言平实又反常,熟悉又陌生,冷静又热烈,沉着又机智。他虽然英年早逝,但在当代文坛留下了一份珍贵独特的文字大餐。无数的读者会从中体会到思维的快乐,觉醒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