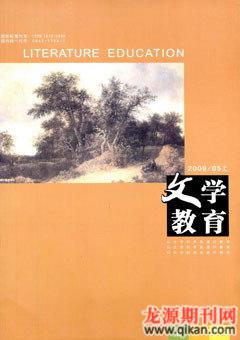让不寻常的发现回归寻常的形态
席星荃
我在第三期的短评里说过:“我希望散文像生活而不太像艺术。而又不是照搬生活。”这篇《护工纪事》似乎正是一个例证。
如果从中国传统散文或主流散文的体式来看,我们会觉得这篇散文有些异样,有点陌生。异样在哪里?陌生缘于何故?首先应该是它的写实风格。它所写的是寻常又寻常的事件:父亲中风住院了。某人中风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大事,对他人来说却是寻常事;但据说中风比例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个题材具有了大众性和日常性,中风似乎可以称为现代生活的某种表征,因此写中风住院可以看作是散文写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这个角度本身就潜藏了叙事的可能与要求,有一种写实风格的指向存在。
然而中国传统的散文讲究一点空灵,一点轻盈,一点飘荡摇曳的姿态。而这篇作品因为写实,抒情和议论这两种散文惯用的主打方武则相对减弱,它通篇就是在说一件事:它的起因,经过,演变,结局。叙述非常完整,注重人物形象,感觉有点像小说,这些就不够符合空灵、轻盈、摇曳的观念,跟我们印象中的散文概念有所差异,我们觉得陌生,觉得异样。
这也许就是它的创新,但是,用写实手法写寻常的题材也危险,人们喜欢亲切熟悉的事物却又不甘心庸常的絮叨,渴望从熟悉琐细里读出暗藏着的一点新奇。林那北发现了什么吗?她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的,她发现了寻常中的一点儿不寻常,就是“同情心不能替代一切。”同情心作为美德一向受到普遍的价值肯定,林那北却提出质疑,要颠覆它,这就是这篇作品的又一个独特处。但任何思想理念如果脱离了具体生动的生活形式都会是枯燥说教,它可以作用于人的智性,却难于打动人心,难于拨响情感之弦。林那北懂得这一点,她采用的方法是,像盐溶于水,像汁液流动于植物茎叶中,让不寻常的发现回归寻常的形态。
这篇作品没有遵循散文要有“我”的传统写下去,不再以“我”为中心;而着力写客体世界,满篇写人物、写事件、写场面、写气氛。人物写了护工小郑、四川帮、母亲等人,都细致生动,而且渗透着人的心理活动、性格因素、思想和情感的波动。写旧川帮:“眼珠子反而只是在小郑和我们几个家属间闪来闪去。看小郑时他们是不屑的,嘴角翘起,看我们时又意味深长,透着一种要揭开什么秘密似的提示。”而小郑“在他们的目光下显得很局促,做这做那都不免磕磕碰碰地不流畅。”再写四川帮“哄地笑起,很古怪地笑,接着他们中就有人大声说,不会做!”这样的文字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散文语言,它少了惯常的“散文气”,让人新鲜。
除了刻画人物,作者还细致地叙事,让事理在过程中逐渐萌芽、发育和成长。出于扶弱抗强的道义和同情心,“我们”断然拒绝了四川帮的提醒和热心,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新手和弱者小郑。但是,接下来,事情渐渐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小郑的低下素质与“我们”的同情心和道义形成尖锐的矛盾,麻烦和苦恼由此不断产生。小郯他不会看仪器,总是忘记按时给病人服药。学不会给病人拍背,老是走神,打完点滴不能发现……“很想做好,可是他做不好”,起初,同情心仍然支撑着,“新手嘛,我们一直试图理解他。……事做不好。态度好,叫人都不好意思多指责”。后来事情愈演愈烈。母亲不断失声叫起,她太吃惊了,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缺卫生常识?洗屁股和洗脸混用盆子,一块布擦完桌头柜又擦鼻食管封口……而小郑对各种卫生要求也不能理解,“十万个为什么,他都无所适从了。”总之,小郑和“我们”,双方都经历着痛苦,事情完全走到了愿望的反面。最后。只好辞掉了事。结束的一笔颇具意味:小郑“居然一下子就同意了,当初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劲完全没有了,甚至还顿时有种轻松感。”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某些时候,同情心带来的不一定全是好事——“同情心不能替代一切”。
这篇作品以叙事为主,笔调深入细切,一如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而具体,充满了当下生存的焦灼气息和复杂况味,作者将对生活的发现回归于生活的寻常形式,而脱离开通常的内省式笔调和抒情性风格,它像生活,而又满含意味,因此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