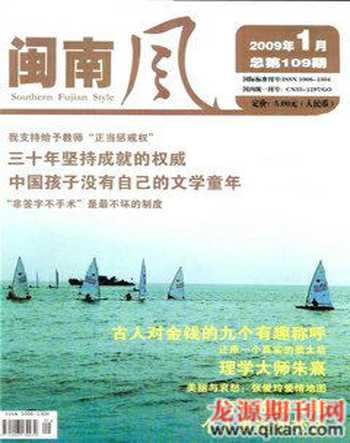中国孩子没有自己的文学童年(外一题)
韩浩月
近日,在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作品研讨会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发言称,“过去是孩子不了解大人,觉得大人神秘。现在倒过来了,大人不了解孩子,觉得孩子神秘了。有些儿童作品出来以后,孩子们会评价说‘弱智。”
媒体报道该新闻时使用的标题是,“孙云晓批评儿童文学‘弱智”,但阅读完新闻全文才知道,哪里是孙云晓批评儿童文学“弱智”,明明是孩子们亲自批评嘛。几年前曾有一份关于儿童文学的读者调查,2000多条来自中小学生的意见中,“儿童读物太弱智了”就十分扎眼地位列其中,更有孩子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希望你们给我们写一本可看一年以上的书”。 而我所理解的“可看一年以上”,是那种类似于《木偶奇遇记》、《绿野仙踪》、《小王子》这样的传世作品。
孩子们的这个请求是直接而朴素的,也一语道破了儿童文学几十年来为何一直处境尴尬——中国儿童文学不乏“作品”但却少有“经典”。作为一名七十年代人,提到儿童文学好歹还可以脱口而出“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和“郑渊洁叔叔写童话”。没想到到了21世纪,提到儿童文学,仍然只有郑渊洁这个也成了爷爷级的人物。想想我们这代人其实是没有文学童年的,我们从小接触的文学,是评书、金庸武侠、琼瑶言情,而这些,都是属于成人的,可以说,我们的阅读经验,是直接一步跨进了成人期,中间并没有一个阅读的“缓冲地带”。
中国也有优秀的文童文学作家,包括“最畅销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以及“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她们都拥有自己的“品牌”,前者的“淘气包马小跳”,后者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都有过数十万、几百万的销量。但这些貌似巨大的销量并不代表什么。首先,青少年儿童是图书消费的主力,这个读者群基数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其次,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群体甚至连100人的名单也凑不完整,核心作家的书卖得多一些,并不代表他们的写作就是被青少年认同的,也许,这不过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已。要论销量,每年父母带着孩子去买的四大名著说不定也会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儿童作家中最具想象力的当数郑渊洁,他一人独撑一本《童话大王》23年,这本身就是一个童话。郑渊洁所创造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也是中国作家创造的最为国际化的儿童卡通形象。郑渊洁的童话突破了中国童话几成桎梏的逻辑和道德框架,为童话人物赋予了更高的人格价值,但他的创作视野并不开阔,因而作品少了纯粹和大气。缺乏想象力是中国作家的通病,只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家身份,读者会对他们的想象力会要求的更高一些,恐怕对这个写作群体,也是无形的压力。
童年是接触文学最好的时期,那些丰沛而敏感的心灵,一旦插上文字的翅膀,他们的一生都会为文学所滋养。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点,后来的家长们,都很注重对儿童阅读兴趣的培养,只是,家长们的选择面太窄了,当年的父母给我们读安徒生童话,现在我们从书架上拿下那本蒙尘的书读给孩子的,依然是安徒生童话。而这些外国童话,大多数也并非是孩子们都喜欢的。中国孩子需要本土作家创作的童话,可是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还是让孩子们失望了。
现在的孩子,与以前的我们相比,更是没有文学童年的。杨红樱和秦文君的作品,大多是现实题材的,说的是校园里的事情,青少年固然喜欢读到身边的人和事,但他们的群体特点更多的却是喜欢毫无约束的畅想。通过排名前100位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作品属性,就可以看得出来,孩子们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即便是经典作品,近些年也逐渐被《千与千寻》、《蜡笔小新》、《麦兜的故事》这样的动漫图书抢去了风头,这意味着,每个时代的孩子对精神产品都有不同的要求,新经典的诞生,必然要吻合当下孩子的心理需求。哪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能有勇气承认自己真正了解现在的孩子?他们的写作,除了被冠以“儿童文学”的称谓外,拥有多少儿童文学应该具备的文学营养?
无限怀念“西北风”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田震唱“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时间的惊异与错愕,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柔软凄怨的歌曲出自“彪悍”的田震之口,那时还没意识到,流行了整整10年的“西北风”行将结束,中国流行歌坛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的“西北风”潮,自此被写进记忆。
现在是流行歌坛的“花儿时代”,如果当时称杭天琪、田震、程琳、范琳琳她们为“花儿”,会觉得这是个非常蹩脚的形容。正是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创造了《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风格硬朗、感情浓烈的流行歌曲。后来在杭天琪接受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那会儿的歌现在听起来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可是她并不知道,正是这些歌,为火红的80年代留下了珍贵如金的纯真印痕。
作为一名70年代生人,“西北风”和小人书、露天电影等一样是永难磨灭的记忆。网络时代,很多人回忆前当年的流行歌曲,莫不觉得趣味横生。比如寂静的晚自习上,突然一个高亢的男生蓦地响起,“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余音绕梁,而且就这一句,没了下文,现在想起来,这歌声里,居然有惆怅和悲伤的味道。在一个流传甚广的帖子里,有人这么写到,“小时候听《信天游》:‘我低头,向山沟,总觉得是‘我地头,像山沟”,还有人写到,“有一次把‘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听成:‘“大爷听过我的歌,小伙亲过我的脸”。尽管如此,“西北风”在当时理解能力并不强的少男少女心里,还是有着独特的启蒙作用,这些流行歌曲,第一次让那些懵懂的心灵,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感性的认识。
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一个10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文艺创作势头蓬勃,全国上下对于精神产品的渴求,可以用饥不择食来形容。适时出现的“西北风”,恰如一顿可以填饱空虚生活的一顿“硬饭”,给一心一意奔小康的人民增加了底气。同时,被贫困生活和思想束缚捆绑了十多年之久的人们,也急需要喊一嗓子发泄一下积闷,而“西北风”无疑成了一个最好的载体。
不止是歌手唱歌“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声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这时已经开花结果,暴发户(可能也不过就是万元户的升级版)从县一级城市开始遍地开花,“全民向钱看”曾被当作社会恶俗现象进行批评,而现在看来那正象征着每个人都被“希望”这个词搅和得热血沸腾。对国家、对故土的热爱,以及个人情感的集体复苏,都通过这“一声声呼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发。
80年代的文艺演出给我留下了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县城里的每一个周末都有歌舞团(现在的说法是野台班子)到电影院或大礼堂演出,演出开始时的曲目以及掀起全场最高潮的曲目,必定是“西北风”的代表作。对“西北风”歌手的模仿是否惟妙惟肖,也决定了模仿者的受欢迎程度。蜂拥而来的观众让挤满了演出场所的通道,外面等待的人群还在试图以冲击的方式通过检票口。而此时里面的演出气氛之热烈已达顶点,噪耳的音乐、失控的歌手、尖利的口哨以及年轻人身上散发的热汗气息,是以后哪怕再狂热的摇滚演出也不能比拟的,那种野蛮且真实的场景令人感动并且融身其中,只有60年代美国摇滚热能与之相比。
“西北风”的流行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并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就像80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一样,“西北风”也是那个时代最为鲜明、最为强烈、最为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情感和心声的文化符号。它如同一个容器,让这个民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开阔的胸怀和原始野性的性格,得以混和在一起,以最恰当的方式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味道。反观现在萎靡的流行歌坛以及虚假、浮躁的社会风气,愈见“西北风”以及它潜在寓意的珍贵。只可惜,作为时代产物,“西北风”已成过去时,怀念的人们,也只好偶尔在KTV喊几嗓子“一望无际唱着歌”抒发一下情怀了。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