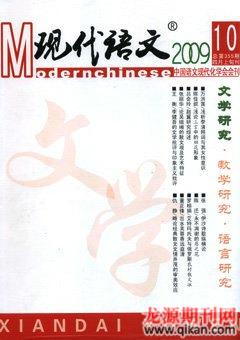“渔父”形象探讨与解读
杨 勇
摘 要:渔父形象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隐逸思想或者说道家处世哲学的具象化。长期以来,在偏重挖掘圣贤光辉思想的影响下,渔父形象往往作为屈原人格的对照,被当作反面人物来看待。其实,屈原与渔父对生存的选择,不是美与丑的对立,而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越,他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人格魅力,渔父与屈原是与世俗相对立的两个美的化身。生存还是毁灭,屈原与渔父对生存的选择,给我们更多的是两种唯美指向。
关键词:《渔父》 渔父形象 生存选择 唯美指向
近日,听了一节苏教版必修五《渔父》的公开课,教师在事先的情境设计下引导学生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像屈原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能像渔父一样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这样的解读让笔者实不敢苟同,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单纯从文本的角度,渔父与屈原不是美与丑的对立,其实,渔父与屈原是与世俗相对立的两个美的化身,两种选择与精神追求。而造成教师这种一元化的解读或误读,究其原因有三:
一、教师多年来对教材编者心领神会式迎合,习惯了在圣贤教育中挖掘圣贤光辉的思想
在屈原与渔父的两种生存选择中,在长期受圣贤教育的影响下,师生习惯性地要拔高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形象,而渔父作为屈原人格的对照自然而然地变得渺小甚至被贬斥了。其实,苏教版必修五编者的本意并没有以自己的一元解读代替师生的多元解读,编者在教材中设计了“直面人生”这一主题,并在下面标以“生存选择”这一子题,原意是要引导教师与学生进行多元解读,但教师多年来对教材编者心领神会式地迎合导致了对《渔父》的误读以及对渔父形象的歪曲。
二、渔父的形象被当作反面人物来看待,属于误读
屈原自沉于汨罗所表现出来的操守与执着,值得我们崇敬。但屈原自沉于汨罗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人生价值取向并无唯一的标准,孔子也认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仁;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甚至包括司马迁本人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结尾也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因此,渔父的生活态度及人生价值取向无可厚非,更何况渔父不是那种“黑白不分”贪图世俗享受的小人,还不至于硬要把渔父摆到屈原的对立面来加以批判。其实,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这篇《渔父》。即使“渔父”后来演变为文学中的“渔夫”形象,在过去也曾长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欣羡。所以,渔父与屈原不是两个对立的形象,屈原的执着,渔父的旷达都是很美好的品质。渔父与屈原是与世俗相对立的两个美的化身,两种选择与精神追求。
三、混淆了“随波逐流”的本义与比喻义
“随波逐流”的本义与比喻义有本质的不同。随波逐流,《现代成语词典》认为其出处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比喻没有坚定的立场,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只能随着别人走。而《辞海》认为《抱朴子·审举》:“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后因以“随波逐流”比喻没有主见而随大流。
结合《渔父》的内容,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可见,前句“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就是对后句“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的解释,这也是对“随波逐流”成语本义的最好解释。通俗地说就是“所谓的圣人,并不拘泥局限于形式,而是可以根据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处世的态度”, 可见渔父的随波逐流是顺其自然、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是隐逸思想或者说道家处世哲学的体现,具有中性偏褒义的色彩;而从《辞海》对“随波逐流”的解释,我们可以大致认为随波逐流的比喻义是从东晋时期葛洪《抱朴子 审举》开始的,比喻没有主见而随大流,这才开始带有贬义的色彩。因此,“随波逐流”的本义与比喻义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渔父”这一形象进行探讨挖掘。
一、从文章本身来看,《渔父》的主人公是渔父而非屈原
屈原作品的真伪向来就有争议,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渔父》是后人伪托的可能性较大,认为《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至于屈原在流放途中,有没有遇见渔父,已无从考证,“渔父”是否确有其人已经不重要,如同后来司马相如笔下的乌有公,苏东坡笔下吹洞箫的“客”,可以当作文学作品中一个虚构的人物看,亦无不可。
首先,单纯从文本本身来看,课文题目既然为《渔父》,那么“渔父”的形象应该是正面的,一般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课文题目如果是人物,往往都属于被称颂的主要人物,所以主人公也应该属于渔父而不是屈原,屈原只是文章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其次,渔父与渔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材编者认为,“父”,同“甫”,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辞海》解释为“对老年男子的尊称。如渔父;田父”。所以,文章中写的是渔父,而不是渔夫,以“父”称之,是对“渔父”这一人物的尊重。文章中,渔父的谈吐引用圣人之言,如“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从这个角度而言,渔父的话表现的是圣人的思想。而且,课文结尾——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样的结尾,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具有了悠远的情韵。
二、司马迁删除文字值得玩味
值得说明的是,《渔父》最后一部分,不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的一部分中,对比文本如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而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结尾也没有提到《渔父》篇名: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苏教版编者也作如下解释:《渔父》是战国时期秦汉间人记叙屈原事迹的文字,又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各种文献。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歌颂屈原的,司马迁考虑到《渔父》最后一部分文字有赞美、渲染渔父的意味,因为屈原清高的个性,在渔父眼里显然是谋略不足的,难怪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不复与言”。而且从形象上看,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渔父莞尔而笑,一幅从容的模样。所以司马迁作了巧妙的删除,这样屈原的形象也就更突出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末尾,“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可见司马迁写屈原,除了赞美他的人格外,更多的是借屈原、贾谊来说自己志向不能实现而感到悲伤的复杂心情。
总之,从《渔父》作为文章的标题到全文对渔父的正面描写,尤其是从文章的结尾看,似乎很难看出有专门褒扬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我们在赞美屈原的同时,应该对渔父表示尊敬,他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人生可能,这种隐遁自然、遨游江湖的自由人生,在没有抛弃高洁人格的前提下,体现了对人生的另一种选择,是隐逸思想或者说道家处世哲学的具象化。屈原也好,渔父也罢,他们都把品格操守与人生追求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宁赴清流悲壮的死,还是隐遁自然自由的生,都是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屈原与渔父也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各自彰显了人格魅力,成为后来知识分子心中美的化身。生存还是毁灭,屈原与渔父对生存的选择,给我们更多的是两种唯美指向。
(杨勇 浙江苍南金乡高级中学 32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