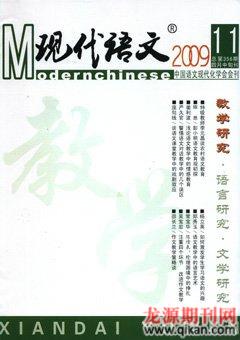警惕语文对话教学中的几个误区
在新课程理念下,语文教师大多“热衷”于对“对话教学”的教学运用与理论探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1]可见新课标对于语文教学的“对话性”是很重视的。而所谓语文教学的对话性,或“对话型”语文教学,“简单地讲就是在坚持教学的教育性特征的同时,教师以对话的情怀对待学生,对待教学,对话精神贯穿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之中”[2]。然而在对话型语文教学的理念认知及教学操作上,不少的语文教师存在误区,导致了“似是而非”的伪对话,即流于对话形式而忽视对话本质的对话行为。
一、缺乏对话的伦理品质:平等、尊重
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对话”是生存最基本的东西,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的同一状态中,语言的“本质”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存在就意味着对话的交际”。这里的对话是就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说的,强调了语言真正的生命在于话语,而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构成了人生命的真正存在。人的意识需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交往中才能自我确定。巴赫金说:“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是构建自我意识的行动,是确定对他人意识的关系。”[3]基于此,巴赫金主张在互相交往的对话主体之间坚持以人为本,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当然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哲学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构建成对话型的语文教学后,必定有教育意义上“受限”,即语文教学不完全是对话性的。但语文教学中对话性的伦理品质不能丢,仍然要以平等尊重作为基本的对话意识。“对话的精神内涵和发展要求规定了对话主体必须有一种对话意识,即民主的意识、平等的意识、合作的意识,致力于共同创造新的精神境界和倾听他人的渴望。”[4]马丁·布伯更是形象地将这种平等对话关系表述为“我—你”关系,根本上是“心灵与心灵的关系”。因此,坚守对话的伦理是体现对话精神的核心所在,是实现对话价值的前提。
在对话性的语文教学中,仍有不少语文教师没有真正的与学生的平等意识,还是以对话教学之形式套装传统的灌输教学之实质。组织学生对话时,以个人的意志控制对话的内容与进程。对学生的对话内容稍不满意,就轻易地制止,转移话题,或改为教师自己的讲授。有的甚至粗暴地训斥学生,讥笑、挖苦的也大有人在。缺乏最基本爱的对话伦理前提,无论对话形式如何精彩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否定了对方的价值独立性,就意味着否定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二、将对话等同于机械的师生问答
自对话在教学中受到重视,语文课堂上由过去的“满堂灌”变为“满堂问”。误以为问的多、学生答的多就是有效的对话教学。如一位语文教师在教学《范进中举》时,与学生进行了一段问答式的对话:
师:这篇课文作者是谁?
生:是吴敬梓。
师:吴敬梓是哪个地方的?
生:安徽全椒人。
师:是哪个朝代的小说家?
生:清代。
师:出生年月是多少?
……[5]
这样的流于对话形式的一问一答是典型的“伪对话”。“巴赫金的对话原则不是简单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讲话,而是主体间性深刻思想的表现。”[6]从认识论上看,对话是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而不是机械地内容再现。即法国哲学家说的“制造意义”,弗来雷的“对话即意味着对世界改造”。正由于此,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比实际对话中的对语关系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王荣生先生也认为,“对话”与否不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交谈”式教学,也未必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因此,在语文对话教学中,我们要关注对话意识、问题意识。对话意识就是互相倾听、交流,共同构建新的意义的意识。“没有对话意识的问答,就像是一具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僵尸,绝非真正的对话。”[7]此外,对问题意识也不容忽视。如上例中的提问就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学生只需看文下注解就一目了然,何必一一作答。真正的问题意识可以促进师生或生生间的深层交流,推动对话的进程,最终生成“新生”的意义。
三、脱离文本、脱离文本语言的泛对话
正如泛人文一样,泛对话也是存在于语文教学中,很多语文教师还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先看两例:
有位教师在上《寂静的春天》时,运用课后思考探究来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上网查找有关环境污染的资料做成课件。于是,学生找来了世界各地因环境污染而造成危害的大量数据与图片资料。上课时,各小组纷纷展示他们的丰富的课件,语文课变成了地理课。[8]
另位语文教师在教学《万紫千红的花》时,与学生一起探讨各种美丽鲜艳的色彩以及花的色彩与酸碱溶液的关系。这位语文教师鼓励学生运用生物学的知识补充解释。这些对话足足花了三十多分钟时间。[9]
上引的两例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脱离文本。他们分别将语文课上成了地理课及生物课,这是脱离文本的典型。当前的语文教学中脱离文本的泛语文现象较为突出,有的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与主题无关的问题,如在上《荷花淀》时让学生讨论“水生嫂被强暴了怎么办”,学生的兴趣很高,你一言他一语,看似热闹的对话,实则严重脱离了文本。这种泛语文现象往往以泛对话的形式出现,偏离了语文的学科性质,缺失了语文基本的价值目标。语文新课标也很注重师生与文本间的对话,而深入文本自然离不开文本语言。文本是意义有待实现的言语作品,需要读者解读生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阅读评价手册》中说:“阅读是一个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构建意义的动态过程。”学生需要在文本语言中感知、理解、欣赏,进而带着个体的解读与问题展开对话。建立在学生与文本深入对话基础上的教学对话才是有效的,否则脱离文本的泛对话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们在警惕语文教学中的泛语文、泛人文的同时,更要关注泛对话形式的蔓延。一节语文课很容易因为教师的随意、泛化的组织对话而浪费过去,这是教师的严重失误。
四、忽视教师有效必要的引导
对话的哲学理念与对话教学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前者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对话的本质意义,即对话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话语的对话性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对话本质,体现了生活的对话本质。”对话永远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过程。从哲学意义上说,对话是不可预设的。伽达默尔说:“虽然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但实际上越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一方的意愿进行。因此,真正的谈话决不可能是那种我们意想进行的谈话。一般说来也许这样说更准确些,即我们陷入了一场谈话。”[10]而这就跟对话教学的教育性产生了一些悖论。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这两者的统一,否则就形成了许多教师一味追求哲学意义上的对话性,而不顾对话教学上的教育引导性。甚至有的教师走向对话的极端,认为课堂上只要是教师的引导、组织都是破坏了对话精神。这个教学理念危害性极大,特别有必要在哲学意义的对话性与教育意义上的对话性取得调和,进而根本上以前者服务于后者。因为“教育作为人类的活动,相对于个体的经验而言,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它对个体总是具有塑造性与引导性,而个体总是要接受教育的引导和塑造”[11]。这是由教育自身的本质决定的。
教师在对话教学中的有效引导,实质上就是扮演好“平等中的首席”的角色。“作为平等中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的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权威也转入情境之中。”[12]
教师作为对话教学的必要的引导者,其原因正如邵巧治在文中所说:“从社会学角度看,对话是有一定的相同资格的人之间的交流;从文化学立场看,两类人或两个人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追求才能坐下来对话。从这个角度,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对话。因为教师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生活,阅读经验都超过学生之上。”[13]所以需要担负起“平等中首席”的任务,在知识及经验上给学生以引导,从而提升对话质量,加强对话的有效性。
教师组织、引导的内涵主要在爱心与知识上。爱学生是根本,马丁·布伯说过,真正的对话就是“从一个开放的心灵到另一个开放的心灵的对话”。雅斯贝尔斯也对缺乏爱的教育提出过批评:“现行的教育本身却越来越缺乏爱心,以至于不是以爱的活动——而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从事教育。”[14]
在知识上,教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心理学及教育学的相关知识来指导学生,使对话获得知识保证。总之,就是通过教师的引导促使学生成为优秀的对话者。
总之,语文教学中的几个误区是对话式教学中存在的,但只要从对话教学的精神出发,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矫正,一定能有所改观。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6.
[2]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35.
[3]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344.
[4]王尚文.中学语文教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7.
[5][8]卢派清.对话教学的误区及对策[J].贵州教育,2007,(9).
[6][7]腾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77.
[9]蔡丽雯.对话式语文教学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对策[J].教育导刊,2007,(4).
[1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87.
[11]金连去.理解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1997,90.
[12]小威廉姆.E.多尔著.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2000,238.
[13]邵巧治.试论语文课堂的伪对话的矫正[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6).
[14][德]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
(严久官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