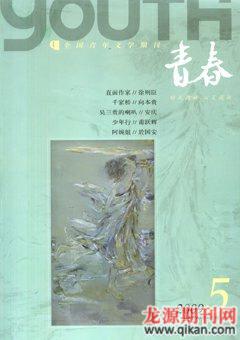随园,那一片新绿
随园,金陵古迹,遗址在今城西随家仓一带、清凉山东麓的大片地区。园始建于明末复社名士吴应箕,清代归江宁织造曹家,传为《红楼梦》中大观园之原型。曹頫被抄家后,园没收入官,复归继任织造隋赫德,取名“隋园”。不久,隋也获罪抄没,该园再次入官。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曾任江宁府尹的杭州人袁枚辞官卜居,购废园依山重建,就势取景,改称“随园”。袁为一代文坛盟主,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有《随园记》、《随园诗话》等名作传世,随园之名得以远扬。
校史逾百年、桃李满天下的南京师范大学即在此地。校园内坡岗起伏,林木幽深,楼台绰影,实为金陵文脉之所系。故南师人常用“随园”来指代母校,此二字遂成为这座“园丁摇篮”的近代高等学府一个富有美感和韵味的“爱称”。——题记
从“志愿”说起
我当过近二十年老师,细想起来,这“职业生涯”的选择是从一张报考“志愿书”开始的。1959年那会的高考,考生填报志愿与今日不同,并非考试成绩公布后的“量体裁衣”和“有的放矢”,而是在报名时“尽情挥洒”,无须做过多的权衡与算计。毕业于“江苏名校”扬州中学的我,一个满脑瓜幻想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在可以填报“十个志愿”的表格上,几乎囊括了当时我知道的所有名牌大学:从“五四”新文化摇篮的北大,到黄浦江边的复旦;从珞珈山下的武大,到省会所在地的南大……一心想当作家,自然将中文系作为所学专业的“首选”,而出身教师之家的背景也让我对“读师范”抱有兴趣,因此“南师中文系”便列入我报考的第六、也许是第七志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对后来录取了我的母校的“大不敬”,幸好母校胸怀宽广,把迷途的孩子给领了回去。
说到“志愿”,不能不提及高中毕业前夕一次名为《我的理想》的主题班会。那是一席让即将离巢的小鸟心生彩翼的“梦想大餐”,同学们畅谈各自的人生目标:有的要当飞机设计师,有的要拍“香味电影”,有的要做地质勘探队员……;我的发言比较靠后,说不出更“精彩”的,便灵机一动,竟说自己想当旅行家,不仅要走遍世界,还要去拜访各位同窗,乘你设计的飞机,看他的“香味电影”……说得大家都非常开心,未来“旅行家”也有几分自鸣得意。1999年金秋,高中毕业四十年,我们原班人马从天南地北回到了扬州中学当年的教室内,坐在从前的座位上,汇报阔别后的情况:飞机设计师成了钢都建设者,“香味电影人”变成了育种专家,勘探队员当了教授;而我的教师生涯是在“不惑之年”结束的,上世纪八十代初我由教育战线调到南京市文联工作,参与组建市作家协会,改行成了一个有机会到处“采风”和“探胜”的“码字工”(叶兆言语,“码字工”是他对作家职业的戏称)——从那时起,我的确走了不少地方,但离“旅行家”的目标,还很远、很远。
那么,我的“第七志愿”,当年填报师范学院、日后也实践多年的“教书育人”的崇高理想,是否因此就落空了呢?说实在的倒没有。无论以前在讲台上打开教案,还是现在面对电脑写作,我都清楚自己肩头的职责,即使在潜意识里也没有遗忘。至今我仍会做这样的梦:上课铃响了,学生们已纷纷走进教室,身为老师的我却因为找不到课程表不知道该进哪个班级的门而焦急不已……如此“迷途”,不也是内心深处依然“执着”于初衷的一个证明吗?而要记叙这一切的由来,还得回到那“初衷”落脚和生根的地方——离石头城不远,靠清凉山东麓的校园深处,那一片沁人肺腑又动人遐想的葱茏馥郁中去。
中大楼纪事
大学之“大”,首先从建筑外观上可以看出来。有“最美丽校园”之赞誉的南师大(当年叫南京师范学院,简称“南师”),在我这个来自苏北平原的一年级新生眼里,最大的特点是校园里有山,山上有楼。楼群中首屈一指的当数“中大楼”——今日南师大的文学院。它依山而建,正面看好像只有两层,舒平、宽阔;侧面看,随山势起伏,逶迤而高峻,将一座西山的轮廓线拉上了蓝天。袁枚在《随园记》中谈他的造园心得:“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引以为傲也为世人所称道全在一个“随”字。以此来观照今日之“随园”,作为西山主体建筑的中大楼“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以说是最能反映个中意趣和神韵的了。
治学亦如登山,整整四个寒暑,我们无一日不与此楼打交道。在它敞亮的阶梯教室上大课,在小教室开班会,资料室查资料,办公室报到、拿成绩单……大多数日子里,一下课,不同年级和班级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会早早把书包放进那宽大的与资料室相邻的自修室,在长条桌上排好队,为下午或晚上的“自修”作准备。学文科,离不开书本,校图书馆一证可借七本书,本系资料室有更多的“专业参考”,如《金瓶梅》和《十日谈》之类,可惜到了我们这一届“时运不济”,奇书都成了“秘藏”。听一位后来与我在中学同事的高年级同学说,1958年大跃进时,中文系里“放卫星”,学生要编“文学史”,为曹雪芹创作“红楼”铺路的《金瓶梅》不读如何写“史”呢?反复研审的结果是,由这位同学担纲“独览”此书,因为身为复员军人的他“已婚”,有了“识别能力”不怕中毒了。有趣的还有,该同学后来被批为“走白专道路”,传说中的理由之一竟是他“值日扫地时,一手拿书看,一手执条帚,焉能不迷失方向!”当然,这也只是那个非常年代里受“左”的影响比较极端的例子。
好学与苦读,是南师人的传统。入学不久,高年级同学就同我们班结对子,巩固专业思想,传授学习方法,如做卡片、编索引之类,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这些刚走出中学课堂的新生的。大学阶段的学习,很重要的一环在于自觉、自学和同学间相互切磋、推动与激励的那种“大学氛围”。对低年级同学来说,当辅导员的高班生、给我们上课的年轻助教,以及同样年轻的班主任,都是更容易“打成一片”的。面对年长的讲师和老教授们,像我这样的毛孩子,一直到毕业都难改“敬畏之心”。有一次,吴调公先生的一位扬州亲戚托我带一件礼物给他,我腼腆不敢面呈,写了条子放在他办公桌上就走了。这位当时已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正在上我们的课,我都没有以此为由去“结识”他,许多年后我向调公先生提起此事,老教授对亲戚送他的礼物(扬州绒花)还有印象。
大约是毛泽东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刚发表不久,我们同班几个平时爱好写作的,在一位美术系朋友协助下,创办了系里第一份以诗歌为主打的文学壁报,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花枝俏》。它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在中大楼门厅内张贴后,吸引了许多眼球,也激发了其他班级的办报热情,一时中大楼内“山花烂漫”,我们几个始作俑者还真有点“她在丛中笑”的得意呢。
食堂“史话”
民以食为天,大学再“大”,也在这个“天”字底下。
我进南师的第一顿午饭吃迟了,空荡荡的大食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与教学区那些华丽的大屋顶不同,转过西山看到的竟是一座我从未见过如此简陋又巨大的芦席棚。正是汹涌的吃饭潮过后,棚顶上泻下的日影在有桌无凳的黄泥地上闪烁,菜已卖光,只剩下几份盐水煮毛豆。那瘪瘪的豆荚长得出奇,除了品种的关系,还因为两头未剪,不同于家里的“精工细作”。然而有一对高年级男女同学蹲在角落里,手拣长豆荚吃得津津有味,说着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
那是1959年下半年,盲目“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很快跌入谷底,困难时期的饥饿感向仍在长身体的我们迎头袭来,尤其是食量大、活动量也大的男生,缺少油水和吃不饱,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恐怕听不懂“瓜菜代”这样的专有名词了,也难以理解我们为填饱肚皮用“价廉物美”的酱油汤泡饭、一餐能喝光半瓶酱油的“好胃口”。大学里流传这样的笑话,“失踪”多日的油条又以高价“昙花一现”时,老教授狠心买了两根与孙子分享,说“孩子,快吃吧,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有这个东西呢。”我们同年级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甚至在西山坡上偷开了一小块“自留地”实行生产自救,被发现后当然少不了挨批。那时市场上还有一种价格奇贵的“高级饼”,是穷学生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却将它引入教材,以此为例讲解“困难时期的供需关系和经济政策”,因此便有好事之徒给这位很有声望的女老师起了个“高级饼”的绰号,现在想起来,她的真姓名反而被我遗忘了。
尽管如此,“天灾人祸”的日子里,身为大学生的我们仍然是“天之骄子”,每人月供32斤粮食的定量,在同龄人中是最高的。当时全国在校大学生总人数只有几十万,国家为培养一名大学生要花费多少名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与今天每年考生就逾百万的现状比较,相对数字大概要高出很多。为抵御由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浮肿、肝炎等疾病,增强学生体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劳逸结合”这四个字就是那个年代才时兴起来的流行语。课程减少了,假期提前了;体育课上教打太极拳,宿舍楼里严格执行作息制度。那位种“自留地”的同学甚至发明了一套“能量守恒论”,说男女同学的目光接触中是有“能量消耗”的,因此他无论做什么都目不斜视、心无旁鹜……多么可爱、可怜又值得人回味和留念的学生时代啊!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日三餐的“大草棚”是同“困难时期”的阴影一起消失的,取而代之并延用至今的是一座砖墙瓦顶、同样又高又大的新食堂,我们也为它的落成流过劳动的汗水。启用新食堂正值“十·一”国庆节,为此而举行的“盛大聚餐”令人难忘:每桌十个菜,前所未有的丰富。不过,菜单的内容已记不清了,若对照今天铺天盖、名目繁多又无所不包的各式宴请来,其寒碜之至非“羞死厨师”不可;留在印象中的似乎只有当时老百姓需要排长队才能买到的并不新鲜的长带鱼。
正是在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喝啤酒,好怪好怪的味道,比“酱油汤”差远了。
杨苡老师
大一那年,我当了英语课代表,教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中等身材,笑容亲切,涂着淡淡的口红,在那“清一色”的年代里有点另类,而更“另类”的还是她的讲课风格。虽说教的是英语,但她的一口京腔却随时能够从那枯燥得不能再枯燥的“九评”英译课文上离开——“九评”是当时全国皆学的批修文件,我们早在政治课上读了,又要读专为外国人“批修”而用的英译本,对中文系学生来说,可谓开了“国际玩笑”,然而这是上面的规定,于是老师便带着她的学生们“集体出逃”——不说“英格列希”了,而大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巴金到沈从文,从徐志摩到朱自清;偶而也谈她自己家的事情,她的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赵瑞蕻教授,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出自其手,我在图书馆借到赵先生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也在诗歌朗诵会上景仰过他的风采。我们的英语老师,同样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她就是当今江苏文坛上受人敬重的祖母级女作家杨苡先生。
杨苡老师出身天津名门,胞兄杨宪益早年留英,和夫人戴乃迭归国后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铺路架桥。杨苡老师是抗日烽火中的流亡学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新苗”,在她的成长路上不仅有良好的家教,更多的还是“五四”那一代知识精英和文学大家的栽培和熏陶。虽然她教我们的是“副科”,但由于她的另类教学法,副科变成了“正课”,我们从她广博的见闻和率真的谈吐中不但学到了活的文学史知识,还了解到当代文坛的风影云絮、龙鳞鸿爪;还有她在报刊上发表的隽永活泼的文字,甚至包括她一度被错误批判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激发了我们对文学的兴趣和思索,更不用说许多年后她的经典译品《呼啸山庄》和获新时期《人民文学》最佳作品奖的散文名篇《梦萧姗》了。
我和杨苡老师的师生缘就是这样开始的,不仅我曾受教于她,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同班女生也曾在她门下选修英语。说来惭愧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学了两年的“英格列希”,在离开教室后几乎连同26个字母全部还给了老师,但老师所言传身教的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爱国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执着追求,如“爝火”般传递和燃烧在我们心中,任凭岁月的雨打风吹也不会熄灭。“文革”浩劫以后,毕业多年的我同杨苡老师、赵瑞蕻先生经常聚首于金陵文坛,我在文联和作协的工作得到他们很多支持、指点和鼓励。杨苡老师有时会向别人介绍:冯亦同做“课代表”的时候,收好班级作业交到我手中,常常会“夹带”他的一首小诗,红着脸要我给他提意见,还是个腼腆的大男孩呢!
其实,尊敬的杨老师记错了,那年月的确“腼腆”的我,连这一点“夹带”的勇气也还没有的。
学者的风采
大学之“大”,决定性的体现还是在传道授业者身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南师中文系师资力量之强,不仅在全省高校中拔尖,放眼全国大学文科,也排在前列。
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南师中文系拥有唐圭璋、徐复、段熙仲、葛毅卿、金启华、杨白桦这样一批堪称“顶级专家”的资深教授,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孙望、朱彤、吴调公、许汝祉、汪靖洋等前辈正值年富力强,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上。虽说那是多事之秋,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和接踵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挫伤了老师们的积极性,但他们在讲台上和教学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品格和师长风范,依然强烈地吸引着“未来园丁”的我们,给成长中的年青一代以榜样的启示。
至今仍记得朱彤教授在107大教室讲授鲁迅作品的“盛况”:座无虚席的阶梯形教室,挤满了本班同学和慕名而来的外班甚至外系的“旁听生”。不修边幅的朱彤老师一只裤管高、一只裤脚低,即便在冬日也如此;为图方便,毛线围脖在他的颈肩上打了个死结;呈坡形的宽阔脑门上沁出的汗珠一闪一闪;鸦雀无声的寂静中,只有他那如诗、如画、如优美的戏剧台词般的人物分析和生动讲述,在课堂上空飞旋,在排排坐椅的空隙间流淌……那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理的碰撞、文学魅力的展示,同时也是一种灵魂的陶治、美的享受与升华!当然小小的瑕疵也在所难免,老教授会读错书本上的常用汉字,给未来的语文教师们留下“毛病”的谈资,但这丝毫不妨碍教学的进行,常常是教者和听者都遗忘了时间,下课铃声的提醒也不管用。朱彤老师的课时是不能以分秒计的,有幸听课的南师学生都会在自己的心中和日后的评议中为他“打高分”。
吴调公先生教了我们一年《文学概论》,他讲课略带镇江口音,条分缕析,表情丰富,讲得起劲时喜欢捋起衣服袖子,露出半条很结实的光胳膊在黑板面前挥动,以示加强语气和作出重要的论断。镇江与扬州一江之隔,方言相近,加上他是小说专家,有《谈人物描写》等专著,因此听他的课也会让我想起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沈蔚德先生教《中国现代文学史》,她仪态庄重,语速较慢,听说年轻时候在话剧舞台上饰演过《日出》中的陈白露,因此她在晚辈的眼中多少有些像从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作品中走出来的人物。
和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们不同,古代文学课堂上的先生们自然更具有“古风”。是他们带领着年轻后生穿越时空,走进灿若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殿堂,去品味诸子百家,去聆听唐诗宋词,去巡礼明清小说……虽然那已是一个“厚今薄古”和“动辄得咎”的年代,不少老师都承受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甚至有的还是“戴罪之身”,但站在三尺讲台旁的他们,无不专精敬业,风采独具,俨然就是一支支燃烧不熄的红烛、一个个深山探宝的向导,以渊博的学识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感染、影响和提升着我们。
教《古代汉语》的葛毅卿教授,清癯瘦小,常拎一个黑皮包走进教室。他的声调高亢、激越,似乎不像从他的身体里发出来似的。虽然教材有点艰深、枯燥,但那些古文例句和语法规则恰如他那并不“普通”的普通话,因为隔膜和陌生反而增添了几分特殊的魅力。了解先生的同学说,葛老师是国内有数的古汉语语音专家,他吟诵古文所运用的“中古音”最接近唐代的声韵,某电台和学术机构曾为他录音作为珍贵的研究资料保存。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我们谁不想听听李白、杜甫等千秋诗魂的声音呢?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葛教授在课堂上高声朗吟他的“保留节目”、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老先生抑扬顿挫又声情并茂的歌唱般的演绎,神奇地将我们带进了那远在天宝年间的唐诗意境。正当大家都陶醉于这“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中古音诗歌韵味时,老教授放在讲台上的黑皮包不知怎的,竟滚出一个沾着黄泥巴的红薯来……那年头“师道尊严”还存在,困难时期学校给教职员工发放来自校办农场的“福利”也是常有的事,老教授自己浑然不觉,看到了这个喜剧镜头的前排同学也不敢发出笑声。下课以后,这则“唐诗惊动了地瓜”的趣事,才在同学中间流传开来。
教《诗经》的金启华先生,高高的个子,儒雅、和霭,他以浓重的安徽口音解读三千年前的周代民歌,从热烈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苍凉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许多年后我读到他以毕生精力完成的皇皇大著《诗经全译》,才知晓他在探索中华诗歌之源上所下的功夫。他和中文系主任孙望先生、此时已调至徐州师院的吴奔星先生,年轻时候都曾致力于新诗创作,是三十年代新诗社团的活跃分子,如今都像激流中搏击过的风帆一样,沉潜于泱泱诗国的悠悠岁月和漫漫征途,同样投入了创造的热情,也同样是为了明天的出发和传统的接力。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这样由今入古、再推陈出新的范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但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楷模,所以更加亲切、也更有现实意义。
印象深刻的还有杨白桦老师的楚辞课。杨老师是胡小石先生的二公子,家学渊源,加上后天努力,他在《楚辞》研究上造诣颇高。每次讲课,仪表堂堂、西装革履的杨教授总是手执粉笔,一丝不苟地从玻璃黑板的左上角开始板书,两堂课讲下来,那笔掺糅了汉隶和魏碑风骨的“粉书”恰好占满整整一黑板,如碑刻般遒劲又严谨,看得当天的值日生都舍不得擦去。因为我们都在南京最有名的“六华春”、“永和园”等店招上熟悉了当时还健在的胡小石先生的书法笔势,虽然不能亲炙这位誉满海内的国学大师,聆听和目睹其嫡传的教诲与手泽,也是十分难得的了。“文革”中,尚在中年的白桦先生死于非命,他的学术生涯遽然中断,今天我想从网上查阅一点有关他的资料竟无所得,然而他那口老南京的“普通话”以及大有乃父之风的板书,学生想忘也忘不了。
诗歌与爱情
“十八岁都是诗人”,十八九岁、二十挂龄的中文系学生,当然离不开诗歌。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章,是从白话新诗开始的;是新诗的开山者们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歌唱表达了狂飚突进的“五四”精神,挣脱了“旧文学”所死守的思想桎梏,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下,开创出一代清新、活泼的诗风。从郭沫若到艾青,从闻一多到郭小川……无数颗年轻的心,被他们的诗句点燃。1979年以后的新诗潮中出名的中年诗人雷抒雁、杨匡满,诗评家谢冕、孙绍振,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中文系里的诗坛骄子。
我的诗心也是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起跳的。引发我第一首诗创作灵感的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人类第一次太空遨游,打开了世世代代中外诗人们仰望星海和想像宇宙的无垠空间,将浪漫诗情化成了高科技的真实。“白云呵,快让开大道;/太空呵,敞开了怀抱……”我以一首稚嫩的小诗《在宇宙的大街上》发表于新华日报副刊,很快在班级内外产生了反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现实生活中的“诗歌王国”却仍然是严峻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文学批评,让共和国诗坛上许多优秀歌者都“消失”了身影。那时,我最倾心的诗人之一是电影《阿诗玛》的原著作者公刘,当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他的诗集《在北方》时,读到《五月一日的夜晚》、《风在荒原上游荡》、《夜半车过黄河》、《致中南海》这些昂扬又缠绵的篇章,真有如获至宝的惊喜。爱不释手中,我除了跟同学中的诗友一起分享阅读好诗的愉快,还跟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生一字一句地将那已经“绝版”的美妙诗集抄写下来。我们将“手抄本”保存了许多年(同样经历了人世的磨难,如“文革”中的抄家、下放等等),直到1988年初夏举办“首届金陵诗歌节”,同仰慕已久的公刘先生初次见面,我才有机会将它出示给作者本人。公刘先生当即在这本纸页已发黄、抄满了他诗作的横格笔记本上题词留念,写下了“患难知音,铭感五内”八个大字。
我在南师结识了我的第一批诗友和文友:同班王盛、张贞忠、徐德顺,同年级的顾明道(顾炯)、王宜早、陆拂明,高我们一班的曹钟陵、王长俊,低两班的何永康。青年教师周仲器是位诗人,在他领衔的一次全校征文比赛中,拙诗《古巴的眼睛》荣获一等奖,奖品是一枚精美的书签。由于诗歌和文学,我得以结识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我已在这组回忆文章中两次提到她了,感谢母校给了我这份命运的恩赐——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无论我生重病住进医院,还是无辜受“左”害失去自由,她都没有离开我,成为我生活和事业最安全的港湾,而且,这位南师毕业生除了贤妻良母外,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优秀教师,像无数南师人一样,在教育岗位上以坚持不懈的默默奉献,播撒和绵延我们曾沐浴其间的随园苍翠中那一抹沁人的绿色。
感赋《校园草》
有“天下最美丽校园”之赞誉的母校,在许多毕业生的记忆里,都跟100号大楼前那块平坦、广阔又丰茂的绿色大草坪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当年跨进南师大门时,是它给予每一位新生这偌大校园内满目葱茏的“第一印象”;四年之后,当我们即将离校,也是它作为背景和底色,在我们毕业班师生合影的纪念照上留下了母校的“深情眺望”,成为所有南师人珍藏箧底和心头的宝贵记忆——都说孩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视线;在我看来,这映照南山松柏、吹拂随园晨风、飘溢四季花香的南师大草坪,就是母校敞开慈爱的怀抱迎送莘莘学子的最好象征。她的华美与清新、蕴藉与芬芳、充满活力和生机无限,是弃官隐逸、诗酒风流在“后大观园”内的随园旧主所难以逆料,也难以比肩的,因为今天的随园之美,就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时代精神的发扬来看,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已经不是一个“随”字所能够代表的了。
2003年春天,我们1959年进校、1963年毕业的中文系四班在宁同学,筹备“毕业四十年重返校园聚会”,向外地同窗发出了邀请,想不到碰上了“非典”,计划被迫取消。2005年,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还是年轻助教的冯云青老师步入古稀之龄,在宁同窗有心为这位谦和、仁义、律已甚严的好老师做寿,只长我们几岁的云青师说什么也不肯,甚至动了气。为了表达多年来的师生情、校友谊,我们几个凑了一副对联,请同学中的大书家王宜早教授挥毫相赠:
藕塘云絮香飘随园路
南山青松情系学子心
上题“云青师补壁”,落款“五九三四班同学”。“五九”是我们进校时间,“三”是中文系代号。“藕塘”系云青师故里,“南山”指校园内的教师住宅区,联语中嵌入了冯老师的名字。我们的班主任攻现代文学,为人低调、不事张扬,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在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动乱年月里,他恪守信念,保护同志、爱护学生,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南师大作为“园丁摇篮”最可贵的校风与品德。
2007年春天,同班好几位学兄、学姐年届七旬,大家在老班长王盛教授的聚福园新居里欢会。王盛兄长我三岁,数十年来我们情同手足,曾以“夏一代”作为共同笔名写诗投稿,在《雨花》上发表过《春风踏着海浪走来》这样境界开阔又富有朝气的抒情诗。他是海内知名的许地山研究专家,曾任晓庄学院中文系主任,退休后仍勤于笔耕,其新作《缀网人生:许地山评传》不久前在香港出版。我以一首《校园草》为他祝寿,此诗又题《迎七抒怀》,有感于我们从“青青子矜”转瞬间成了“白发翁媪”,但“三月芳菲”犹在心中,“落花结硕果,芳香四海飘”依然可贺可期。诗不算长,兹录于后,作为这组系列文章的尾声,与所有南师人及尊敬的读者们共勉:
金陵春三月,芳菲何处找?人云聚福苑,我说校园草。
识君三月始,南山风华茂;青青大草坪,丹心著妖娆。
沐春复四载,同窗亦同道;草根紧相连,绿鬓存旧照。
甘作随园风,喜将春雨浇;情谱灯下曲,晓庄育新苗。
倏忽古来稀,聚首皆二毛;缺齿话南山,松柏不言老。
生年定满百,笔耕助逍遥;落花结硕果,芳香四海飘。
我写三月赋,功归校园草;天意犹怜绿,春风颂师表。
责任编辑维平
作者简介:
冯亦同,男,1941年出生。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原南京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诗集《相思豆荚》《男儿岛》;文学传记《郭沫若》《徐志摩》;散文诗剧《朱自清之歌》等。
——“随园夜话”班主任沙龙10周年学术论坛活动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