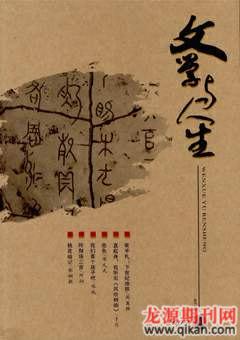直起身,我听见《风吹树响》
才 苟
《风吹树响》是一本书,也是一个短语,它带给我的首先是一种动静,低分贝的叙述的声音,然后才是文字上的建筑。声音不全是从底层发出来的,而且它的丰富内容本身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声音,是低微的身体位置所察觉的事物本质通过声音这一形态化的要素呈现出来。《风吹树响》,它多半打开的和作者意欲打开的,事实上是不同环境不同季节不同人性认识的一种表象,很繁复的过程和场景性的定位,不得不叫人联想——风起树才响,风起之前和风吹之后的景象,以及有着丰富个人生活体验和丰富个人写作经验的作者的处境。
我一直是坐在南方的一把椅子上不想动弹,这无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注脚”,当想象多于实践的某一个人给自己的位置命名为一把木头椅子时,显然不是一个充满文学野心的解释,而是一个具有好奇心的偷窥者。他眼光局限,“预谋”难以实现,想直起身体,走出这种局限时,《风吹树响》从空气中跌落,很有厚度,落地有声,同时颠覆了惯有的倾听姿态。
它的作者周蓬桦,山东人,读书万卷,出书数卷,成绩斐然,名声远播。我一直不敢轻信这些虚无的东西,有时候会仰望,就像每每看见天上飞过的云雀,它在我仰慕的开阔处飞得很自由,但是它也仅仅是一只飞过我视野的鸟儿,不会落在我的头顶,给我膜拜的机会,它很快就飞过去了,简单得只有时间。我认识的人就会不同,我经常这么想,他因为我在南方才飞向南方,他需要我领受的是他飞行的姿态,还有另一种可能,他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我能看见的高处,我能发现的大小,他用力地证明给我:你坚持了,你发力并且努力在提升。他已经飞了很远的路,我还没开始。周蓬桦先生的经历我无法妄为地去猜度,有一天我通过网络将一些简陋的文字送到他面前,他看了,给了我一个惊喜,又给了我写下去的信念。并不是说知遇之恩就应该回报,而是一本好书是需要读者读出味道来的,何况周先生用的是重笔,他无意隐藏在文字里面的情与思打动了不止我一个人。在经验面前,在事实面前,我仅有的力量是抓住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散文的背后,不仅是站着一个人,更是孕育那个人的土地。周蓬桦先生生活在山东偏东的地方,那里有独特的地貌和迷人的人文景观。这些都是陌生的,我需要在他的文字中找到它们,然后串联在一起,构成属于周先生精神领地中的乌托邦。《打麦场》里有现实的疼痛;《干旱的日子》村庄里集体失语;《被雪掩盖的谷仓》中有一只容器在童年的时光中像一个能装下生死的盒子;《敞开》里竟然还有一枚果实,含在口中的一辈子,都是苦涩的;他《还乡》不是为了看望故人,而是寻找自己,他发现自己丢在故园的某个地方,他或许在那里拾回一些梦,或丢下一些遗憾,总之他用他的抚摸让故园出现了对应的轮廓……不能再寻找下去了,我已经被他深沉的忧伤伤到了。忧伤是俯地魔,贴近乡村,和村庄上的烟火生活息息相关。他将忧伤托孤和深刻在小辑的名称里:微火——叫喊——黑管——房间——浆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取出如此有内容的名字,仿佛将他骨子里流淌的忧伤稀释在里面。我用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去联想和虚构这些名字,以及名字统领的散文篇章,想不透彻,只能询问。他说依靠它们分类,按照大致的情绪走向归类在一起。这个答复很明确,我却理解得很朦胧,也就不再往更深处想象了,这样做的唯一结果是更加忧伤。
带着沧海浮云笼罩着的情绪继续行走,有些决定竟然果断起来。周蓬桦先生的《风吹树响》究竟让一种什么样的声音高扬起来,他听起来好像轻歌慢唱的流水旋律最终给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他好像有些迷恋疼痛似的在自己的手臂上文身,好像画出来的就是一棵竹子,每一个节段上都有一条很深的刀口,行走到刀口的地方你会逗留、体察和困顿,伤口上的血分明已经凝固,变成黑褐色,让你既理解了流血的过程,又能看到愈合的希望。《别人死的日子》将暗示和现实缝合在一起;《风吹树响》里一只麻雀,它的死因是从胶东平原上刮起的风,作者描写中没有消极,七天七夜的风竟然卷不走一个少年郎坚定的信念——从这里,我好像找到了线索,事实上作者身上与生俱来的坚定,或者是在经常席卷村落的狂风中锻炼出来的信念,最终给了他文字胡杨一样坚韧的生命力,几十年就这样寂寞而平静地坚守在文学的身旁,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一天天进步,他已经不满足于在村庄里发掘疼痛和悲情,他用幽默和俏皮的口吻打诨,读者这时候也变得轻松了——既是阅读的,又是身心的。
也许距离淄博太遥远,也许距离蓬桦先生心性太遥远,以致有时候在回味他的描述时觉得自己不配在他专属的乌托邦里行走,他歌唱的起调是清音,纯粹得像一枚浆果,有着太绝妙的色泽与线条。我久久地捧着《风吹树响》发呆,却忘记了自己有限的臂展采摘不到那枚浆果,它成功地装扮了树,成功地扮演了树响的一部分,依旧是迷人的清音,倾听之后却不能逼视,这样的结果表明,我成不了学唱者也写不了诗歌。然而,居住在山东以东的蓬桦先生,他既是出色的歌手,又是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