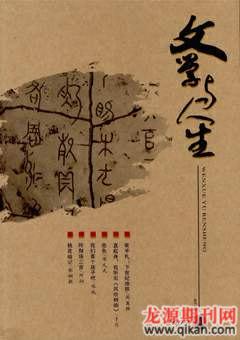我们要个孩子吧
陈 纸
陈纸:本名陈大明,曾用笔名橙子,1971年生,南宁市首届、第四届签约作家,出版散文集《停下来看一朵花》、中短篇小说集《有鬼》等,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城》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0多篇,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广西文坛后三剑客之一”、广西作家协会理事。现为《南宁日报》文艺副刊部记者、主编。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我和妻子结婚八年后,决定要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我先作出的,还是妻子先作出的。起初,我们都为这个决定大吃一惊,好像还彼此陌生地看了几秒钟,双方的眼神里除了陌生,还有很多紧张。就像我们当初决定结婚一样。
不知是谁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我们要个孩子吧。
那会儿,刚熄灯,我们正像往常一样,穿着彼此的睡衣,占着彼此的地盘,滑进了被窝,准备背对背安稳地睡个觉。
这句话像平地起惊雷,把平静的空气撕裂了。漆黑的卧室好像也抖了一下,我们都翻过身来,再也睡不着。
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去细究这句话是谁先说的。我们直接讨论:是不是真的应该要个小孩了?
更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对此持有疑义。妻子首先说:要了一个小孩,你可能再也不会那么野了,我要你天天在家煮饭拖地板冲牛奶喂小孩。
我说:要了一个孩,你可能再也不会那么疯了,你话剧团里那些涂得像鸡屁股鸭屁股驴屁股的脸,就不会像苍蝇一样往你可爱的脸颊边凑了。
妻子拉亮了灯,刮了一下我的鼻子:你损不损人,至于把我的同事骂成那样吗!
话题一下子明亮起来了。我们像两个刚刚懂得什么是游戏的孩子,我们都跃跃欲试,好像前面八年的煎熬,就是为了等待做这件事。其实,在这八年中,我们都曾先后试着刻意地去走进这个话题,但不知是谁(也许双方都干过这个勾当),总是先后刻意地去避开了这个话题。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妻子除了讲话剧团排练演出的事,就是讲穿着打扮的事,这些事在晚上无数次地爬上我的身子,代替了她前两年风情万种、妩媚娇柔的躯体。我渐渐地习惯了这种生活,就像习惯了我办公室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女人。
我得承认,我是老马吃嫩草,出生于一九七一年的我能找到一个“80后”,这是我的福气,我曾经的的确确是这么想的,只是,后来,随着这种风气愈演愈烈,这种幸福感越释越稀了而已。所幸,我是经过了无数次挑拣才选中她的,我对各种各样的女性略有阅览,否则,我也不会与她结婚,并且容忍得了她的撒娇疯癫。
所以,既然谈到要一个孩子,而且她没有异议,不管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和配合。
妻子显然在发挥她在这个两口之家中的一贯作用,她把被子撩起来,露出她的真绸睡衣。灯光下,我又一次看到它溢出炫目的光彩。
妻子的表情很丰富,也很严肃,我想起了她在团里排演某一部主旋律的话剧的情景,她的表现在舞台上一模一样,她向我凑近,我的鼻息对撞着她的鼻息,她把蜷曲的身子拉直,语气也被拉直,她说:这件事必须认真对待!
我说:是的,必须认真对待。
妻子说:不是开玩笑的,这次。
我说:我知道,这次不是开玩笑的。
妻子说:得有充分的准备。
我说:是的,要有准备,怎么准备?
妻子又往我面前凑了凑:没刷牙吧?满嘴的烟味和酒味!
我忙不迭翻身下床,再回来时,还是挨了她一个耳刮子:从今以后,不得抽烟喝酒!
我说为什么呀,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当我脱口而出这句话时,我就知道我是在找骂。
妻子说:为什么,为了我们家的希望和未来,为了我们家不会生一个像你这样又懒又笨的白痴!
我说:好,我是白痴,我答应你,不抽烟不喝酒,来吧,为了我们家的希望和未来……我一边说,一边往她身上爬。
妻子脚蹬手推,像个话剧中抵抗侵害的烈女,拼命保护自己。
我更加紧张而陌生:你、你、你怎么啦?
妻子踹了我一脚:白痴!不是在今晚,今晚不是排卵期。排卵期你懂吗?白痴!
如果以知不知道排卵期来衡量是不是白痴,那我就是白痴。为了不永远做白痴,我必须去了解什么是排卵期。
我在网上搜索“排卵期”三个字,结果,跳出来的条目总共不下三万,它们像一个个精子一样铺天盖地而来,而我的目光,就像每个月才游出来的那枚珍贵的卵子,不知该停留在哪个条目上。我想,当我的目光停留在哪个条目上,那就会像卵子与精子结合,肯定会有一个结论的。
我双眼一闭,点击一个条目,我把眼睁开,那条内容像双腿一样张开,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教你识别排卵期:为了优生优育,请你在排卵期受孕。大部分妇女在下次来月经前2周左右(12~16天)排卵,俗称‘排卵期,排卵一般发生在基础体温上升前由低到高上升的过程中,在基础体温处上升高水平的三天内为‘易孕阶段;‘易孕阶段宫颈粘液变得清亮,滑润而富有弹性,如同鸡蛋清状,拉丝度高,不易拉断,出现这种粘液后湿润期就应计划受孕了……”
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所幸这一些内容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但我又十分地相信,这些知识,妻子十五六岁时,就熟稔于心了。我永远佩服女人,不管男人知识多渊博,女人只要稍微“现身说法”,很多男人的知识在女人面前便相形见绌。
妻子从容地准备着一切。她每天除了早早唤我回家睡觉,并且在睡觉之前与我狂吻外,就是用温度计在她的两腿之间测量。
我知道,妻子狂吻我是为了“测量”我的烟味和酒精度数,我被狂吻吻得喘不过气来,我像一名在战壕里待命许久、就等着对方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去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有几次,我按捺不住,要往“阵地”上爬,但被妻子推下。妻子一边推,一边声嘶力竭地喊:还没到排卵期呀,白痴!
“还没到排卵期呀,白痴!”——这句话从决定要一个孩子起,便成了妻子决定与不与我做爱的惟一理由。我问妻子:为什么想到要一个孩子呢!妻子扇了我一个耳刮子,说:趁你现在还对我偶尔有点兴趣赶快为你生一个!
想想,从恋爱到结婚,整整十年,我们就像游戏中的孩子,由着彼此的性子、稀里糊涂地走过来了。当年的我,女朋友像走马灯似的换,误撞入她的一句话:我们结婚吧。她就变成了我今天的妻子。今天的妻子,由着她的性子,我一路被她牵着,一牵就是八年,我由原先一头激情四溢的公狗,变成了一条在她面前摇头乞尾、可怜兮兮的看家犬了。
现在,决定要一个孩子了。这迫使我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随时待命,把状态调整到结婚的前两年。
妻子向我发出信号的那天晚上事先没有丝毫征兆。我照例匆匆审完所有的小说稿,关了编辑部的门,也把刚才小说里的所有情节关了起来。我先奔了菜市,进了厨房,接着坐在饭桌上,再进了厨房,我把围裙解下来时,妻子已盘腿坐在床上,像个打禅的和尚,扳着手指念念有词。
我刷完牙,洗了澡,坐到了床上,妻子把温度计拿了出来。
妻子的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跳,我拿着书被她扑倒在身上。
我说:干吗干吗?
妻子说:就在今晚就在今晚!
我看见妻子满脸潮红,手心出汗,当我把手搭在她的颈脖时,我感到她全身微微颤抖。
我突然不知所措。妻子也不知所措。她一会儿看着我的脸,一会儿看着我的下面。我这才恍然,跟着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下面。
妻子先我脱下衣服,她秉承了演员的天赋,比我先进入了角色,她有两腿雪白而闪亮地晾着,她的双目微闭,她在等待着我的表现。
我好像是生平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演员,我感觉到空前的陌生而紧张,我迫切地想调动情绪,想以某个标志性的肢体语言来迎合对方的出色表现。
我努力地想啊想,使劲地用力啊用力。妻子也拼命地配合,但无济于事。我看见妻子胸口一拱一拱,手一动一动,言语一句比一句重:平时行现在怎么不行啦?厌倦我了是不是?厌倦我了早说我趁早决定不要孩子,我还可以再嫁一个比你行的。妻子又等了一会儿,恶狠狠地说:这么久没给你你都不想要,是不是出去偷吃了?嗯?老实坦白,你这白痴!
我一边听着,一边闭上眼睛使劲地努力,但还是无济于事。黑暗中,我把满腔的歉意小心送给她:老婆,真的对不起,不知怎的,我今天怎么反而不行了呢?要不——开灯试试?
开灯我肯定不适应,白痴!妻子的背影像一堵墙,突然隆了起来。黑暗中,我的眼前更黑。
我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腰背上,说:可能是近来工作忙,加上家务活多,我没有精力和时间准备……
妻子翻过身,说:这种事只有我准备,男人还用准备吗!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再等等再等等,它会行的。
妻子又把身子背过去,说:再等?再等什么都干了!
痛失了第一次机会,妻子差一点打了退堂鼓,她一口咬定我在关键时候不行,肯定是在外面偷吃了。
妻子说:你还没有与以前的那些文学女青年断绝关系,要不就是又培养了新的文学女作者。妻子逼迫我:说!她到底是谁?妻子一边怒气冲冲,一边翻出我们最近几期的杂志,一页一页地看,主要是看那些作者,先是从姓名上去判断是男的还是女的,再看照片,看是长得漂亮还是丑陋。如果看到漂亮一点的,她就说:我看就是这个狐狸精,你说,是不是这个狐狸精?她说着,把手中的杂志丢到我脸上。
我不敢看,其实也看不清,没法看清。我小声说:没有那样的事,你别生气,谁都不是,你不要猜疑。
妻子把那些杂志一本本地摔到我面前,说:就有那样的事,你没结婚之前是怎样的人我还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勾引到我的,你还不清楚?
我说:现在我变了,你还感觉不到吗?我天天准时回家做你的保姆你还想叫我怎么样?
妻子说:我不想叫你怎么样,我只想叫你行,关键的时候行就一次就可以,我为了这几天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但不知怎的,就是不行,我真的对不起你。下次我一定行。你相信我一次行不行?
我安慰妻子,不但在床上用言语,还在厨房里加倍努力,而且用钱包说话,硬着头皮陪她逛商店。
妻子的火气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下来的,妻子还说:一定要一个孩子。她的语气仍是那么坚定,让我很是感动。
如果这时我还不有所表现的话,那真是太对不起她了,我想了一整天,赔着小心对她说: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这次我们换个地方吧?新的地方容易产生新刺激,肯定行。
妻子的眼睛放出光彩:换地方?行啊,去哪里?
我一边看着妻子的神情,一边慢慢地把话放出来:去,野外?……
妻子一只手高高地抡了起来。
我忙侧过头,又慢慢说:去,去公园吧……日坛公园、天坛公园、地坛公园,都行。
我见妻子的手一点一点地放了下去。
妻子说:天坛公园不行,天坛公园因为一口钟,引得人太多,而且都是外地人。
我说:那就地坛公园吧。
妻子说:亏你还是个被文学搞的人呢,一想去地坛公园,就想起那个坐着轮椅的作家,我怕你跟他是熟人,不去。
我带着妻子雄赳赳去日坛公园。
日坛公园离我们家最远,好在有的是时间,也不怕时间晚,我们洗完澡了才出门,我看见妻子一路走,一路时不时地看着我。
我明白妻子眼中的意思,我边走边在心里为自己打气:你要争气啊你千万要争气啊!
从我家到日坛公园,有三路公交车,我拉着妻子上了一辆双层巴士。我推着妻子的屁股到了上面那一层,而且是坐在最前排。
透过前面的玻璃窗,往外一看,路一下子变得低了,掠过的桥洞也变矮了,两旁的高楼大厦好像也弯腰了。我四脚叉开,一副凭海临风的样子。
妻子白了我一眼,说:等会儿像现在这样豪情万丈就好了。
十七八站的路,才到日坛公园。下了车,从立交桥上穿到对面,妻子拉着我进了公园旁边的肯德基。我们要了一份三十一块五的套餐,有汉堡包、辣鸡块,还有薯条和饮料。妻子只吃了一个汉堡包,其余的三样命令我干掉。
我乖乖地、认真地干掉了,妻子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走出门时,她还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这可能是我与妻子结婚后第一次逛日坛公园。八年多了,恋爱时看起来恣意疯狂的树们,这会儿在我眼里仍躁动不安。
我和妻子的脚步都很急,我看妻子的眼神局促不安、四处乱转。我们先是穿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道路两旁林子间的凳子上一坨坨的,全是人头,透过乳白色的灯光,像顽固的、风化的牛粪一样。
肯定没有位置。妻子有点生气地说。
往前走,去钓鱼区,那里不是有几处凉亭吗。我拉着妻子干脆不往两边看,直往前奔。
经过一片闹区,整块都是水泥、大理石铺的广阔空地,乍一听,闹哄哄的,仔细一听,好像只有音乐声,走进去一看,大多是老年人和携儿带女的青年夫妻,还有舞动的人群。妻子的脚步慢了下来,她冲着一位手推车里的小孩扮鬼脸。多么熟悉而动人的鬼脸啊,它曾经在我们初恋的时候,和结婚后我的梦中出现过。与妻子自认识到今天,我惟一能够常常记起她的美好之处的,就是鬼脸了。这个鬼脸曾经把我的年龄拉到了与她一样冲动的状态,这个鬼脸曾经让人确认她纯真可爱。现在,这个鬼脸又出现了,它让我回到了美好的从前。
想到这,我倏地从背后一把将妻子拦腰抱住了。我甚至完全把她抱起来了。妻子先是怪叫一声,然后喊:你这流氓、白痴,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不知道?我涎着脸说。
不行不行,这里人那么多!妻子说,口气却比我还急促。
我把妻子放下来,我们加快了脚步,朝钓鱼区奔去。
到处都是人呀,怎么这么多人?他妈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北京人都缺这么一块干事的地方吗!我看见妻子像个饿极了、正四处张望、伺机猎食的母鹿一样,她一边急走一边又说:你说这些狗男女中有多少对像我们,是正规的夫妻?又有多少对是在谈纯洁的恋爱?
我说:老婆,我等不及了,管他呢,人多才刺激,我这会儿行得不得了,来吧!我一把将妻子推到一棵黑暗的大树下,准备行动。
妻子急促地扭了两下头,狠狠地打掉了我的手。
我的身体一阵发热,头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妻子的怀里。
从日坛公园回来,我看不出妻子是什么心情。我只听到妻子说了一句:回去你自己洗裤子。
我想,这个孩子肯定是没什么希望要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挫折感。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决定要一个孩子是不是我先提出来的。因为我的内心浮出的这种渴望很强烈。同时,我又为自己感到可怜,接着,为妻子可怜,为我们两人可怜,为还未怀上的我们将来的那个孩子可怜。
妻子倒显得比我平静,她说:哪里地儿最大,人最少,最清静呢?
我认为妻子是在幻想。结婚之后,我才发觉,妻子很多话都是幻想,我想,这也许是上世纪70代初期出生人与80代出生人的区别之一吧。
我想都没想,笑着随口说:王府呀,夜晚的王府地儿大人少,连鸟都飞不进去。
妻子双手一拍被子,说:对啊,王府,就是王府,我们到王府去,嘿嘿!
我睁大眼睛,看着妻子,说:你疯了?
妻子说:你才疯了,到王府去,你就是王爷,我就是王妃,嘿嘿,真好玩!
王府我不是不熟,王府的研究员王九月是我的作者,我曾经在我们的杂志上连载过他有关王府的散文。我对王府最初的了解就是从他的那些散文中获知的。后来,王府成了我与王九月联络的纽带,每次与他见面,他就与我聊王府。王府——这个神秘幽深的词,通过他喋喋不休的叙述,在我心中渐渐变得亲切随和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没去过王府。我把要去王府的想法告诉王九月,王九月很高兴。这就像一个媒人,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说了几年的好话,对方终于愿意见对方一面一样。
王九月在电话里说:你早该去一趟王府了,哪天我陪你去!
我说:我带我老婆去。
王九月说:好啊好啊,你带谁去都没问题。
我说:我要晚上去,最好是九点或十点钟去。
王九月说: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在王府管理处住了七八年,还没有一次在晚上九点以后进去过呢。
我说:那就进去一次。
王九月说:没有惯例,恐怕不行。
我说:就当去采风,体验一次生活。
王九月笑了:亏你想得出来。
我把决定晚上去王府的事告诉妻子,妻子很高兴,说:要去就趁早,不然,过了排卵期。
这真是一次新鲜而刺激的冒险之旅——王九月一路上都在念叨着这句话。他手握的手电光微微有点摇晃,把妻子的身子直往我的怀里摇。
周围是高大的寂黑,近处有惨白的清辉,裹住我的是一层冰冷。
我们是从王府的后门进去的,我们走进了王府的后花园。
王九月轻声说:只能到这里了,到这里都已经是破例了,不能再往前走了。
妻子说:这里是哪里?
我说:后花园呀,别的地方不能去了。
王九月说:王府只有后花园可以参观游览,其他地方都是单位办公地儿了。
妻子环顾四周,笑了:这里真是冷静安宁啊。
我对王九月说:我和老婆商量着想在这里过一夜。
王九月说:好啊,如果你们不怕孤魂野鬼的话。
我说:这里有什么孤魂野鬼?
王九月说:王府的女子跟深宫大内的女子一样,一旦失宠,便在冷寂中等死。也有被处罚而死的,孤魂野鬼自然难免。
王九月接着说:还有不计其数的冤死宫女,听说到了晚上,有人能听到她们如怨似艾的啼哭声,一旦附着到人身上……
妻子的双手把我的胳膊拽得生疼。
我说:王九月,别说了。
妻子说:我们快走吧!
王九月说:当然,这些只是迷信的说法,当不得真。
我说:出去吧出去吧!
王九月笑了几声,说好。
第二天,王九月给我打电话,先笑了几声,然后说:怎么样,经过我添油加醋一番,她应该打消此念了吧?
我说:九月,我只是要你劝劝她,没叫你把她吓成那样,回来后,她一直冒冷汗,说胡话,什么孤魂,什么野鬼,把我吓得也没睡着。
从王府回来的妻子显得越来越烦躁,她有时会狠命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和盖在身上的床单,当然,也会撕扯我的头发。妻子好像把这套叫“家”的房子看成了天底下最容不了身的地方。她在客厅里、卧室里来回走动,不知所措。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妻子的举动让我心疼,也让我不忍。
我说:亲爱的(这三个字我是很少很少说出口的,只有在我觉得极大亏欠她时的有限的两三次才说过这三个字,其中有两次是恋爱时,一次是婚后),我们到宾馆里去住两个晚上吧。
妻子说:住宾馆不要钱呀,白痴!
我说:明天有我一个作者的作品研讨会,他是个广东人,小说写得奇臭,但腰包里的钱奇多,自费印了一本书,非要到北京来发红包,还包了京西宾馆一层楼,找了一帮所谓文学评论家和刊物编辑来填满所有的客房。
妻子扯了一下我的头发:老实坦白,是男作者还是女作者?
我说:当然是男作者。
妻子说:他也给你在宾馆开了房,是不是?
我说:是,两个晚上。
妻子说:我去填另半边床吧,我怕你给小姐睡了。
我说:我是真心真意欢迎你,全心全意等着您。
妻子说:这几天正在排一个该死的剧,下个月要到台湾演出,晚上要加班……
我说:不要紧的,我等你,多晚都等。你该不会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潜进来吧?我学着她在剧里的一个动作——拍了一下手掌说:那就太刺激了!
妻子的眼神是从未有过的柔软:你在房间等着吧。
第二天,我赶到京西宾馆,我作了精心准备。但是,在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我简直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像梦游一般。我的准备全“作”在与妻子的那件事上。我叫服务员到房间洒了一遍香水,我还利用午休的时间去三里屯一家文化画廊里花三十八块钱买了两块装裱着《杜鹃山》和《红灯记》剧照的画框放在床头,那是妻子最喜欢的两部剧。为了这,我曾说她这是惟一一处不像上世纪“80代”女性的地方。妻子反驳说:这是艺术,你懂吗,艺术是跨越国界和年龄的,你这白痴!
我还在附近一家鲜花店订了一束鲜花,玫瑰与紫色百合夹杂,几株满天星点缀其间,像激动不安的心跳敲击在甜蜜的湖面。
整个下午我都坐着,微闭着眼,那些文学评论家言不由衷的话根本停驻不进我的脑海,我似睡非睡。在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那个作者的女秘书笑我:“陈老师今天状态不好,比上次到广东来讲课时差多了。”
那位作者挥挥手,制止了女主持的话,满脸却是笑:等一下你多灌他几杯,他的状态不就好了吗!
研讨会上的人都看着我笑,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文学味一扫而光,大家纷纷急不可待地离席,开赴楼下的餐厅。
大家按照级别和资历分好包厢,我的目标是绝不喝酒,我趁着几个老头子正为该进哪个包厢推让时,从他们的夹缝中溜进了记者席。记者席上的记者们不像与会者那么放得开,有两三个女记者还把一双手放在桌下,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我怀疑是因为我来了的缘故,便扫了全桌一眼,挑了一个认识的女记者问:你们何主任还好吗?
那名女记者有点受宠若惊地回答:还好,不过他很少出来跑了。
我又对另一位女记者说:你们《新京报》办得不错呀,尤其是文化周刊,办得很有文化味,我经常看。
我又说:当然,《竞报》办得也很好。我的眼睛对着一位戴着眼镜、长得洁净斯文的女孩子。
我也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不想,几句话,把那些记者捧得很兴奋、很激动,本来准备拎到别的包厢去的白酒,也被留了下来。有一个年纪约莫四十来岁的男人站起来,要拿我面前的酒杯,还说:陈总编,喝白酒。
我把酒杯拿到手上,放到酒桌下:不,坚决不喝,我晚上还有任务。
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男记者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弯下腰来夺我的酒杯:是不是叫你总编还不够呀?知道你小说写得好、评论也写得好,叫你陈作家、陈评论家,你总该满意了吧!
我站起来,把酒杯放在怀里,对他说:我认识你,你还采访过我,你不要起哄啊,我今天真的不能喝。
这时,那几个女记者全站了起来,有的说,总编、作家不喝一点酒怎么也说不过去,有的在往自己的小酒杯里添酒,有的则跑过来夺我的酒杯,她们在我的怀里乱抓,真让我受不了,我只得把酒杯交出来,说:就一杯啊,象征性的,就喝一杯。
我真的就喝了一杯,如果没有女记者逼我,我一杯也不会喝的。我当时没记住桌上有什么菜,也没有记着要去隔壁的包厢为我的开研讨会的作者敬杯酒表示祝贺呀什么的,我只记得晚上的任务,没有什么有比晚上的任务更重大了。
我正乐得逍遥要吃些菜喝点饮料,一个女的端着一只杯子走了进来。她先是端着杯子沿着桌子的大致方向划了一道弧线,说了一句:各位记者,辛苦了,我敬大家。然后抿了一口。接着还不待我站起,一只手便搭到了我肩上,说:你怎么也好色,喝起鲜橙多了?状态还没出来呀?
我说:晚上不喝了,有任务。
那女的睁大眼睛:不是住在宾馆吗,你还要回去呀,审稿还是创作?
我笑了一下:没有。
那女的换成了半眯眼,双腮肌肉一耸,积了两个小酒窝,全身的肌肉好像都荡漾了起来,她改用胳膊碰我了,还说:下午开会说了你一句,生气啦?
我说:没有。
她说:我老总特地来向你赔罪的。
我说:真的没有。
她说:没有就喝白酒。
我说:真的不能喝。
她说:真的生气了?
我说:真的没生气。
她就冲着门外喊:服务员,倒酒!
服务员走过来给我倒酒,她把我盛饮料的杯子端起,把里面的饮料一饮而尽,然后用茶水冲洗了一下,说:倒在里面。
我忙说:不了不了,要小杯。
她把大杯递到我面前,说:你的酒量我们老总跟我说了。
我说:不喝不喝。
她说:我们交杯吧。
我说:真的不喝。
她把我的手臂与她的手臂绞在了一起,一只手端着她的酒往她嘴里送,另一只手把我的酒杯往我嘴边推。
我当时在想着我妻子的事,根本不在酒上,我的眼光被她的胸挡住了。我不得不看她的胸,很自然地,我把她的胸跟妻子的胸联想到一块去了。当时,她的衣领开得很低,她的手一推一推的,胸前一颤一颤的。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真好。
她展颜一笑:这酒当然好。
我说:我会醉的。
她说:醉了我扶你回房睡。
我把酒杯仰头一倒。
妻子什么时候进的门,怎么起来开的门,我一概不知。我只记得妻子很激动,我也很狂放,我很清楚我的动作很粗鲁,每次喝醉了酒我都这样。妻子非常非常讨厌我喝醉酒,她不但知道我醉酒时动作粗鲁,而且知道我每次喝醉酒时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每次我脱她衣服时,她都惊叫着誓死反抗。
这次也不例外,她知道我只是象征性地在做动作,根本不可能进入实质阶段。她反抗了两下之后,狠狠地扇了我一记耳光。
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痛了,不知道难受了,不再喊了,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再叫她来宾馆,她却关机了,打电话到家里,也没人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一高兴,又喝了个酊酩大醉。
想想,我他妈的真是失败啊,结婚八年才想到要一个孩子。妻子也说:你真是失败透顶啊,我看梁朝伟都要比你先要到孩子。妻子把手中的一本《精品购物指南》翻得“哗啦啦”地响,封面上梁朝伟与刘嘉玲的一张结婚照被她翻得春波荡漾。
我夺过妻子的杂志,我的眼睛瞪得田螺大:梁朝伟与刘嘉玲结婚了?
等你知道,人家连孩子都有了。妻子说。
我一看内容,果然,离梁朝伟与刘嘉玲结婚日已过了半个月了,但刘嘉玲的那身洁白的婚纱在我眼中仍然新鲜。
你不是说过迷恋刘嘉玲吗,这次受打击了吧?妻子说。
你不是见了梁朝伟两眼也发直吗。我说。
妻子夺过杂志,一边翻着一边说:我就要看梁朝伟,我就要看梁朝伟。
我说:我把你当成刘嘉玲吧。
妻子怔了一下,然后推了一下我的肩膀:搞文艺的都有这臭毛病,就是会想象。
妻子接着就钻进了被子,她把嘴撅得老高,声调也吊得老高:到了易孕期的尾声了,这次不行,我把你阉了!
我不说话,电视画面里,火红的高粱地被壮汉疯狂地掠倒一大片比人还高的高粱,为他劫持来的女人做好了窝。
此时的妻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荧屏。我的心也莫名其妙地狂跳起来。
我靠过去,开始抚摸妻子的颈脖——我想从敏感的部位入手,以便尽快进入角色。
妻子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她扭了一下脖子,我感觉出了是拒绝,便抽回双手,乖乖地坐着陪她看。我一动不动时,妻子的呼吸却粗重起来了,她轻轻的尖叫(是的,她控制不住地尖叫了一下,但本能地斜了我一眼,忙捂住了嘴)。
我不知道妻子在看谁,在想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扫兴,很多余。
我摸着妻子的脖子,妻子还是不理会,我把一只手伸到妻子的大腿,这时,我的手被遥控器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不知道妻子是不是无意的,我看见她盯着荧屏,好像忘记了手中还拿着一只遥控器,而且,重重地敲在她的丈夫身上。
我一把将妻子抱住,猛地压了下去。我瞥了荧屏一眼,片中传来的唢呐声激情四溢,高粱地正血一样的红。
妻子又尖叫了一声,说了句:轻点,白痴!
我不理她的话,急切地摸索着。
妻子急了:行了吗行了吗?
我比她更急。
妻子气急起来:你笨蛋啊。
我说:等等,等等!
妻子说:算了,算了。
我说:求求你,再等等。
妻子说:算了,你不行,真的不行。
我说:去他妈的!说完,像一个混球一样从妻子的身上滚了下来。
我的心骤然冷了下来。我滑进冰凉异常的被单里。
空调开得嗡嗡嗡嗡地响,像极了单调而乏味的时光。
我长吸了一口气,鼻子里好像有粘稠状的液体流出。
这时,妻子也打了一个很响亮很响亮的喷嚏。
我想,我们是不是都得流行性感冒了?
完稿于2008年8月19日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