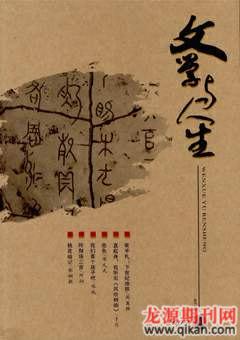河边的村落
张明润
在河边漫步,我们一定不会感到寂寞,河首先就是一道叫人看不厌的风景,而同时我们又随时可以走进一处村落。在许多地方,包括我的故乡,河与村落相互牵扯,紧密相连。现在,当我的意识重新在故乡的那块土地上游离时,河与村落的影子便在我脑子里纠缠不清。
河自然并不一定是条了不起的河,故乡的那条河叫小湾河,这河名准确地道出了这河的特征:一是小,仅百十米宽;二是弯,随地势任意流淌。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小而弯的不知名的河,它的旁边却散布着众多的村落,这些村落外表上很相似,屋舍旁均是一片长得茂盛的树林或竹林,村落的前边便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这些相似的村庄实际上还是各有其独特标记的,这种标记表现在一些物体上,或是一棵老树,或是一匝篱笆,或是一方水塘,或是一条老沟……正是这些独特的标记深深地印刻在久居村庄的人的心上,使得他们对每一个看似相似的村庄有一种惊人的辨别力。这些村庄自然还都拥有各自的村名:张家河、戴家河、前河、后河、东畈河、西畈河……从这些村名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村落的另一个共同处,那就是每个村名均有一个“河”字,这些独特的村名含义丰富却往往让人容易忽略。这些村落散布在河边似乎没有什么规则可循,然而如果我们将它们整个地纳入视线,就会发现这些村落一个个错落有致,构成一片绚丽的景致。
我们站在河边,看着河水的流淌,我们的思绪也跟着流淌起来。河是一个很容易叫人产生联想的事物,如果这时再融进了村落,我们的那种联想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河从高处流来,也从时间的深处流来。我们或许会从河的变革中去猜想村庄的历史,又或许会从村庄的变迁中去猜想河的渊源,但实际上村庄里的人并不习惯于猜想,代替他们猜想的是一些流传不衰的传说,村里的一代代老人都会给他们的后辈复述这种传说。听老人们复述传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老人们的思维跳动性很大,稍一闪失你就会滑落在传说之外。
提到传说,我的心田已变得一片潮湿,我曾认真地听过老人们复述的传说:我老家那块地方几百年前曾经是水汪汪的一片湖泊,后来湖水退尽,地面生起,湖底低洼的部分就变成了那道河,我们的先祖就是那时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来到了这里,开垦湖地种起了庄稼,同时也就繁衍了我们这一代代子孙。
我曾经认真地分析过流传于我老家的这一传说,总感到它既可信,又似乎不可信,我的眼光一时无法穿透村庄几百年的历史,我想传说是否可信并非一定重要,传说流传的意义,或许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传说之外去理解传说的真正含义。
当传说成为传说之后,我们面临的就是现实中的村庄,现实中的村庄与河相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背景,这种背景的色彩是多色调的,在这种多色调的背景下,那一个个身居村落的人们的面孔,那一幕幕乡村生活的场景,便在我的眼前清晰地凸现出来。
我老家的人很早就常常说,落在这块地方是怎么也不会饿死的。他们说这话时伴随着一种丰富的得意的眼神和手势,让人感到这话多少带有一些炫耀的成分,但这实在又是一种经验之谈。村庄坐落在河边,村里人靠种庄稼为生,而庄稼自然需要水分,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河就像是天生为庄稼而存在着,那纵横交错在田野中的一道道水沟,是河为庄稼伸出的一根根血管,河水便是这样如血液一般浇灌着庄稼的生命。村里人因河而得意,同时,也对河怀有一种深深的敬重。他们对河和河所延伸出的沟总是惦记在心,为了它的畅通;他们格外舍得花力气,哪里淤泥了,会及时疏通,哪里堤损了,会及时整修。在那种干旱的季节里,村里人的身影会在河上河下沟上沟下反复出现;夜晚,他们只有枕着河与沟里的流水声才可安然入睡。
无可置疑,村庄坐落在河边,使得村里人总感到有一种生命上的依托,但实际上村里人又是以主人的姿态站立在河与村落中间的,村里人对河的选择显示出他们的一种智慧,但他们在选择了河的同时,又使他们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无法选择,当河在他们面前变幻出另一种面孔时,他们也就不得不以另一种姿态与河相对。
那是在一些夏季的暴水期,平时作为村人生命依托的河突然变为威胁村人的凶悍之物,村里人这时无疑被河给激怒了,他们必然要全力以赴地去抗击洪水。我老家那里的人们对抗击洪水有另一种说法,他们称之为“抢命”,这一叫法实在是最通俗最深刻又最贴切不过。很显然,如果洪水冲垮了河,洪水就会无情地毁坏庄稼,毁坏村落,毁坏村里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作为一个在村庄里长大的人,老家人“抢命”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那种场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在这里我并不想对那些细节作过多的描述,因为描述往往会变得苍白无力。
关于河以及从河里延伸进来的沟,村庄里还有太多的故事。在我老家那个村子有一条老沟,它像一条巨蟒一样蜿蜒穿行在田野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关于“老沟”这一称谓,我们那时曾感到迷惑不解,老沟到底有怎样的老?许多年轻人去找村里岁数最大的永伯问过:是你的岁数大,还是老沟的岁数大?未料永伯满脸不悦,他说,你永伯难道老了吗?你们怎么能把我和老沟比?永伯那时就是这样一个极不服老又极要脸面的人,他一生有许多趣事在村子里传诵,而他最后留给村里的故事却是与老沟连在一起的。那天正午时分,村里人都集中在河边的一块稻田里拔草,在村里人俗称为“秋老虎”的毒日下,大家都在坚持着,后来就有个人影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走开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才有人醒悟过来,发疯似的冲上了沟堤,看到永伯静静地躺在老沟里,他的头横在沟沿上,一双赤脚任沟水冲刷着,他已永远不能回到田里了,在那个临近鬼节的日子里,村里人将永伯送上了村边小山上的一块安息之地,那一块地穴与老沟遥遥相对。
我在描述故乡田野和老沟的形象以及与之有关的人物故事时,我想所有熟悉乡村的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道关于田野、村庄和人所交织的风景。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蕴藏在我记忆深处的血迹,我虽不敢肯定那河边流淌的血是我生来第一次见到的血,但我却是在河边第一次看到血是怎样从人的身上流出来的。那是一个极为缺雨的夏季,老沟里的水已落得很浅了,而这时上村的人为了水要将河的上游堵住,于是在河的堵拦处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村里的汉子和上村的汉子缠抱在一起,他们的身子全是赤裸的,全都沾满了泥水,血,也就是这时从他们身上往外流,那殷红的血与河水相融,使河水一时变得滞重。这一次争斗后来当然是被平息了,事实上两个村里的人也早就和好如初,然而那流淌在河里的血总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
无论如何,河是同一条河,田野永远是整个的一片田野,所有居住在同一条河边的村人,总是同河与田野相伴共生息息相依。其实,河归根结底还是会给村人带来许多的欢乐,在炎热的夏季,村人在河边劳作,河风会给他们带来凉爽,使他们多少减轻一些劳作的疲累;在河边,他们还能听到水鸟欢快的鸣叫,常常不经意地产生一些劳作之外的联想,这些联想多是美妙的。他们有时还会趁着汛期带着一张网下河去,捕几尾鲜活的鱼做一顿美味的餐肴。河自然又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几乎每个村里的孩子都在河里学会了游水。村里的女人早上总会来河边洗衣,在清清的河水中,她们陶醉地展开红红绿绿的一面面生活的旗帜,清朗的说笑声在河水中荡漾。下田的男人听了洗衣女人震天的杵响,干起活来于是一身神劲。而在“双抢”过后,农事一时小闲,村庄里恋爱的年轻人就会急着往对方家跑了,偷偷闲和对方亲近,夜晚双方相送回家时,经过河堤,此时河流生风,凉爽得很,夜色很美也很安谧,河坎或河滩上总有人家晒着稻草,一切都很美,一切都很方便,于是一对人这么送了几次,女的往往就怀了孕,很显然,在村庄又将诞生一个村里人的后代。
而真正让村里人感到生活在河边最快意的时候,无疑还是秋天收获的季节,此时村庄前的道路敞开,道路无所不在,秋天成群结队的稻子欢快地回家了。回家,是稻子永恒的归宿,就像河流和村庄,永恒地相依为命。稻子背负着使命,走过了一生的路,曾经的阳光和雨水,稻子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稻子本身就是对村里人的一种诠释。
对于村落,对于河,我们还应当说些什么呢?一位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于村里人来说,河或许是会永远流淌的,而他们则是在一边重温着传说的同时,一边又在创造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他们是否想到,他们所创造的那些故事,在流传给他们的后辈时,又会成为一种怎样的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