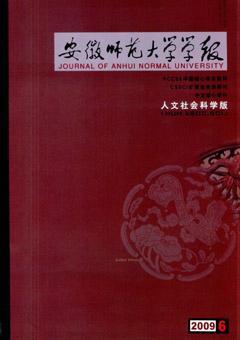中国当代西部诗歌的终极关怀
张玉玲
关键词: 中国当代西部诗歌;终极关怀; 命运; 时间
摘 要: 西部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独立品格也在悄悄形成。其中终极关怀源于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终极关切,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西部诗歌表达了对灵魂的叩问,对时间的关注与对人生的思考。西部诗歌所具有的终极关怀使西部诗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增强了西部诗歌的焦灼感。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65406
Ultimate Concern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etry
ZHANG YuLing (School of Chinese, Zhejiang Uniw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etry; ultimate concern; fate; time
Abstract:
The western poetry has offered a kind of artistic spirit and its independent character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 ultimate concern was a kind of deep concern for life and a kind of metaphysic thought to universe and life . The western poetry expresses the inquiries to soul, the attention to time and the thought of life. The ultimate concern fillls the poetry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ardship,tragedy and anxiety.
“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兼有沧桑、严酷、贫瘠、荒芜、苍凉等多种内涵的情感代名词。有一种不成文的观念甚至认为:每个西部人的生存史都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这里的“题材”实际上暗藏着一个认同性的语境:即磨难、奇异、与众不同。这一特质也就决定了中国当代西部诗歌的与众不同,它的独特当然与这一严酷的地理环境、历史成因有关,而西部诗歌当然不可能无视“西部”这一重要背景的影响。因此,西部诗歌往往带有更多的苦难感、历史沧桑感,与此相对的还有戍边卫国及与苦难相抗衡的英雄主义情怀。但西部诗歌并不仅仅是表现为这样几种精神特质,它有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西部诗歌在对人生和生命进行观照时,走向了生命的更深处——向人生的终极逼近。这就是西部诗歌中对终极关怀的追问。他们反对的就是只以经验的功利的眼光去看世界,因此,他们要把自然和世界精神化、深化,其目的是要为世界找出一个意义,找出灵性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去利用世界。由此,西部诗歌在观照人生和生命时,不自觉地将笔触探向了灵魂、命运、时间、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等终极对象。回溯本源,这个终极关怀的愿望导致了西部诗歌具有这样重大的意识变化:首先,由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关注、赞誉和批判进而发展为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注;其次,由对群体历史和文化表象的美学透视转向了对人性奥秘与生命苦难的探寻和表达;再次,由对生存过程的反思与观照转向了对于生存内涵、生存本质、其价值与意义的探求;最后,由对情感意识领域的倾向性表达转向了对普遍人性经验的终极性表达。同时,这些对终极的关怀和疑问带来了西部诗歌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色彩和救赎意识,使西部诗歌的文化意识空前复杂也更加痛苦,在平静、淡泊和空灵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更加强烈的失衡、焦灼和沉重。这也使得西部诗歌具有极大的张力,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对终极的关怀和疑问增加了西部诗歌的厚度和深度。下面,我们就选取西部诗歌对灵魂、时间、痛苦的追问这样几个角度来探视西部诗歌的终极关怀。
一
首先,西部诗歌回荡着灵魂的呼喊,表达了诗人对终极的关怀。人邻在诗歌中这样写道:
它们/让我难过。/哪怕是一只小小飞虫,/只要会飞,翅膀闪亮,嗡嗡作响;/是空气,哪怕看不见。
命给了它的,命又拿了去。/灼热的沙砾上/它转弯的时候,那一刻/巨石般黑暗。
——鸵鸟
这是对命运的思考,诗中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鸵鸟对命运茫然无知,而“我”对命运则困惑不解。它们之所以让我难过,是因为它们毫无例外地在命运的掌控之中毫无自知,无论多么小,即使小到空气一样,仍然挣脱不了命运之手。尤其是“命给了它的,命又拿了去”和“巨石般黑暗”之间造成一种奇异的美学效果,它们在我们心中投下的疑问和阴影既令我们痛苦也令我们迷恋,这首诗直逼我们的灵魂,我们如何来面对命运之手?诗歌没有做出回答,但它所营造的诗意氛围足可以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命运深处。
昌耀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原是孤独的人类用以倾诉内心情绪、宽慰或内省的方式。艺术是灵魂的歌吟。而灵魂的歌吟恰是广义的诗的精髓。”[1]392这话是不错的。因为“个人生存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不断返回不断追问的话题。在真实的生存境遇中思考和表达的作家,一旦触及了人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困境,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会在生死、意义、爱、虚无等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滞住。对于现实人生来讲,这是每一个清醒的人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绕开的生存处境。但是,对于写作者和思考者来说,这又是最困顿、最棘手、最无法越过同时又最容易回避和绕开的问题。这是人生的难题,同时又是时代的困境,如果作家的写作是在这些问题的层面上展开和推进的,那么,文学的内在精神就从个人关怀走向了终极关怀。”[2]诗人昌耀正是在对个人生存的真实性的不断追问中,体验到艺术是灵魂的歌吟的。 “诗,终归不是诗人可随心所欲拈来的装饰品、桂冠或筑巢的羽毛,直到今天我仍然信仰诗是生命化育‘血必浓于水,而诗人是痛苦的象征。这样的诗人必具有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与生俱来的生之悲悯。这样的诗人正是人类自己在不经意中造就的一束极具痛感的神经纤维。诗人,即更具痛感的人,直面生活,索解命运,勿为形役,人类史上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哲人、社会活动家都不乏这种诗人的气质。”[1]434昌耀在生命的大摧折中体认到诗人与痛苦具有不可分隔的关系,诗人是直面生活、索解命运的人。
“人世是困蝇面对囚镜,/总是无望的夺路,总有无底的谜。” “一切是在同一时辰被同一双手播种。/一切是在同一古藤由同一盘根结实。”(昌耀:《箫》)“我的箴言在恓惶的夜阴差阳错,/不幸是施术的咒语。”(昌耀:《恓惶》)当诗人无奈地感慨到这些时,他已经越出生活的表层,将笔触逼近命运的深层,诗人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
诗人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终极始终是人类感受的极限,然而又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人生,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3]而终极实体是无限的、完美的和不可把握的力量,同时又是最内在的、人格化的;它的不可思议的可能性,构成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秘性,同时这个神圣的存在又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所以,当诗人略去生活的表面浮尘后,关于人类的命运等终极问题就会自然凸显出来。
毫无疑问,对终极的关怀就不应该无视生命的沉重和命运的荒诞。昌耀就曾这样说过;“无可动情于生命的沉重,无可困惑奋发于人类的命运,我不以为他会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作家。”[1]401海子认为,诗人应当“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而不是局限在忧患现实或者喟叹身世际遇的层面上作诗。”(《诗学:一份提纲》)[4]昌耀信仰着作家应该动情于生命的沉重,海子认为,诗人应该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人,他们都从诗歌艺术观的高度上确保了自己的诗歌能够接近终极关怀这一层面。
二
谈到生命我们就无法忽略“时间”。时间组成了生命。时间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对此都会感到困惑不解。因而,人们总是从他们各自不同的思考、认识对象来领会时间。从亚里斯多德到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时间,是根据事物的运动过程去领会时间;奥古斯丁是从维护上帝的存在的角度去思考时间;而海德格尔则是从此在的存在而提出的新的时间观。时间,是认识生命本质的关键所在,也是历来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那么,西部诗歌对时间的追问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说在不同的诗人中,对时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对于人邻来说,时间是“非薄,无法捏住。/时间,只听见自身最娇嫩的那一刻。/暗伤无法确定。/无法描述。/感知的人啊!只能/屏住呼吸,寂静。”
(人邻:《时间》)人邻笔下的时间是充满诗意的时间,虽然无法捏住,但可以感知。人邻的时间在诗人的心里,它体现在“自身最娇嫩的那一刻。”还有,“只能/屏住呼吸,寂静。”这就确保了人邻的时间是无声的,或者说是静的、轻的。人邻喜欢这样的时间,也便赋予时间这样的特点。人邻曾这样写道:“那人给我沏茶的一瞬,/河水忽然加速。/我看见它们蜂拥/盲目而过时。//茶在漫溢;/整条河流都过去了。/整条河流阴郁、颓废/匆忙间消亡了自己。”(人邻:《河边一瞬》)诗人将“那一刻”写得丰满而有趣,我们也在体味“那一刻”中感受到生命的无限美好。
与我们对时间的常规理解相反,人邻笔下的时间是缓慢的,因唯其缓慢才能从容,才能富有诗意。请看这首诗:
荒芜的房间/我在阳台,见到这棵橡皮树/还有些叶子挂在上头。/它们挨得很紧,/从一,我数到第十七片/
第一片叶子和第十七片一样沉。
从一,我数到第十七片。/它们有另一件事情,这个冬天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把它们从一,惊喜地数到十七/不多也不少。/我也有一件事情,就是数到我的房间荒芜。
我数了很久,我是为了完整,避免数得太快/避免它们哀伤落尽。/但我怎么可能比时光更慢、更慢。
—— 十七片叶子的橡皮树
诗人渴望一种悠闲、诗意的生活,一种可以完全占有或者说拥有自己时间的生活,于是诗人感叹道:“但我怎么可能比时光更慢、更慢。”
而沈苇对时间的认识几乎与人邻相反。在沈苇那儿,时间是匆匆的。诗人这样唱道:“就在昨天,一百个处女还在瓦房上曼舞歌唱/一夜之间都糊里糊涂做了新娘/她们凝视远方,世界便在身后出现/给她们突然一击,——这一切总来不及思考/那远逝的春秋啊,如花丛中升起的云朵/飘向蓝天,使翘首者泪流满面/我正走向我诞生的木楼/——我是否还在里面?/在一岁的早晨,或者十岁的黄昏?”(《故土》)时间是如此的匆促,“一夜之间,一切总来不及”这是沈苇笔下的时间,与人邻的能不能比时间更慢的疑问正好相反,为什么我总是来不及,也就是为什么我总不够快?在另一首诗歌中,诗人干脆说:“我天生就是一个被追捕的人:被影子追捕/被影子的影子追捕,被影子的影子的影子追捕/一个被追捕的人,一个被轰出书斋的人/……/一个被追捕的人/像吃下砒霜的鸟儿努力飞了最后一程。”(《状态》)时间是如此匆匆,我被追捕,像吃下砒霜的鸟儿。真是无比痛苦。诗人为什么如此痛苦,时间对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时间意味着消失。诗人说:“想象,多余的想象,从未抓住/交臂而过的景物”(《状态》)时间意味着重复。诗人写道:“我在镜子里看见春天,以及春天之前的春天/那遥远的传统之父和虚幻之母/一切仅仅是摹仿,一切仅仅是重现。”(《春天》)时间意味着不可抗拒的力量。诗人悲哀地看到:“他的方向早被指点/他的道路早已限定/他的爱情只得到日月星辰的支持/作为家族的长子和嗣子,他必须回到/现实的操劳:学艺、仕途、买卖、婚丧/用一根丝线串连过去和未来/像腌鱼,以垂死的姿态晾晒在屋檐下/使基石进一步坚固,富有秩序”。(《中国屏风》)时间是如此的匆忙,人生又是被限制、被安排,那么,我们当何为?如何超越时间?沈苇告诉我们,向死而生。诗人在《吐峪沟》中为我们描绘的场景是颇耐人寻味的:
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
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
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
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
村民们在葡萄中采摘、忙碌/
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
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
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这是这首诗歌对我们的智慧点拨。诗人在另一篇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四季的流水帐。死者的奢华超过了/生者的盛宴,那是往日歌谣、古老的安魂曲,/是流逝的一切安排了未来。向死而生啊,/向着死亡的还乡,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到达。”(《新柔巴依》)那么,“向死而生”对于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有两种样式:一是“非真正的存在”。“非真正的存在”就是“沉沦”,就是失去个人的独立性。就是被剥夺了个人充分展开自身诸种可能性(自由)的存在。二是“真正的存在”。人的“真正的存在”,就是人超越世俗的限制,摆脱“他人”的羁绊,按照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的、已经内在于本身的可能性去追求。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真正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因此,人若能真正地“向死而在”,就能从“非真正的存在”中提升出来,达于“真正的存在”,达于“自由”。
三
关于时间问题,走得最远的应该是昌耀了。昌耀的时间意识是变化的。诗人对“时间”的态度有三个阶段:即由最初对于时间的敬畏、感激到对于时间的焦虑,最后是对于时间的不信任,认为时间是荒诞的,从而消解时间,消解必然性,并以选择死亡这一绝然的作为作为对于时间的超越。
先说诗人对于时间表现出的敬畏阶段。写于1980年的长诗《慈航》中反复吟咏:“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这可以看作是对时间的敬畏,对善与恶角力中孰赢孰输的坚信,以至诗人坚信“该出生的一定要出生!/该速朽的定得速朽!”诗作充分展现了诗人对于时间的态度:在时间面前一切都会得到验证。写于1980年的长诗《山旅》的副题是“对于山河、历史和人民的印象”,从副题中我们基本上可看出诗人写作的主要用意。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再一次表达了对于时间的信任:“时间的永恒序列/不会是运动的机械延续,/不会是生命的无谓耗燃,/而是世代转承的朝向美善的远征。”时间成为正义的象征,诗人对时间是敬畏的。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从1985年开始诗风有了巨大的转变。由80年代早期的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变为对荒诞人生的抒写,并且诗人在1985年之后时间意识也有了陡然的变化——由过去的敬畏,变为内心的焦虑。先让我们来读一首诗歌《晚钟》:
行者的肉体已在内省中干枯颓败耗燃。
还是不曾顿悟。
啊,在那金色的晚钟鸣响着的苦寒的秋霜,
是如何地令迟暮者惊觉呀。
那惊觉坠落如西天一团火球。
这首诗歌写于1985年11月18日,诗歌意境苍凉悲壮,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焦虑。
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焦虑感进一步演变为荒诞感。诗人开始对时间进行解构。当我们知道了诗人曾经如此的敬畏时间时,我们就会同时想到解构时间对于诗人来说并不是像第三代诗人消解英雄,消解崇高,消解历史那样的一种解构,昌耀在解构时间时已融合了无奈、苍凉和悲愤的生命体验。至此,我们说,诗人在对时间的追问中已不自觉地靠近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时间观。昌耀说:“然而‘存在永远是一个有待稽查的课题。这犹如梦与醒,当我‘醒着,我才明白此前梦里貌似正常的一切原来破绽百出且荒唐之极,故证之为梦。那么,谁又能保证我此刻感受的‘确而无疑不成其为又一场梦醒后的又一场虚假?‘存在何以自解?惟释以‘人生如梦无懈可击。故‘醒着状态之追求始终是人生聊可自慰的大事。其实‘醒着只是直面枪口,徒有几分行色的悲壮,并不能改变潜在的厄运。”[1]655表达的是一种深重的生存危机感。无论是醒还是睡,都是不真实的,虚幻的,虚假的。而厄运则是无法改变的,醒着就是直面枪口。在另一篇文章中诗人甚至对时间本身也提出了质疑:“时间何异?机会何异?过客何异?客店何异?沉沦与得救又何异?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忽忽然而已。但是,真实的泪水还停留在我的嘴角。”[1]659时间对于诗人已不再具有威力,也不再是创造,对于诗人来说,人生不过是从一扇门进到另一扇门,从生的门到死的门,忽忽然而已。与其说诗人这时谈论的是时间问题,不如说诗人谈论的是死亡问题。这泪水既有对流逝时间的痛惜,也有对当前时间的无从把握,因为晚期肺癌的病痛折磨几乎取消了诗人享受未来的权利。诗人在浓缩人生经历时,时间的概念就变成了从生到死。在这里,时间是时间性的到时,意味着时间不再是流动着的线性形式(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一接续),而是“将来”、“过去”、“当前”三种时间样式的共同到时,是一个三维交互伸达的整体。三维的交互伸达为存在开辟出一片疏明之地,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伸达,来临(将来)和曾在状态交互供呈而二者的交互牵涉则呈公开场的疏明”。[5]时间也不再是独立关注的有强大意志的存在者,而是展现存在的一条“地平线”,是打开人们视域的一条虚拟的线条。诗人在写于1989年的《哈拉库图》中感慨道:“时间啊,令人困惑的魔道,/我觉得儿时的一天漫长如绵绵几个世纪。/我觉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尽快意的聚饮。/我仿佛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我每攀登一级山梯都要重历一次失落。”“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诗人在面对时间时,感到无比的苦闷。首先时间是如此匆促,“我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然而,时间并不昭示未来,“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这真是令人绝望的时间。在诗人看来:“世界到处都是既定的血与既定的杀机。承认或习惯于这一事实也许可以减轻内心煎熬的痛苦。这就是说,我们默认双料的自我既是潜在的罪人也是潜在的牺牲。不胜唏嘘。”[1]704活着就是承受内心的巨大痛苦。“世界到处都是既定的血与既定的杀机。”诗人将死亡与时间并列起来。时间已不昭示希望和未来,我们是罪人也是牺牲。
四
昌耀最后在与死亡不断的照面中,选择了死亡不是偶然的。对于诗人昌耀来说,“死去活来是如此艰辛的一份义务。”诗人认为死亡是“对生的净化,是解毒剂,是最后的安慰。”所以,我们说,诗人其实是把死亡当作生命的最终归宿来看的。在面对肺癌晚期病痛的折磨,面对无路可走的人生境地,面对致命的苦闷,诗人在叩问时间,叩问信仰,叩问生的意义、死亡的意义后选择了自动死亡。
潘知常在《王国维的美学末路》中指出: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山祖师,王国维的最大贡献,是将生命还原为个体,因此,个体唯余“痛苦”,个体就是“痛苦”。结果,与传统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美学形成“反讽”,一种全新的充满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诞生了。遗憾的是,王国维为这一全新的发现而手足无措:既然成也痛苦,败也痛苦,“解脱之事,终无可能”,王国维找不到一个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理由,投水自尽是他的必然结局。百年之后再来评价王国维的选择,应该并非一件难事。他没有意识到痛苦就是人生,因此竟然拼命地去寻找痛苦之源,遍寻不着,其结果是整个地让出了生命。面对几乎可以说的突兀的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王国维的思考明显缺乏一种起码的内在力量,精神皈依。尽管同样是在思考生存的根本问题,但王国维与叔本华等西方大哲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依托的是经验,后者依托的是信仰。为什么叔本华可以终生坚信其哲学而王国维则不能,并且要弄到自杀的地步呢?差别在于叔本华是“生命”(本体)的,而王国维是“生活”(经验)的。一旦从“可信”入手去要求“可爱”,就会陷入中国传统的封闭的精神怪圈:只依赖经验来生活,背后没有信仰作为依托。以谈论经验的方式谈论信仰,难免就事论事,就痛苦说痛苦,因此也就永远无法达到“可爱”。在我看来,王国维所代表的,是一个信仰维度阙如的国家试图在学术上超越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失败,这是一个民族的最为深刻的内伤。[6]这段评论虽然说的是王国维,在某些地方对于昌耀来说也是合适的。首先,昌耀发现人生就是痛苦,无论成败,事实是,诗人认为,人生是败局已定的。从上文论述中也大体可以看出诗人这一观点,我要谈论的重点是昌耀像王国维一样让出了全部的生命,也像王国维一样是因为“明显缺乏一种起码的内在力量,精神皈依。”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诗人曾经有过信仰,先是革命英雄主义,后是信奉爱的力量,并认为诗歌本身就是自己的信仰。然而,随着一个个的所谓信仰的失落,诗人最终走向了虚无论、悲观论,并选择了死亡之路。正像王国维是凭经验活着,昌耀也是这样,而昌耀人生的经验就是痛苦,是痛苦的煎熬。所以,昌耀最终认为死亡才是解毒剂。潘知常认为,王国维所代表的,是一个信仰维度阙如的国家试图在学术上超越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失败,这是一个民族的最为深刻的内伤。这一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昌耀其实已经站在寻找信仰的路口,他说:“我崇尚现实精神,我让理性的光芒照彻我角膜,但我在经验世界中并不一概排拒彼岸世界的超验感知。”[1]523他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人们是蜜蜂。如果说人们仅只是蜜蜂。/人们为什么又仅只是蜜蜂。”
(《一幢公寓楼》)然而,没有答案。对于沈苇的“永恒就是过程”的信奉已经不能满足昌耀的需求。因为过程本身是如此痛苦,难道永恒就是痛苦吗?对于人邻的“一瞬即永恒,永恒在审美的瞬间”也不能解答昌耀的疑问。因为审美也无法解决昌耀内心的焦虑和苦闷。所以,昌耀只有自己硬挺着了,他也才会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背后就是易水。/我们虔敬。我们追求。我们素餐。/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堂•吉诃德军团还在前进》)才会悲哀地感叹:“人啊,正是如此领有信徒的虔敬,/又复领有征服者的悲凉。/明智的妥协与光荣的撤退都无济于事。/人,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我今夜依然还是一只逃亡的鸟。”(《人:千篇一律》)这是怎样的恓惶与悲凉啊!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昌耀的悲哀是我们国人的悲哀,是一个信仰维度阙如的国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