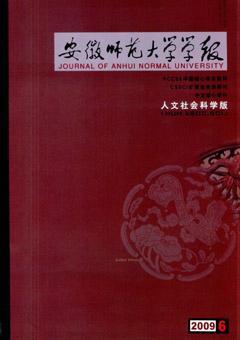“悲剧的解放”
章 池
关键词: 悲剧;政治;革命
摘 要: 新中国初期和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艺界先后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
社会悲剧的两次论争,虽间隔较久,精神却一脉相承,都是为厘清社会主义制度与悲剧的关系。这固然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不成熟相关,但亦是彼一阶段中国文学隶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必然结果。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64905
Emancipation of Tragedy-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from Two Discussions on Tragedy
ZHANG C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tragedy; politics; revolution
Abstract: At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here emerged two discussions on socialist tragedy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ircle, which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tragedy. I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mmaturity of Chinese modern tragedy.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for Chinese literature is subordinate to politics and servespolitics.
1948年5月,郭沫若为《白毛女》的演出撰文,认为《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因为这个封建社会里的典型悲剧,其结局由悲转喜,并不同于旧式的孟丽君女扮男装的中状元名扬天下,后者只是“得到一个虚构的满足”,而前者则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遭了扬弃”,所以封建主义所产生的典型悲剧也就遭了扬弃。[1]郭沫若的这一论断
代表着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普遍认识:将悲剧的有无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先进落后、清明与否紧密相连,将悲剧艺术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等同为直接的反映关系。这样的绑缚与类比,使悲剧一踏入新中国,就被自以为已抵达至善、至美之社会的人们欢欣鼓舞地“解放了”。
新中国的人们“解放了”悲剧,但是刚起步的新社会新生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新的痛苦、新的问题取代旧的记忆一样渗透在日常的生活中。现实与想象的差距、悲剧性事件的存在,使人们开始困惑,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悲剧、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有悲剧这样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关于悲剧的两次论争。
一
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悲剧的第一次讨论始于1957年老舍的一篇文章。
1957年3月18日,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不久,老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悲剧》一文。虽然彭鼎很快便撰文
同他商榷,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讨论戛然而止。1961年,在经过一系列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这场由老舍引发的讨论才真正开始。
老舍的《论悲剧》基本上是由一系列设问式表述构成,但其中最核心的发问则是:“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2]79这是当时的老舍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个现实,也是最令他困惑的。
但是,后来人们却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反倒是抓住他那些自问自答式表述中的问题重新做着自己的答案和解释,并最终构成了这次讨论的四个主要问题:一、什么是悲剧?二、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悲剧?三、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产生悲剧?四、社会主义时代悲剧有何特征?四个问题中,最核心的是第二个,“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悲剧?”虽然“什么是悲剧”具有前提性的理论意义,但由于大家普遍性地持有郭沫若式的社会悲剧观,将悲剧看成是灾难和不幸的代名词,所以给出的说法大同小异,无可多论。三四两个问题实则是第二个问题的延伸与强调。
对“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悲剧?”的回答,无非肯定、否定两种意见。
否定论者以细言为代表,1961年他发表《关于悲剧》,坚定地否定了老舍的看法,认为:“在我们这个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已经成为命运的主宰,美的总是战胜丑的,正义总是战胜邪恶”,不再有悲剧。他最后的结论是:“社会生活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格式自然也会发生变革。不能因为悲剧这个格式是‘古已有之的,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如果产生悲剧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或正在消灭,悲剧恐怕也不能够脱离社会生活而永生。在这个唱赞歌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歌颂的事物是太多了;即使也有应该揭露、批评的现象,也不能把它当作悲剧来处理。悲剧这种格式,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园地里,应该是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的东西。”[3]在他看来,老舍的倡导悲剧显然已不合时宜。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中的悲剧并不像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绝迹,全盘的否定已然难以令人信服。与细言的否定论相比较,肯定论者明显占多数,他们基本上都能够从现实出发,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悲剧。不过,其承认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
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根源上,都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悲剧,另一方面更要证明这悲剧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如何梳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他们论证的着力点所在。不约而同地,他们都选择了在悲剧的性质和特征上做文章的方法。如蒋守谦所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同传统的旧悲剧有“质的差别”:“新悲剧主人公的流血牺牲是为新的理想所鼓舞和支配,他们牺牲的代价,是换来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或者是作家在描写这个悲剧人物的时候,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肯定和歌颂新的理想、新的社会制度;而旧悲剧主人公的死亡,其意义往往仅是对旧社会的抗议与否定。”[4]至于它的性质,则是乐观主义的,而且“悲剧的形成只能是局部的”,“悲剧冲突也只能是暂时的”。[5]顾仲彝对此还作了明确解释: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之所以都是“乐观的、鼓舞的”,是因为“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沮丧,不是害怕,而是鼓舞,而是激励,使我们更憎恨敌人,更爱社会主义”。[6]
肯定论者给出的答案似乎与否定论者颇有差别,但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区别只是表面的肯定、否定而已,在本质性前提上他们同否定论者是一样的,最终性目标也相同,即从根源上将悲剧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剥离掉,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和神圣性。也正是因此,他们才会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悲剧“不再是戏剧的主要的样式,而是次要的了。正剧和喜剧,……将取过去悲剧的地位而代之。”[6]
在《论悲剧》中,老舍曾痛心而忧虑地说,悲剧是“用不着我来提倡”的,只是“我却因看不见它而有些不安”。因为“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难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2]7980更让老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发现今天的社会一样有悲剧性现实,也一样有喜欢上戏园的观众,他们依然会为古代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悲情故事掉眼泪,而且,现代悲剧《雷雨》也依然很叫座。但为什么就再没有出现新的悲剧作品呢?[2]7879他困惑而无奈:“我们反对过无冲突论。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去写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悲剧。是不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不够彻底,因而在创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呢?假若这是真情,那么,谁叫我们采取了那个态度呢?我弄不清楚。”[2]80是啊,是什么让人们人为地回避了悲剧,不谈不写呢?几年过去了,他的回应者,无论是早期的彭鼎,还是后来的细言他们,都避重就轻地偷换了话题,所谓的讨论,不过是在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做着这样那样的辩驳,对悲剧,则依然是冷淡有加。
回顾这次讨论,与其说它是对悲剧的理论探讨,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申与强调,“解放了”的悲剧,仍然在放逐中。
二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次讨论,人们是在竭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寻求某种制度外的原因,努力消弭社会主义社会悲剧的存在和悲剧的价值;那么“文革”后这场因为沉重的痛苦记忆和压抑不住的苦难叙述而被推上前台的悲剧讨论则坦然了很多,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而是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讨论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85年才告沉寂。据《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7]和《新中国40年文艺理论研究资料目录大全》[8],直接讨论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79-1981年,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作为一个已然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制度的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悲剧?紧承着这个问题的,就是如何去写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它们的相连,就像当年的学者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悲剧后,马上全力分析这悲剧的产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实质上都是出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以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这次讨论的核心,而所谓的悲剧定义,则是为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作铺垫。
1978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向彤的《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一文。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分析了三方面原因:其一,“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其二,“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斗争中,也可能发生悲剧”,“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常常互相交叉”;其三,“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以及一切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也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也是造成悲剧的因素之一。”[9]从向彤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并未能脱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思维,而且坚定地将它贯彻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中。同“文革”前的讨论者一样,向彤坚信,作为光明理想社会的象征,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不可能产生悲剧。因此,他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特点和创作:“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与旧时代的悲剧有本质的不同:旧时代的悲剧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造成的。”所以,“我们时代的革命作家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悲剧”,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敌人,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9]本着这样的前见和思维惯性,注定了向彤对悲剧问题的阐述不可能超出“文革”前的水平。
不独是向彤,接下来的理论文章基本上都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如,刘季星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是现代阶级斗争生活的暴风雨造成的结果,是“阶级敌人打入党内长期不能予以清除,居然让他们以阴谋手段窃取高位而不能及时制止,居然无力保护我们的杰出的领导人和优秀的同志而听任他们摧残”,造成的不可弥补的重大过失。说社会主义有悲剧,“未免亵渎我们的先烈和我们都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理想”。[10]言下之意,悲剧是阶级敌人造成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决不可能产生悲剧。这种认识和观点,在细言的带有反省意味的文章中表达得更清楚。1978年12月12日,细言(王西彦)在《文汇报》上发表
《悲剧的成因》。他首先推翻并检讨了自己当初的结论,“‘四人帮的产生和横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悲剧,而且是极大的悲剧”,“面对这种现实,我那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悲剧是‘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的东西的论断,就显得十分错误、十分可笑了。”简言之,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有悲剧,罪魁祸首就是“四人帮”。这论调正是当时的主流。在林彪、“四人帮”成为众矢之的之时,一直在苦苦寻找社会主义社会悲剧根源的人们也“茅塞顿开”,而且蛮欣慰,因为终于发现了
源头所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不再令人痛苦、恐惧。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与悲剧无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性将得以重塑。
从首发的向彤到自我反省的细言再到走向深入的刘季星,虽然他们的观点有差异,
但只是具体的分析有所不同,整体上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敌人、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做悲剧文章,
与“文革”前的讨论相比,对悲剧的认识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悲剧的价值也依然只在于为现实鼓与呼。所有的不同仅在于,悲剧不再被讳莫如深,它获得了初步的解放,被诚恳地请出了冷宫,并予以了相当热烈的欢迎。但繁荣热烈只是表面的,喧嚣过后,悲剧研究收获的依然是一片荒凉落寞。
三
1980年代中后期,在总结这两次讨论时有观点认为,它们,尤其是新时期的这次,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或者悲剧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使社会主义悲剧这一概念真正确立了起来。[11]
今天再读到这样的评价、再看这所谓的“贡献”,相信认同者了了。事实也是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政治与艺术硬性联姻的概念早已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名词,无奈地见证着自己和一个时代的记忆,很悲情,也很耐人寻味。
有关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两次论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主义悲剧概念的发生、成长史。
它以其悲情发展史,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从革命年代到和平年代的微妙演化作了一次完整的另类演绎。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是个老话题,学界也多有论述,笔者比较认同这类观点:在正常存在的态势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同样以一种相互想象的关系而存在。它们彼此在对对方的想象中实现自己的存在。文学因想象政治而参与了政治,政治因想象生活而借用了文学。文学与政治的这种互缘的想象关系在革命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关于革命,英国政治学家彼得•卡尔佛特认为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指一个过程:一些重要集团不再留恋既有政权,并转向反对这一政权的过程。其次,它指一个事件,一个政府被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而推翻的事件。再次,它指一个计划,新成立的政府试图改变它所要负责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一个但并非最终一个方面,它指一个政治神话,讨论得更多的应该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12]革命的这最后一方面同文学一样,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描画,也正是缘于此,它与文学达成了一致。但这种一致又因政治家与文学家想象的不同而显得非常脆弱。政治家不同于文学家,他不是纯粹的想象者,他同时还是实践者,他要将想象贯彻到实践中。在政治家的具体践行过程中,先前的想象必定会因为现实的限制而萎缩、褪色甚至变形。当“应该是什么”变成“实际上是什么”时,政治与文学的想象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地形成,并最终带来二者的分离。
文学与革命之间这种始合终离的关系注定了它与现实政治之间关系的微妙。如果说在革命阶段,文学与政治因想象的联结而形成一种共进退的亲密关系,那么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文学与政治之间便主要是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但这是正常健康状态下的理想情景。现实中,它们却常常是矛盾、冲突的,原因很简单,文学所想象的政治,始终来自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带有人类理想政治的特点,这使文学的政治想象具有极大的自由,它“可以在理想的境界中来表现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13]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必然使文学会对现实的政治进行监督、批判甚至否定,虽然它本意是为了政治的更好建设,但现实政治如何来理性地认识、面对文学的这种超越性的否定和理想化的要求则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就社会主义悲剧概念的发生发展历程来看,当时中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强势话语,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是被规定了的,文学必须表现政治,而且只能表现符合现实政治意图的政治,为它宣传歌唱。这时候的文学已不能自主,要么沉沦于枯寂,要么开口唱赞歌,以想象中的“应该是什么”粉饰、歌颂现实中的“实际上是什么”。把握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学者们为什么要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进行辩解,为什么一定要将悲剧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剥离。悲剧的毁灭叙述、悲剧的忧伤恐惧、悲剧的否定批判等等,根本不合当时现实政治的需求。不仅如此,悲剧甚至还令它心有余悸,因为其所独具的紧张的矛盾冲突和它所张扬的执着的自由反抗精神。
同所有的文学样式一样,悲剧也以“想象一种美好生活”为目标,但作为“一种经营人类的绝望和悲伤的艺术形式”[14],悲剧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另出蹊径的,它是通过否定来进行肯定的批判性艺术。在绝望悲伤的交织中,在矛盾冲突的撞击中,悲剧以主人公执着不悔的挑战勇气和自由不屈的反抗精神歌颂着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不久前的革命年代,悲剧正是借此而颇受青睐,郭沫若社会-历史悲剧的成功与巨大影响力至今还让人们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这是悲剧的特色,也是悲剧的魅力,但对于刚刚夺取政权正处于转换建设中的新政治而言,尤其是当它还在延续着战争年代的思维时,悲剧的存在便不仅仅是善意的监督,更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对于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陈思和曾从战争文化心理角度作过精辟的解读。他将“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40年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认为这是“战争因素深深地铆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意识也相应地留下了种种战争遗迹”。[15]也即,战争文化心理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这分析可谓深中肯綮。联系悲剧来看,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第一次讨论从否定的粉饰到肯定的辩解,从拒绝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悲剧到努力地寻求制度外的根源,表面看好像是学者们在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维护,但实际上这些讨论者已成为强势的新政治的理论代言人,于是,他们整齐划一的强调与重申所体现的不过是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对巩固、稳定和统一的需要。否定与批判是不被容许的,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一个群体的理想、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亵渎”,更意味着质疑和挑战。否定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否定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实新时期的讨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而且还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自觉延续,尽管它发生在一个解放思想、全面反思的时代。长久浸淫于阶级斗争、政治批判的生活中,人们的政治化思维几成惯性,再加上参与者自身对新社会的由衷“爱护”,短时间内他们根本难以抽出身来作冷静、客观的反思、批判,不能自拔的陷入与挚爱,使他们重塑社会主义完美形象的努力与坚持格外动人,惟其如此,他们自说自话的无奈结局也就格外令人伤感。
进入1981年后,随着悲剧论争的寥落、马克思主义悲剧观讨论的深入、西方各种悲剧艺术和理论的引入,困扰了中国人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思维和政治话语魔幛终于从悲剧的舞台上慢慢退出。备受抑压的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开始了它的全面发展期,并最终迎来了它的真正解放——不是来自于人们善意的放逐,而是来自于自由、宽松、包容的政治环境中悲剧观念的开放、多元。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M]∥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768.
[2] 老舍.论悲剧[M]∥老舍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3] 细言.关于悲剧[N].文汇报,19610131.
[4] 蒋守谦.也谈悲剧[N].文汇报,19610415.
[5] 缪依杭.谈悲剧冲突及其时代特征[N].文汇报,19610503.
[6] 顾仲彝.漫谈悲剧问题(下)[N].光明日报,19610516.
[7] 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1976—1985)[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8]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中国40年文艺理论研究资料目录大全(1949—1989)[C].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
[9] 向彤.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从《伤痕》谈起[N].光明日报,19781103.
[10] 刘季星.悲剧随想[N].文汇报,19791128.
[11] 刘崇义.这里是罗陀斯——论社会主义悲剧[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28,41.
[12] 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M].张长东,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2.
[13] 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J].文艺争鸣,2007,(5):1617.
[14] 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杰,方宸,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
[15]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9899.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