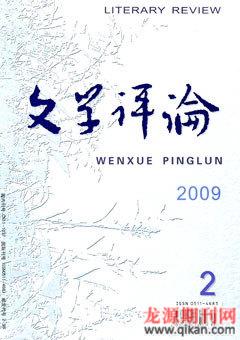论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
徐群晖
内容提要曹禺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希腊戏剧、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作家对曹禺的影响,而对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深层联系却缺乏关注和认识。本文通过翔实的研究资料表明,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存在着深层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通过“莎士比亚化”的途径实现的。在全球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研究和认识曹禺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莎士比亚作为人类戏剧史上杰出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任何一个时代。直到今天,他的作品凭借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仍然出现在世界舞台,成为全人类的艺术瑰宝,给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以丰厚的滋养。在中国,曹禺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优秀作品,也与莎士比亚作品一样,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呈现出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并成为中国与世界戏剧艺术的经典杰作。但是这两位世界戏剧大师的之间的联系,却很少被人提及。2006年,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和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两部国产大片分别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曹禺《雷雨》改编的。这也从一个角度暗示了曹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经典上所存在的某种关联。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更多地强调希腊戏剧、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作家对曹禺的影响,当人们在热烈地讨论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作家对曹禺的影响时,却忽视了莎士比亚与曹禺的深刻关联。人们往往把《雷雨》与易卜生联系在一起;把《日出》与契诃夫联系在一起;把《原野》与奥尼尔联系在一起,而对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深层联系却缺乏关注和认识。如钱理群先生在《大小舞台之间》中指出:“曹禺从希腊悲剧、易卜生(确切地说,应该是《娜拉》与《群鬼》、《国民公敌》时期的易卜生)走向奥尼尔,是必然的。——曹禺这一时期没有最终走向契诃夫,而走向奥尼尔,还有情感、气质上的原因:此刻曹禺郁热的性情显然是更接近奥尼尔的。而在《原野》的创造中,走向奥尼尔,……”事实上,曹禺的艺术成就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确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关联。《雷雨》、《日出》、《原野》等几部最重要的顶峰之作,都与莎士比亚戏剧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是曹禺在无意识的创作过程中实现的。正如曹禺自己所说:“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或拉辛的《费德尔》的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像不来白昼的明朗。这表明:曹禺受其他作家的影响时,始终处于一种非自觉的潜意识状态。这种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处于无意识状态,并通过作者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产生影响。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翰·加斯纳指出:“剧作的各种风格是彼此碰撞又相互沟通的”。这说明,曹禺的作品不是直接受哪一个戏剧家或哪一部戏剧作品的影响所产生的,而是通过一种系统接受和综合影响的过程实现的。当然,这种关联是复杂微妙的,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或者仅仅是审美风格的相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莎士比亚戏剧作为人类戏剧史上的顶峰,影响力遍及后来各个时代和不同民族,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作家和作品间接地对曹禺产生影响。因此,在全球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研究和认识曹禺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人类情感为核心的人性表现的深刻性在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深层关联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人性主题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为了响应以自由人性对抗封建神学的时代召唤,莎剧中的人性主题的地位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对人和自然的生命本能及其以真善美为内核的美好情感的肯定和歌颂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并且使生活的整个有机体继续不停地运动。”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朱生豪译:《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而莎士比亚戏剧对人性的歌颂和肯定使曹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中所说:“‘人是一件多少了不得的杰作……这段话写的不就是莎士比亚自己么?他不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么?”曹禺在《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中通过蘩漪、陈白露、仇虎、金子等形象高度捍卫和肯定了人性的神圣,对不人道的生存状态提出了义正辞严的控诉。他将人性自由完美的体验注入自己创作中,并升华为人类生命本原的体验。曹禺在《雷雨》序言谈到,他想通过人性的“挣扎”,表现宇宙压抑人性的悲悯、恐怖和残忍。从而通过激发人的生命冲动,创造一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在《日出》中,他要表现比蘩漪等人的“挣扎”状态更残忍的“被捉弄”的状态。对于陈白露所处的“被捉弄”的状态,曹禺作了精妙的注释:“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入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因此,曹禺的剧作可以说是他自己人性在作品中的映射和升华。在《原野》中,曹禺将审美视角转向比《雷雨》中的周公馆和《日出》中的高级饭店更广阔的宇宙中的人的生命冲动、人的生命激情、人的生命欲望等人的自然本性,以及人性的升华,向往和追求那天边外的“黄金铺地的”乌托邦境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性的肯定和赞扬还体现在其悲剧结构的理想主义美学风格。莎士比亚总是通过悲剧性结局的理想化升华,给予人性最高的肯定,从而让人性中的真、善、美彻底战胜假、恶、丑。这也表明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观念是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殉情而死,但两个家族的仇限和敌意因此而和解,两个青年的爱情终于胜利;在《哈姆莱特》中,虽然哈姆莱特中计身亡,但终于报了杀父之仇,正义得以张扬;在《奥瑟罗》中,虽然奥瑟罗因为听信了伊阿古的奸计,而错杀了美丽善良的妻子苔丝狄梦娜并自杀偿命。但结局最终水落石出,善人得到善报,恶人得到恶报。莎士比
亚这种乐观的人道主义对曹禺的人文观念影响很大。当曹禺在创作《雷雨》、《日出》和《原野》的时候,结局安排基本上是纯悲剧性的,往往给人以强烈的“怜悯和恐惧”。在《雷雨》中,四风与周冲触电身亡,周萍自杀,蘩漪和侍萍发疯。在《日出》中,陈白露吃安眠药自杀。在《原野》中,仇虎自杀身亡。而当曹禺创作《北京人》和《家》时,以前那种纯悲剧性结局的审美风格发生了变化。这种风格的转变与莎士比亚悲剧风格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曹禺正应邀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前言中谈到:“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四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哭泣起来。”曹禺的《北京人》和《家》的结局风格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响是明显的。曹禺说:“我觉得《北京人》是一出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因此,从曹禺戏剧结构的美学风格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乐观的人道主义对曹禺人文观念的深刻影响。
女性解放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莎士比亚戏剧洋溢着崇尚个性解放、关注人性张扬的时代激情,对女性的解放也给予了深厚的人文关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张扬的个性、优秀的品质、卓越的才能;她们热爱生活,大胆追求理想、爱情和自由,向往幸福自由的社会和生活;她们敢于对抗外界的虚伪、自私和残暴。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敢于违抗父命,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虽殒身而不恤。在《威尼斯商人》中,鲍细娅不畏强暴,用智慧战胜了残暴凶恶的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实现了美好爱情的理想。《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和《终成眷属》中的海伦娜也以智慧的心灵和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腐朽顽固的封建等级制度,最终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莎士比亚除了塑造众多正直、善良的女性形象外,还塑造了大量富有魅力却又极度追逐自我欲望的女性形象。如《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风流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女主人克蕾雪,《哈姆莱特》中的母后葛特露,她们美丽富有魅力,但在利益和欲望的淫威下却又放弃道义,暴露出女人软弱的天性。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相似之处在于将女陛形象提高到戏剧的核心地位。他通过刻画蘩漪、陈白露、金子等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她们作为“人”的最真切的生命意志的冲动。如在《雷雨》中,蘩漪为了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不惜背负乱伦的罪名。而当周萍退缩后,她所采用的极端手段,体现出主体性的张扬。而曹禺想要表现正是她身上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他在该剧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
曹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极端性格也与莎士比亚戏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强大的主体性意识使女性性格都显得非常极端。无论是朱丽叶、克莉奥佩特拉,还是考狄利娅,都有着追求极度伸张自我主体价值的极端性性格。这种极端性性格在曹禺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无论是蘩漪、陈白露,还是金子,都有一种为人性的完美和自由,不惜牺牲一切的极端倾向。正如曹禺自己在《雷雨》序言中所说:“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许有一条折衷的路。”曹禺通过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表达了与莎士比亚极为相似的以张扬主体性为核心的女性观,同时,对于像蘩漪、陈白露、金子这些生命意志高扬的女性,给予了强烈的肯定:“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头的日子更值得佩服。”。
二象征手法在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关联
莎士比亚非常善于用象征手法来为情节的发展烘托氛围。在莎士比亚戏剧中,象征性与戏剧情节冲突往往融为一体。如在《麦克白》中,女巫的神秘出现,成为麦克白命运的象征和预言。在《暴风雨》中,大自然中的暴风雨成为李尔王身心所遭受的打击的象征。在《裘力斯·凯撒》中,当凯撒命运遭受不测前,曾有一个预言者出来预言:让他留心三月十五日。这种神秘感充满了命运无常的象征意味。这表明:象征手法是莎士比亚戏剧强大感染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象征手法往往是通过某种怪诞的自然现象或者超自然现象的方式来表现的,这有点类似于现代荒诞剧。正如波兰学者杨·柯特指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场景“大都是自然景物。盛怒的自然眼见人的失败,或如在《李尔王》中那样,它积极参加到行动中来……自然已从这里完全消逝。人被禁锢在无生命的东西中间。但现在的东西已被提高到人类命运或紧迫局势的象征地位上来,并发挥莎士比亚的森林、风景或日蚀所发挥的作用。”而曹禺戏剧在运用象征手法来突出悲剧气氛的审美风格上与莎士比亚非常相似。在《雷雨》中,曹禺巧妙运用外部环境气氛来烘托主人公内在的“郁热”心理和生命冲动。雷雨的气候环境,正是曹禺内心郁热心理和外在残酷压抑的社会环境的象征。
曹禺在《雷雨》的序言中指出:“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火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因此,作品中的雷雨实际上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象,他象征着作者心中的一种无法言说的郁热。同时,该剧一再强化“雷雨欲来风满楼”的象征性气氛,与戏剧情节的紧张推进形成照应。从而象征着戏剧冲突即将象火山一样爆发,周家最终走向崩溃的悲剧性结局。
曹禺笔下的这种象征手法,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审美风格如出一辙,充满了命运转变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这种充满神秘感的象征手法对于曹禺来说,是内心郁热情感的自然进发。正如曹禺自己所说:“《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神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从曹禺的自序中我们不难发现,雷雨象征着作者心中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的吸引”或“心灵的魔”。
同样,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作品,也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风格非常相似,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象征性意象,象征着作品的主题和情节气氛。《日出》中,“日出”象征着“损不足而奉有余”的非人社会的结束和美好的生活的到来。《日出》的象征意义可以曹禺在该剧的跋里看出:“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是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我忍而不住了,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
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上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太阳的人们。”在《日出》中,作者多次强调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出意象,以反衬群魔乱舞的黑暗世界。例如:“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真奇怪,你为什么不让太阳进来……你看外面是太阳,是春天…”你听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同时,剧中打夯工人的歌声,象征着“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的生命冲动。《原野》中,曹禺对生命原生态的赞美心理进一步升华。剧中的原野正象征着可以容纳更为宽阔的生命空间的宇宙,及其在这种浩淼宇宙中富有诗意的自由人性。曹禺曾说:《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他读到波斯诗人欧涅尔的诗歌‘只要你在我的身旁,那原野也是天堂。他的心怦然而动: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因此,原野象征着曹禺对生命的呼唤,象征着大自然与人类命运之间的神秘关系。“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但这也正是‘原始的生命的魅力所在。”也就是说,只有最令人恐怖的原野,才能容纳最广阔的生命空间。这表明,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使曹禺作品与莎士比亚戏剧呈现出极其相似的审美风格。
三心灵辩证法在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关联
莎士比亚是一个心灵辩证法的大师。莎士比亚善于通过心灵化手法表现人的内在精神状态。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都可以归纳为心灵化的悲剧:《哈姆莱特》展示了哈姆莱特为父报仇过程中忧郁和延宕心理的演变。《奥瑟罗》展示了奥瑟罗受伊阿古欺骗后对苔丝狄梦娜所产生强烈的妒嫉心理并最终激化的心理过程。《李尔王》展示了李尔王因两个女儿忘恩负义而无法接受现实而发疯的心理过程。《麦克白》展示了麦克自在实施杀死国王并篡夺王位的阴谋中,精神崩溃而毁灭的心理过程。而曹禺戏剧在表现人的心理变化方面,与莎士比亚戏剧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本质上说,《雷雨》也是一部表现人的心理过程的悲剧。鲁大海、四凤、蘩漪、周萍、周冲都具有火一样的热情和火山一样的爆发力。他们的心理随着情节急速推进产生强大的震撼力,从而成为悲剧性重要源泉。特别是主人公蘩漪长期压抑在痛苦和郁闷之中。《雷雨》深刻地表现了被愤怒、欲望、绝望等恶性情感压迫下的蘩漪心理崩溃的过程。正如蘩漪在剧中所说的:“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向冲,半疯狂地)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在《日出》中,曹禺深刻表现了陈白露在丑恶的都市生活中沉沦堕落直到毁灭的心理过程。如果说曹禺通过蘩漪表现了她在封建大家族中由挣扎而走向毁灭的心理过程,那么曹禺通过陈白露表现了她在魔鬼世界中由无奈、抑郁、绝望而走向的毁灭的心理历程。陈白露自杀前的遗憾是她最真切的心灵告白:“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老吧。可是……。这一么一年一轻,这一么一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而在《原野》中,曹禺的心理刻画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特别是他对仇虎的分裂心理的表现与莎士比亚《麦克白》的美学风格非常相似。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是这样描述麦克白杀死国王后的心理分裂的:
麦克白:可是我为什么说不出“阿门”两个字来呢?我才是最需要上帝垂恩的,可是“阿门”两个字却哽在我的喉头。
麦克自夫人:我们干这种事,不能尽往这方面想下去,这样想着是会使我们发疯的。
麦克白: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那日常的死亡……
麦克白夫人:你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麦克白:那声音继续向全屋子喊着:“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不再得到睡眠,麦克白将不再得到睡眠……这是什么手!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而在曹禺的《原野》中,当仇虎杀了大星和小黑子后,内心也陷入了麦克白式的负罪感和恐惧感。该剧的心灵化辩证法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心灵化风格如出一辙:
仇虎:(举起一双颤抖的手,悔恨地)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这么抖。(由心腔内发出一声叹息)活着不算什么,死才是真的……(匕首扔在地上)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
焦花氏:你赶快把手洗洗。
仇虎:不用洗,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干净的。……
焦花氏:小心你手上的血会擦到脸上。
仇虎:怕什么,这血擦在哪儿不是一样叫人看出来。血洗得掉这“心”谁能够洗得明白。啊,这林子好黑!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叹了一口气)
1935年4月,郭沫若在观看《雷雨》后,在《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中赞扬曹禺在“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对人性心理的真实把握是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性的重要源泉。弗洛依德、琼斯、霍兰德等心理学家对莎士比亚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进行了极高的评价。而《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心灵化美学风格,也表明了曹禺在人性心理的把握上的卓越才能。这也是曹禺戏剧经典陛的重要源泉。
四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产生深层关联的基本途径
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深层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源于曹禺对莎士比亚戏剧直接或间接的接受。虽然人们强调曹禺是“易卜生的徒弟”,然而,用曹禺自己的话来说,他最敬佩的戏剧大师正是莎士比亚。人们曾向曹禺提问:“在您所读过的剧作家中,您最喜欢谁的作品?”曹禺明确地表示:“当然是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我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也不能比拟的。”他指出“莎士比亚和达芬奇同是伟大的天才,人类的奇迹……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事实上,中学时代的曹禺就认真地阅读了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吟边燕语》。特别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给年轻的曹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进入清华大学后,曹禺系统地阅读了莎剧原著,特别是对四大悲剧及《裘力斯·凯撒》作了反复的研读。这对于他当时正在创作的《雷
雨》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曹禹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执着和热爱的程度,用他自己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表明,莎士比亚的影响与曹禺的戏剧成就是密不可分的。为进一步推进莎士比亚戏剧对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响。40年代,曹禺还亲自翻译了《柔密欧与朱丽叶》,他在《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风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曹禺还尝试翻译了《哈姆莱特》的一部分内容”。
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密切接触,使曹禺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华和特色。当然,这种影响和借鉴是处于潜意识层面的。但是,曹禺受莎士比亚等外国优秀文学大师的巨大影响是肯定的。正如曹禺自己后来在中国莎学会开幕式上所说:“天才从来是受文化传统和历史影响最多的人……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匠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
另一方面,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的深层关联是通过“莎士比亚化”的途径实现的。即通过塑造生动真实的性格描写和情节建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价值倾向。莎士比亚戏剧对人性给予了强烈的肯定,对违背人性、压抑人性的社会压迫和禁欲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的和生动的戏剧冲突表现了当时英国社会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新兴的资本主义蓬勃崛起的历史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表达戏剧的价值倾向,是通过塑造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建构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来实现的。唯其如此,他才能深刻展示丰富真实的社会历史环境,从而表现出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此称为“莎士比亚化”,并将莎士比亚戏剧中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市民社会背景称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氓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物象不能发现。”而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剧作也通过像蘩漪、陈白露、仇虎、金子的人性和精彩的情节充分展示了“吃人”社会本质,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迫害。曹禺戏剧“莎士比亚化”的真正含义正如曹禺自己所说:“莎士比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是最贴近人心的一个,他为普通的人而写,又为天才而写;为智愚贤不肖的人而写,又为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有文化的角落而写,然而他又是多么深、多么难以讲得透的诗人啊!”正因为优秀的戏剧是“难以讲得透的”,所以曹禺认为:“戏剧的天堂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它永不宁静,它是滔滔的海浪,是熊熊的火焰……只有看见了万相人生的苦与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同时,曹禺作品“莎士比亚化”的深刻性也可以从他在《雷雨》的序言中得到印证。然而,正是在这生命冲动的自然传达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将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展示“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追求中国现代文学中渴望的“大旷野精神”和“原始的自然生命”等时代话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正如曹禺自己所说:“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啊!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标志着“莎士比亚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深入。而曹禺作品在“莎士比亚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优秀的典范,从而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