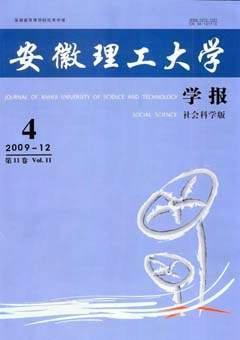《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任树民
摘 要: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 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 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 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关键词:《诗经》;赋;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4-0041-04
A New study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s of ode in The Book of Songs
REN Shu-min
(School of Literature,Beihua University,Jilin,Jilin 132013,China)
Abstract:The artistic characters of ode about The Book of Songs are newly realized by distinguishing theconventional opinion of it.Direct and vivid depi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expression,mentality,and feelings without comparison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artistic characters of ode about the Book of Songs.However,based on the essence of expression inthe lyric nature of versification,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artistic character of ode about The Book of Songs lies in exploringand expressing emotions so as to “narrate” out the objective phenomenon correlative with the special emotion and have such“temporary feeling” materialized.
Key words:The Book of Songs;ode;artistic characters
关于《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古人的认识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认为“赋之言铺”,即铺陈直叙;另一种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 1]954。当下的学者多认为“叙物以言情”“才真正触及了《诗经》‘赋法的根本特征”[2]38。那么,本文就从这两种说法出发, 在辨正的基础上对《诗经》“赋”法予以重新认识。
一、关于“赋之言铺”的几点批评
郑玄注《周礼》首次拈出“赋之言铺”这一“六义”意涵下的“赋”之界定:“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善恶。”[3]魏晋南北朝,文体自身 的审美意识觉醒,陆机在曹丕“诗赋欲丽”的基础上,提出“赋体物而浏亮”[4]的文体界定。刘勰“诠赋”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5]关于刘勰的这一界定,纪昀评论说:“‘铺采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6]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刘勰的这一界定是在抛弃了郑玄伦理比附的尾巴之后,吸收了曹陆以来特别是陆机的见解,把作为《诗》 之情感言述方式的“赋”与作为文体的“赋”体联系起来而一并论之的所得。因此,李祥在补正黄叔琳《文心雕龙注》中才批评刘勰说:“彦和 铺采二语,特指词人之赋而言,非六义之本源也。”[7]而刘勰的这一混乱,笔者拙见,郑玄其实已经开始了。
赋,一字多蕴,属钱钟书先生所论“并行分训”,“两义不同而亦不倍”[8]之列。而且,不仅如此,作为文体的赋还离不开属于六义 之一的赋:“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9]311,这就是 说,文体意义上的“赋”包含了这一源于《诗》之言述方式意义上的赋。这样,当我们考察郑玄传注《周礼》“六诗”之一的“赋”之为义之时, 显然就要注意郑氏下这一传注的文化语境。
郑玄生活于东汉末年。是时,宦官弄权,外戚专政,朝纲日非。作为“通儒”的郑玄,一方面打破经今古文之争,遍注群经,坚持固守儒家的 六经政治比附传统;另一方面也通过注经寄寓着自己的国事之慨,于是有了他把赋与“政善恶”联系起来的“六诗”传注。此其一。同时,我们 更要注意郑玄所属时代他能够接受到的作为有汉一代文体表征的汉大赋的文化语境。司马相如答友人如何为赋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 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951扬雄讲:“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0]1756班固说汉大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 嗣,抑亦雅颂之亚也。”[9]311尽管郑玄不是以赋名家,其传世之作也只有《太平御览》所引《相风赋》之残简,但郑氏对汉赋的 熟悉与了解也由此可见一斑。寻绎上述诸家对文体之赋的评介,比照郑玄的赋之界定,考虑到汉大赋的“虚辞滥说”(司马迁语),铺张扬厉 ,笔者拙见,郑玄的“赋之言铺”实际上已经有了汉赋创作及其理论评介的渗透与影响。源于此,继踵郑玄,一方面,刘勰诗赋混论,推波助 澜,使论者对六义之赋的理解赋予了更多的文体之赋的色彩。例如,清人程廷祚即认为:“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诗骚论 上》“体万物之情状”显然是陆机“赋体物而浏亮”的渗透。另一方面,与刘勰大致同时的钟嵘,其于《诗品》当中的赋之为义,不但浸润着文 体之赋的色彩,而且还越说越狭窄,进一步把《诗》之赋的意涵简单化。
钟嵘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11](“寓”,《说文》:“寄也。”[12]“寓言”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寓言十九 。”郭庆藩《庄子集释》引《释文》解释说:“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13]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宣颖的注解说:“ 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并加己案云:“意在此而言寄于彼。”[14]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索引》引《 别录》注解说:“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词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15]2144寻绎前此钟嵘的“寓言”用例,考察古今 学者对庄子以及司马迁使用“寓言”时的意涵注解,不难看出,钟嵘也是在此意涵层面上使用“寓言”一词的——“寓言”,即寄言,“意在此而言 寄于彼”。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赋虽然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与“《诗》之风谏”不异[15]3073。宣帝刘询以为:“辞 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之观。”[10]2829班固说汉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 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就告诉我们,经学的时代语境所致,致使汉人认为在这一铺张扬厉的辞体当中是有作者的讽喻之旨寄慨其 间的。陆机考辨赋体,抛弃其讽喻之旨,仅注意赋体自身的写作特点及其美学特质:“体物”与“浏亮”。那么,考虑到时代的前后相继,钟嵘 的“写物”,显然有陆机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其“写物”就是由“体物”而来。不但如此,比照汉人对赋体的认识以及我们对“寓言”一词的解析 ,不难看出,钟嵘的“寓言写物”,其整体思路就是在摆脱汉人经学语境下的赋体认识之后,借鉴了陆机的考辨模式及其话语言述而得出的这 一关于六义之赋自身美学特质的界定。至于其“直书其事”的“直”,不言而喻,理当是源自郑玄的“直铺陈”。《文选》注解陆机的“体物”说:“ 赋以陈事,故曰体物。”那么,“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显然就是互文见义,意谓直言其物而有所寄托了。我们认为,钟氏的意见虽然有失偏 颇,但也探到了“龙之一鳞”。可惜后此论者,一方面借鉴钟氏,屋下架屋,另一方面却又在钟氏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赋”的认识推向简单化。 例如,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16]42张戒说:“凡此事既明白,但直叙其事,是非自见,六义所谓赋也。” [17]于是,赋者,直言其事,其陈其事,成了人们剖析《诗经》的“赋”法最为常见的意见了。
因此,我们认为,正是缘于赋体创作实践及其理论评介的前后影响,致使郑玄以来对于六义之“赋”的认识不仅带上了文体之赋的渗透,而且 ,源自钟嵘,开始屋下架屋,进一步把《诗经》的“赋”法认识简单化、狭窄化。后此论者不察,于是大多数便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直言”、 “直陈”或“铺陈”其事的方法了。笔者拙见,正是这一先入为主的理论强迫以及屋下架屋,影响了人们对《诗经》“赋”法的深入理解与认识。 因此,我们认为,“赋之言铺”,即便是“直言铺叙”,均非《诗经》“赋”法的探本之论,这四个字对“赋”的解释不但是不够的,而且还带有片 面、狭隘的倾向。
二、《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探源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想否定《诗》的“赋”之言述有着“直言铺叙”的意涵,相反,在笔者看来,“赋之言铺”或“直言铺叙”也着实显现于《诗 》。不但雅诗当中,确实有不少铺张其辞的诗作,即便《国风》,如《小戎》、《七月》、《硕人》等,也运用了层层铺叙的方法。但是 ,情境互动,合而成诗,诗的本质在于抒情,可情感本身不具有抒发性,于是诗人寻找可以物化情感的物象以使情感物化、客观化。这个 时候,诗人为了表现情感,固然可以直言叙述,也可以层层铺叙,但“物色摇动”,“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很显然,情境相合,赋并非只 是起了“直言铺叙”的作用,寻求物质表现形式以物化情感,使情感得以客观化才应该是《诗经》“赋”法的本质指向。关于这一点,宋人李仲 蒙、清人李重华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1]954;李重华说:“赋为赋陈其事而直言之 ,尚是浅解。须知化工妙处,全在随物赋形。”[18]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说:“所谓‘叙物以言情,所谓‘随物赋形,才真正触及了《 诗经》‘赋法的根本特征。”[2]38
陆时雍说:“《三百篇》赋物陈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所以意广象圆,机灵而感捷也。”[19]“赋物陈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 ,可谓痛快!诗的本质就在于抒情,所谓“赋物”乃是为了“陈情”,这才是探本之论。“予谓诗人赋物,不过写一时之情”[20],要不然就无以解释世间之物、之事也可谓多矣,何以是诗只出现此种之事、之物,而不是它事、它物?因为这很简单,诗不是以 反映客观生活为其目的,诗所展现的本来就是一种个人情感的真实,也许这一事、一物对别人而言毫无价值,但于诗人可能却是一生的刻 骨铭心。“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邶风•静女》)不是茅草美,而是因为这是“美人”所赠。是故,一朵花可以 珍藏很多年,一句话可以询问很多遍。“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 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洧之外”之所以“洵且乐”,很显然是因为“伊其相谑”的“士与女”共观。一片风景就是一种 心情。游山玩水,不在乎山高,也不在乎水灵,但是,毫无疑问,与何人一起游山玩水却是非在乎不得的。我们说,这就是情感,它芴漠 无形难以捉摸,但它又确是真实的存在。诗的本质就在于抒发这一芴漠无形的情感。是故,所谓的“随物赋形”,我们的理解即是寻 求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而这,据上述剖析,显然是真正触及了《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
潘啸龙先生认为:“《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并不只是在于‘陈述铺叙,还在于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 ,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所谓‘直言,并非只是直接叙述之意,而是与‘比、兴的须借助外物相对而言,更有直接描绘、刻画、抒写 之意”;“我以为,诗之‘赋法,主要在于不借比兴而对事物、人情作直接的描绘和抒写;至于是否‘铺张其辞,这须视表现需要而定,并不能 作为衡量‘赋法的标准。”[2]37-39我们认为,潘先生的这一看法无疑是颇有见地的。但是,明了了诗体的抒情本质之后,潘先生 的这一意见显然需要加以说明与补充。
孔颖达说:“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词也。”关于“比”、“兴”、“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孔颖达认为:“兴、喻名异而实同”,“喻犹晓 也,取事比方以晓人,故谓之为喻。”这样看来,所谓“不譬喻”在孔氏的语境中即是不用“比兴”的意思。关于“比”,孔颖达还有一个意见:“ 诸言‘如者,皆比辞也。”下面,我们从孔氏的这些意见出发,来剖析一下下列诗句: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
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斯飞,君子攸跻。(《小雅•斯干》)
王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大雅•常武》)既然孔氏把“诸言‘如者”均视为比辞,那么上述言“如”者的部分章句自然即被孔氏视为比诗了。而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君子攸跻”以 及“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按照其不用比兴皆赋词的意见,那么,这些诗句在其语境中便是赋句了。而朱熹却与之不同。朱熹是把上述诗句均 视为赋词的。冯浩菲先生剖析《诗经》中的比诗,认为“从比句的多少着眼,可分为全篇为比与部分为比两类”,“部分为比的诗,即一篇诗 中既有兴句或赋句,或两者兼而有之,又有比句者”[21]。按照孔氏的意见,在其语境中,显然上述言“如”者的诗句均是部分为比 的比诗。以我们的理解,上述的描摹,刻画也着实为比,即便以朱熹的“以彼物比此物”[16]5的比之界定衡之,显然也是符合朱氏 的条件的,那么何以朱熹却把它们均视为赋,难道说朱熹不承认部分为比诗句的存在?显然不是这样的。“兴而比也”在朱氏的《集传》中, 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即便是“赋而比”的提法,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整部《集传》中也曾五见。这就是说,朱熹不但承认部分为比诗章的 存在,而且朱氏也承认赋中可兼容比。那么何以上述诗句朱氏却均视为赋而非比呢?在笔者看来,这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何者为比的界定 歧异所致。我们认为,这里还透露出一个何为《诗经》“赋”法根本的艺术特征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朱熹认为赋而兼比的诗句:“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邶风•谷风》)朱熹剖析诗意及其手法云:“言我之被弃,行于道路,迟迟不进。盖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 乃不远而甚迩,亦至其门内而止耳。又言茶虽甚苦,反甘如荠,以比已之见弃,其苦有甚于荼,而其夫方且宴乐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见 恤。”[16]25按照孔颖达“诸言‘如者,皆比辞也”的意见,“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显然,孔氏也会承认此句为比诗。至于“如兄如 弟”,在孔氏的语境中,自然也是部分为比了,但看朱熹的释义,很明显,朱氏并没有把它看为比辞。这就告诉我们,朱氏所认为的比之意 涵与孔氏着实还有些不同,正因为如此,在何处为比,何处为赋的地方还有些意见分歧。但寻绎对照孔、朱二氏的比中兼赋或者赋中兼比 的诗句认定,我们固然可以以“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三义原非离析”[22]143的解释以对。因为这本就是古今通识,例如毛先 舒即认为:“诗有赋比兴,然三义初无定例。如《关雎》,《毛传》、《朱传》俱以为兴。然取其挚而有别,即可谓比,取因所见感而作诗 ,即可为赋,必持一义,殊乖通识。”[23]即便朱熹本人也是以二义相兼或者三义相兼来论诗的。似乎鉴于此,我们就可以以三义 界定之不同而致诗句认定之不同来解释上述朱、孔歧异这一现象了。但在其间的比照当中,笔者却发现,问题的解决不可如此莽撞。
孔氏言“不譬喻者,皆赋词也”,“不譬喻”即不用比兴,但诗之三体三用,不用比兴即用赋,这是明摆着的或言命题,说了等于没说。此其一 。再者,“三义原非离析。如《黍离》、《清庙》、《丝衣》、《宫》之类,本直赋其事,而托黍离、衣服、宫室,亦即是比”[22]144,赋之叙事本来即可兼比。但是,寻绎上述赋而兼比之章, 比照孔、朱二氏关于赋与比同与异之处,不难看出,赋之为义也着实区别出自己,那就是孔、朱二诗均能认可的“陈”。也就是说,比可以以 静态的方式存在,但是赋则不可以,它本身必须具有势能,有着自身的叙述能力,亦即李仲蒙所言的“叙物”。但是,诗的本质在于抒情,“ 叙”必须有所选择地“叙”,亦即“随物赋形”,即寻求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是故,赋,乃是拥抱着情感的“ 叙”。其实,关于赋的这一根本特征,不但李仲蒙、李重华二李氏有所见,不同的论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流露过这一意见。例如,上 述提及的陆时雍与毛先舒即分别有言:“《三百篇》赋物陈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取因所见感而作诗,即可为赋。”另外郝敬有言:“ 情动于中,发于言为赋。”[22]143朱熹说《鲁颂•泮水》首三章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以及“思乐泮水, 薄采其茆”是“赋其事以起兴也”[16]279,显然也有“赋物陈情”的味道。它此不再枚举。
综括言之,《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按照潘啸龙先生的意见,“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 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我们认为,随物婉转 ,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1]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艺苑卮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潘啸龙.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0.
[4] 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47.
[5] 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0.
[6] 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
[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36.
[8]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2.
[9] 费振刚.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何文焕.历代诗话•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2004:3.
[1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8:151.
[13] 郭庆藩.庄子集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407.
[14]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5.
[1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朱熹.诗集传[M].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7]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岁寒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466.
[18] 李重华.清诗话•贞一斋诗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30.
[19]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诗镜总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20.
[20] 马位.清诗话•秋窗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27.
[21] 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3:77.
[22] 郝敬.毛诗原解[M].济南:齐鲁书社,1997.
[23]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诗辩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