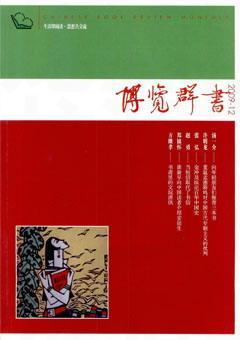周作人未自选入集的两篇文章
李青果
恕我孤陋寡闻,之前几次在图书馆与《中国新文坛秘录》相遇,都擦肩而过。原因是作者“阮无名”相当陌生,书名“秘录”,也有“黑幕”揭私的气味。想到鲁迅先生对晚清黑幕小说的批评,就以为所谓“新文坛秘录”,离不开暴露八卦花边的“秘辛”之类。之后得知阮无名就是素所敬仰的阿英先生,如此常识不备,真耍叫声“惭愧”。拿来一读,原来该书是阿英先生在1932年为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准备的资料。其时新文学运动刚过十几年,他认同刘半农惊讶于新文学发展之速之诡异,而感叹五四过后没多久,一代开新作家俨然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阿英先生决意尽量勾稽渐行渐远的史料,以打破“恍若隔世”的感觉,为写成一时代之史书做准备。只是考虑到书局的“生意眼”,在著述体例上需要“调剂严肃的空气”,“有兴味的文人趣事也说了一些”,所以书名“秘录”就不奇怪了。
从现在的阅读、使用和研究情况看,经过长时间的“层累”效用,书中的材料基本已成为常见的史料。“林琴南先生的白话文”、“老章(士钊)又反叛了”、禁售陈独秀胡适书籍的“文字狱之黑影”、吴虞“只手打孔家店”后所作“英雄若是无儿女”的艳情诗、郭沫若“孤山的梅花全文”等等,我们都不陌生。倒是书中周作人写的关于《阿Q正传》和“革命文学”的两篇文章,觉得所涉问题值得进一步追究阐发,或望联类相关资料,经过一番“旧事重提”,即使无法全历史之真相,也可算作“读其书,知其人”的补充。
周作人的评论文章《阿Q正传》发表在1922年3月19日的《晨报副刊》上。周氏以“与著者是相识的”开场,大约也承认《阿Q正传》意旨复杂,难以衡论周详,所以对读者通过此文了解它的真相和好坏,也表示“也未可知”。引发后人多方联想的是,此文后来没有入选周作人的任何一部自选文集。按周氏自己在《关于鲁迅》中解释,是这篇写作之时曾得到鲁迅首肯的解读文章。因受到成仿吾的讽刺,为避“后台喝彩”之嫌而抽去的。但据鲁迅在1925年追记,其实他对周作人的批评文章是有所不满的,不满之处,是周作人定位《阿Q正传》为“冷嘲”(《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态度与周作人认为的“后台喝彩”并不一致,而且这可能也只是不满的冰山一角。因此,我们可以推想,除了之后一年兄弟失和这一外部事件外,作者和评论者围绕作品本身的歧义,也是导致鲁迅的不满和周作人最终从文集中抽去此文的原因。
其实,周作人的文章引用之前一月茅盾对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评论,指认“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这一点,就是以勾画“沉默的国民灵魂”为职志的鲁迅也当无甚疑义。追踪周氏的文思,问题可能出在对作者心态的摸索和对作品的中外文学史类比勾稽方面。前一方面如他说“《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并且“没有笑中的泪”,以致“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无疑与作者相当隔膜。他似乎不能体会鲁迅“有爱才有憎”,以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哀心态。这种描写,把鲁迅刻画成出语刻薄的冷漠看客。其实在兄弟二人留学日本时,鲁迅就批评过“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换旬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的毛病”。(许寿裳《回忆鲁迅》)因此周氏对鲁迅心态的摸索不免有前事已忘之嫌。不过他的观点,后来毕竟引起鲁迅“自己也要疑心自己心里是否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的反讽和反思(《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则这种近于“失位”的苛评,又未必没有一定的触及灵魂的效果。
至于对《阿Q正传》进行中外文学史的类比勾稽,周作人可能更多“出位”的联想。他指出作品深受果戈理、显克微支影响属于切中肯綮,但把它与中国清代小说《镜花缘》、《儒林外史》和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我是猫》、森鸥外《沉默之塔》作“家族类似”的比较,就是跑题之论。我们知道,鲁迅本人就是中国小说史名家,对日本文学也相当熟悉。翻开《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对《镜花缘》、《儒林外史》评价都不高。他称《镜花缘》为“以小说见才学者”,评价它“不如作诙谐观”的讽刺笔法,仅有“启颜之效”,即博人一笑的意思;他称《儒林外史》为“谴责小说”,评价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所以周氏拿《阿Q正传》与之相较,就撞到了鲁迅不满的枪口上。至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恰恰是兄弟二人合作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作者。在这部译著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里,鲁迅称夏目漱石是“低回趣味”的“有余裕的文学”的代表,他的《我是猫》“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又说森鸥外的《沉默之塔》“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我们现在也正可拿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其中鲁迅所指出的低回、余裕、轻快、轻妙、机智、发一大笑,均非《阿Q正传》的风格、趣味和题旨。所以,当周作人进一步指出《阿Q正传》“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时,就更是离题万里了。
究其实,周作人的《阿Q正传》的评论写得相当用力,与他的其他作品评论比较,他为这篇文章进行的知识准备和调动的理论资源也最为丰富。之所以为求“洞见”而屡现“盲视”,之所以为求“切题”而时时“跑题”,应该是兄弟二人在文学的观念、知识和趣味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像周作人这样的行家里手也失手于对《阿Q正传》的解读,则又反过来证明《阿Q正传》在中国文坛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异数。因为它的“新异”,导致了解读的困难,也使它的评论者变成了“强作解人”。
另一篇周作人的文章《文学的贵族性》,发表在1928年1月5、6日的《晨报副刊》上。它是周氏应中法大学之邀,对之前一年由在他之后留日学生创造社成员发起的“革命文学”所作的演讲。“革命文学”是对周氏身与其役的“文学革命”的“再革命”,周氏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要。可是这篇文章也没有收入周氏的任何一部文集,推测其意,或许因为此文是由他人记录整理的讲稿的缘故,也可能因为它的题目根本不合文意。文章其实无甚高论,它否定革命文学,同时也宣传周氏本人一贯反对“载道”的文学主张。但值得注意却少人关注的是,周氏在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文学是表现思想和情感的,或者说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当我对于社会不满,或者社会加诸我不快,我对准这一个和我相反的对象来表现我所想到的思想,所感到的情感,这一种反映的苦闷的象征,就成为文学的立场和背景”,这一点值得摸索。
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研究,关于引进厨川白村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一说,其专属权大都在鲁迅,而往往把周作人当作反面的陪衬。如果从他们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来观察苦闷的象征对各自的影响,则周作人就不是站在“反面”,而是也分享了它的“一面”,甚或至于对它进行了“改头换面”。他不像鲁迅那样,从苦闷的象征出发,依据厨川白村后续的《出了象牙之塔》,希望文学离开象牙塔(个人主义)走向十字街头(普罗革命),——他是主张独自在“十字街头建塔”(《十字街头的塔》)。这种调和厨川白村理论的姿态,既不遗忘对社会有所议论,又不放弃个人主义。然而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都倾向革命的关头,坚守个人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苦境”,表现为“我”与“社会”在“常”与“变”的紧张冲突中互相的“不满不快”。所以周氏所说苦闷的象征,是个人主义与阶级革命在当时中国互相抵牾的表现。因之他的文学也就成为咀嚼“人间苦的根柢”,是“不得已的内底要求”,是别一种的用“创造力”来安顿他的“生命力”(《苦闷的象征》)。假如我们不依据惯常的进步思路,切入“文化选择”的视角,就更能理解这一问题。对周氏而言,这也并非不是一种“生是战斗”,不过表面不是诗的激烈,而是隐藏在平静的散文下面。从此出发,他闷对“苦雨”、杂记“苦竹”、“请到寒斋吃苦茶”和欣赏文字“涩涩如青果”等等,就既是他所体味的苦闷的象征,也是他所认定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上的坚守。
关于周作人的是是非非,陈平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思想史、学术史的层面加以讨论,否则“不但容易持论过苛,而且可能漠视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突破与创造”(《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如此一来,“趋新”未必都好,“守旧”未必没有道理。特别对于一些“落伍人物”出处进退的心路历程,就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或一帮一派的立场,而有较为持平的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