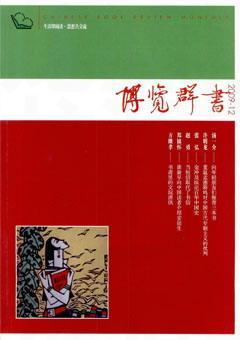张之洞的当代意义
喻 中
一
张之洞,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10月4日,历经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当时政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幅末世景象。张之洞的一生,就寄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建立。借用孔子的名言,几乎可以说是:“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从张之洞辞世到2009年,一个世纪的光阴飘然而逝。今天再读张之洞,可以发现,百年之前的张之洞,与当下的中国现实,依然具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1998年,李书磊在评论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时写道:“他的论题竟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好像在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日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品味李书磊的这段评论,我发现,把它套在张之洞的身上,也是贴切的。因为,梁启超关心的问题恰好也是张之洞留意的问题。梁、张一度是论敌、政敌,但是,正是这样的关系,表明他们在共同探索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关系问题。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至少是前期思想)被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受到了百年知识界的普遍重视;而张之洞的思想,由于被贴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在思想史上,总是不大受待见。
然而,保守者的声音也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逻辑,看到复杂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学术当于百年之后论沉浮。其实,思想也当于百年之后见分晓。在张之洞盖棺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妨以“百年祭”的方式,回首他与法理派的争论,品评他的“变法不变道”思想,重新思考他的“中体西用”的当代意义。
二
张之洞政治生涯的早期,立言大于立功,并以清流健将的角色,树立了“直声震天下”的良好形象。1882年以后,他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立功重于立言,并在洋务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对武汉的近代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晚年,他进入军机处,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人物,既立功又立言,影响力随之升至顶峰。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大讨论”,即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后世一般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源于清末修律。本来,张之洞是修律的积极鼓吹者。1902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署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详细地论证了跟国际接轨、参照西方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必要性。同年,他还与袁世凯、刘坤一共同推荐熟悉中国法律的沈家本与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律大臣。
1904年,伍廷芳正式就职修订法律大臣,标志清末修律活动全面展开。两年以后,沈家本、伍廷芳陆续向清廷提交了他们的修律成果:《刑事民事诉讼法》与《新刑律草案》。然而,这两部新法引起了张之洞、劳乃宣等人的激烈反对。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随之开始。
按照法理派的看法,修律的方向就是向欧美看齐,用西方流行的法理来指导中国的修律工作。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都是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伍廷芳认为,日本已经走过的法制改革之路,就是中国应该照着走的法制改革之路。
沈家本虽然没有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却持有与伍廷芳相似的法律改革观。在沈家本的眼里,中国法律的西方化,乃是不容抗拒的。因而,修订法律就必须以“模范列强为宗旨”。
对于修律活动中的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张之洞不愿认同。1907年9月3日,他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指责新的诉讼法“有碍难通行之处”。因为,它违反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礼教。在张之洞看来,新的诉讼法对于传统的三纲五常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动摇了中国文明的大根大本,必须予以驳斥。这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于新法的基本态度。
其实,张之洞一直都承认,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应当与时俱进,并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但是,新修订的法律,必须尊重中国的民情、民俗,必须以传统中国的纲常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因此,“今日修改法律自应博采东西诸国法律,详加参酌,从速厘定,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方为妥善办法”。
张之洞的这种观点获得了当时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譬如,劳乃宣就为礼教派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学理化”的论证。他说:“风俗者,法律之母者,立法而不因其俗,其凿枘也必矣。中国,农桑之国也,故政治从家法;朔方,猎牧之国也,故政治从兵法;欧美,工商之国也,故政治从商法。若以中国家法政治治朔方,以朔方兵法政治治欧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行也。今欲以欧美之商法政治治中国,抑独可行之无弊乎?”在这段文字中,劳乃宣把法律分为三类,目的也是为了论证中国的法律必须符合传统中国的风俗,必须遵循传统中国的纲常。
三
通过比较法理派与礼教派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两面。
一方面,张之洞虽是礼教派的主要发言人,却主张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变,也应当变,不变不行。而且他不但宣传变法,还积极推荐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并批判那些裹足不前的守旧者:“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迁儒”,“一为苟安之俗吏”,“又一为苛求之谈士”。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认同变法、积极推进变法与修律的同时,却又在法律与纲常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法律可以变,但纲常不能变,且变法不能冲击纲常。在写于1898年的名著《劝学篇》中,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就是“变法不变道”。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具体的法制应当按照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革,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圣道”、“伦纪”绝不能丢。否则,就将无以“立本”。
与“变法不变道”相比,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人的观点是“变法也变道”。譬如,以“父子平等”取代“父为子纲”,以“夫妇分资”取代“夫为妻纲”,以西式的“个体主义”取代中式的“家族主义”等,虽然没有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却已隐藏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了。尽管如此,法理派并没有只手打倒三纲五常的决绝。他们只是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法理与法制来改造中国的法律;如果在无意之中触及到三纲五常,那也是改革本身的
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改革而必须支付的代价。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对于法理派的批判,对于“变法不变道”的坚持,并不是一个临时生出的念头,而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礼法论争中的“法”、“道”之分,不过是他的“体”、“用”之别的具体运用而已。在礼法之争中,张之洞对于三纲五常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对“中体”的坚守;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不过是把“西学为用”付诸实践而已。
在张之洞的思想中,体与用的区别,对应于道与法的区别。在体、道与用、法之间,主次、轻重、本末都有严格的差异,绝不能相互混同。大致说来,中体(不变的道)是根本,是目标,体现的是价值理性;西用(可变的法)是路径,是方法,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因此,中国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及其他制度、技术的吸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这场争论,清廷的立场当然是偏向礼教派。1909年2月17曰,清廷以最高仲裁人的身份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这段话,听上去几乎就是张之洞的口吻。
作为法理派的对头、礼教派的旗手,张之洞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支持他的清廷很快就跨台了。而张之洞也在清廷作出裁决的数月之后,撒手人寰,彻底告别了这场所谓的礼法之争。
四
以中国礼教纲常的名义反对西方法理,尤其是反对西方法理对于中国纲常的挤压与消解,几乎可以视为张之洞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推出的压轴大戏。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张之洞在自己年届七旬之际,掀起这样一场“思想大讨论”,当然是多种历史机缘交错作用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个思想事件却可以解读为一个暗含着历史玄机的隐喻:张之洞殚精竭虑的一切,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而且,在这个主题上的争论并未随着清廷的裁断而结束,也未随着张之洞的辞世而结束。在张之洞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礼教与西方法理之间的争论,在“中西之争”的思想潮流中,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反反复复地出现。
在宗教学界,1973年,陈观胜出版《中国转化佛教》。在这本著作中,陈观胜认为,与其说是外来佛理征服了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转化了外来佛理——禅宗就是这种转化的产物。同样,张之洞身后的百年史,是证明了西方法理已经征服了中国文化呢?还是中国文化正在转化西方法理呢?此外,在中国思想界,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在语文学界,有汉字是否应当拉丁化的争论;在经济学界,有要不要市场的争论;在政治学与法学领域,有儒家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争论,有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专业化的争论,有法治保守主义与法治激进主义的争论,等等。大致说来,在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论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的影子。这样的争论,也许是现代中国人根本无法摆脱的一个历史宿命。谁让中国从“天下时代”迈进了“万国时代”呢?
在张之洞的晚年,时代的主题词是“变法”。张之洞也支持变法,但要求“变法不变道”。在张之洞辞世一百周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变法”虽已换成了“改革”,然而,改革就是变法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改革的实质就是“变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其实就是坚持变法、深化变法。既然如此,我们在强调变法(或改革)的同时,有没有“不变的道”呢?现在,按照决策者的说法,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不变的道”。如果说,张之洞守护的“道”,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那么,现在必须坚持的“道”,其核心内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表面上看,张之洞与法理派关于清末修律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百年的实践似乎也证明:是张之洞错了。他太保守了、太落后了。然而,就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后的今天,一场大致相似的争论正在或隐或显地展开:在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法制之路,到底应该如何往前走?
60年的法制之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借重苏联的经验;后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参考欧美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制度安排、技术手段。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欧美式的法治,几乎成为共识——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法学人,都希望早日告别“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状况。然而,在经历了30年的法制改革实践之后,决策者发现,欧美式的法治既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临中国,甚至也难以妥贴地回应、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决策者开始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有意与资本主义(欧美式)法治理念形成某种相互对照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具体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法律、法治、法制的领域内,为不容变更的“道”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变法不变道”:当下的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完全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法治的因素(先进经验),以之完善中国的法治或法制。但是,在变法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道。这样的“理念”(道),与张之洞着力维护的不容变革的“纲常”(道),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五
当下,众多的法学人依然在承袭伍廷芳、沈家本等“法理派”的思维模式:必须把西方法理作为中国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大多数当代法学人看来,只有欧美的法理才具有普适性,才具有正当性,才是更高的“道”。同时,也只有欧美的近现代法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无论是法律的理念还是法律的制度、技术,都应当向欧美看齐。30年来,中国法学人关于法治的“十大训诫”之类的主流论述,无不是以欧美国家的法理及其实践为理想图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法治建设之后,当代的“法理派”学人不免有些失望。因为,理想中的欧美式法治,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中国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理想中的法治图景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面对这样的落差,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批评现实,试图以理想强迫现实,试图以西西弗的精神,驱使现实向理想靠拢。还有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干脆不再关心实践中的法治或法制。他们退回到书斋,在“纯学术”的旗号下,“为学术而学术”。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法学景观。正是这样的景观,让我想到了张之洞,并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张之洞百年祭”。
“祭”往是为了开来。百年前的礼教派与法理派虽然观点对立,但争论尚未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张之洞就去世了,清政府也很快覆灭了,双方的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但是当下的分歧,则象征着已经消散的烟云又一次汇聚成为了浓浓的思想迷雾。而且,决策者必然会坚持不容变革的“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法学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一方面,对现实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当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远离现实的“纯学术”也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法制改革的方向呢?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呢?旧的“纲常”与新的“理念”的关系呢?哪些是“可以变的法”?哪些是“不能变的道”?如何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之间进行恰当的取舍?“体用关系模式”的解释能力到底如何?甚至,“体用二分”能否成立?等等重大现实问题,法学人岂能袖手旁观?岂能在“以学术为业”的名义下推得一干二净?
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际,通过理性的、平和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思考与对话,重建未来中国法制改革的共识,也许是当代中国“法理派传人”、“礼教派传人”共同的任务。让我们翘首期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