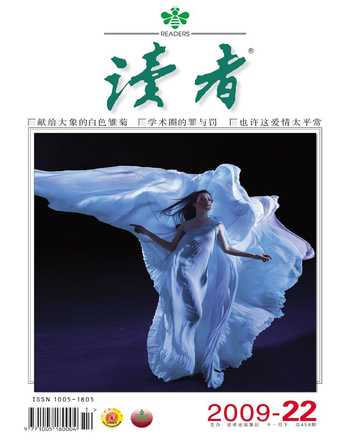在篱笆外奔跑
张祎旸
小格,你也和我一样铭记着那个夏天吧?
在那段废弃的弄堂里,常有乌鸦呼啦啦地飞过,深灰色的影子掉落下来,落在柔软的青苔上,发出清晰而巨大的声音。那声音在深深浅浅的时光中飞行,寻觅,永不停歇。
一
小格是一个画家,我永远深信这一点。他那干燥的手掌上总残留着色彩明媚的味道,那些缤纷的颜色渗入他纵横的掌纹,让他的手成了一幅独立的画。
那段废弃的弄堂是小格最宝贵的财富。里面有凌乱的画夹和成沓的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颜色随着小格的手跳跃,奔跑,飞翔,落下。橘色的灯斜斜地照着小格苍白的手指,感觉像一幅寓意深刻的画。
“你要离魏小格远一点儿。”妈妈坐在橘色的灯下对我说,“你要像我一样当个医生,别像魏小格一样……”我望着妈妈苍白的嘴唇在橘色的灯下一张一合,厌恶一点儿一点儿聚集起来。“明白吗?”妈妈忽然提高了声音,声音尖锐地刺破了橘色的灯光。望着满地斑驳的碎片,我机械地笑了笑:“明白了,我会当个医生。”
“明白就好,学习去吧。”
我掩上房门,从床下拖出一沓沓儿时的画,眼泪无声无息地滴落,激起细碎的尘埃。泛黄的纸上堆积着陈旧的颜色,一张又一张,像一个又一个离我而去的古老而陌生的童话,在早已远去的岁月里,带着嘲讽的微笑冷冷地望着我。
二
坐在弄堂潮湿的地上,魏小格自信满满地告诉我:“苏朵,我要当一个画家。”
望着小格闪闪发亮的眸子,我用力点点头。
我是那样羡慕小格,也是那样同情小格。我知道,那些无意间被小格带回家的画,会被小格的妈妈用力撕掉。小格的妈妈,那个烫着棕色头发的女人,流着泪,咬着牙,让那些无辜的画变成无数浸染着明媚颜色的碎片,再用力把这些碎片扔在小格头上,让它们纷纷扬扬地落下。那场景孤独而无奈地映入小格的瞳孔,成了我们心中共同的忧伤。而小格没有把他的颜色封存在时间中,他让他的颜色随他的梦一起在时间的河上生长,繁衍——尽管他的妈妈也是那样期望他成为一名医生。
小格在他凌乱的画夹中画着画。他苍白的手指在同样苍白的纸上游移,像深海中一条孤独的鱼。
我站在小格的旁边,翻着他的画。浓郁的色彩抱在一起,像凝固的时光。
“画好了。”小格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仿佛是从某个极为遥远的岁月缓慢地抵达现在。画面是那样凌乱,让人不知所措,像一块破碎的壮锦。我仿佛看到那些在小格笔下游走的颜色在尖锐地破碎,终碎成一地眼泪。
“小格,你画的是什么呢?”
“小格,你画的是什么呢?”几个月后,有一个女孩儿也这样问小格。她有着细长而迷蒙的眼睛,倚在小格瘦削的肩上,带着浅浅的笑。
她是蒙子。她的到来使小格冰一般冷冷的眸子略略闪出些细碎的温度。
小格在作业本的末页为蒙子画了像。画像上蒙子细长而迷蒙的眼睛像一口充盈着无穷诱惑的井,令人沉醉。
谁也没有想到小格的爸爸发现了这幅画。在小格家宽敞的客厅里,小格妈妈尖锐的哭叫声有力地击打着满屋坚硬的沉默。小格的爸爸与小格之间是那种男人的对视。爸爸眼中含着愤怒,他的眼神是单一的,愤怒就在其中疯狂地演绎;小格望着爸爸,他的眼神是那样复杂,既倔犟又恐惧,既无助又忧伤。
“说吧,魏小格,你画的是谁?”
爸爸拼命压抑着愤怒,而他所讲的内容忽然让魏小格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他笑出声来。
魏小格的笑声在那一刻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刺耳。这笑声击碎了爸爸的压抑和妈妈的哭叫,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在魏小格的两侧脸上各扇了一巴掌。
魏小格愣了一下,他在那一刻感到了什么。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立的,却没有想到,牵着他的两根线,一直没有断裂。
魏小格转身跑了出来,他的动作是那样迅速。他把门狠狠地摔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三
妈妈忽然说,魏小格是个独立的孩子,只是独立的方式过火了。
我愣了一下,既而点点头。
四
魏小格告诉我他要走了。
魏小格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夏天已经要结束。空中飘着雨,打在对面的房檐上,檐上有黑的瓦楞,细致得像描出来的。雨又从檐上摔下,摔成更小的碎片,无声地隐入空气。
魏小格背着画板,带着那种我无比熟悉的颜料的味道上了火车。他的笑很从容也很坚定,洗去了以前的冷漠,他仿佛真的独立了。
火车开走了,小格的爸妈匆匆赶来,他们只看见了小格在白雾中挥动的手臂,带着一种坚定的独立感。我猛地想起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和那条弄堂里雨润烟浓的长街。
向远处望去,我仿佛看见天与地的交会处,一个人在缓缓地行走——在那笔直的银亮中,一个独立的剪影渐长。
五
长大后,遂妈妈的愿,我成了医生。某一天,在报纸的角落里,我看到一篇极短的文章:画坛新人魏小格画展于今日举行。
瞬间,无数的人与事重新在我脑海中蔓延:小格、蒙子……那些画面从已逝的时光中站起来,抖抖灰,又重新浓艳。
小格,他真的独立了,可我呢?
望着逐渐远去的岁月,我不知用何种表情面对。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都已起程,笑笑,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立蓝天。
(顾盼诚摘自《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