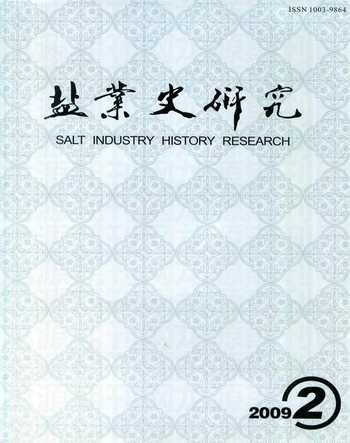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
汪崇筼
摘要明万历年间,淮盐逐步实行“仓盐折征”。这是朝廷“政商分离”变革的第三步,并有潜移默化的可能。袁世振于万历四十四年,在其《盐法十议》中,并未提出“纲运法”(本文称其为第二疏理方案),而是提出一个更加损害盐商利益的方案(本文称其为第一疏理方案)。但该方案出台后,即遭到盐商(尤其是大盐商)的抵制。“纲运法”则是在袁世振第一方案失败后,于万历四十五年九月,在去扬州的路上,经与盐商接触后,偶然提出的。
关键词明代;万历年间;淮盐;盐政变革;疏理方案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9)02-0003-10
明万历年间,淮盐经营曾完成其“政商分离”的第三步变革,并在四十五年进行过一次盐政疏理,推出纲运法。因从明初开中盐法的实施开始,直到万历年间,若依据盐法,则盐引的使用是一次性的,但纲运法是将盐商编人纲册,并“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故人们一直以为,纲运法导致(或加强)了两淮盐商的垄断。笔者在以往探讨中,曾于不同场合,分析过疏理原因,指出万历晚期的淮盐经营已到崩溃的边缘,并分析过纲运法的内容和实质,指出纲运法并无导致(或加强)盐商垄断的目的与效果。只是这些探讨比较分散,有些也欠深入,尤其对盐政变革较少分析。此外,袁世振在其《盐法十议》中,并未提出纲运法。该法是在其第一疏理方案遭抵制后才被提出。现本文着重就盐政变革、疏理前淮盐经营已到崩溃的边缘,以及袁世振的两个疏理方案等问题,再进行一些集中的表述,以向学界请教。
一、“政商分离”的第三步变革
明代初年,朝廷是全部盐货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当时朝廷迈出“政商分离”的第一步,是告别国家专卖制,以盐粮交换方式,允许商人将盐货从盐产地官仓支出后,运往引地销售,这时商人与灶户不能进行交易。到明代中叶,随着余盐开禁,灶户可将余盐直接卖给持有正引的商人。但这时灶户的正额盐仍不能直接卖给商人,故这是朝廷迈出“政商分离”的第二步。到明万历年间,则已出现盐商所掣正余二盐,均须向灶户购买的局面。即《清盐法志》称:“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这是明代淮盐经营中,“政商分离”变革的第三步,也即关键性一步。自此以后,朝廷便摆脱全部经营风险与烦琐,扮演起专制性收税人的角色。只因史料对这步变革的直接记载过于简略,故下面要就此问题作一些探讨。
从袁世振所留史料看,仓盐折征并非一蹴而就。它也是逐步演变,并有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如袁世振在论及“平场盐之价”时称:“所虑者惟场盐踊贵,……盖十年以前,甚苦盐贱而病灶。近十年以来,又苦盐贵而病商。往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为价仅七八分,近渐增至三钱。每一引须火盐五桶,则去价一两五钱。”。该史料写于万历四十四年。由此可知,十年以前的“往时”,应约在万历三十四年。当时火盐价每引银0.375两(桶价平均取0.075两,5桶共0.375两)。近十年以来的“近年”,则渐增至每引银1.5两。袁世振称:“两淮岁额盐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除开豁、逃亡及改征折色外,实征本色上仓盐三十七万三千二百余引耳。视之岁额仅仅强半。以若干草荡,办若干引盐,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单盐停滞十余年未掣,各场额盐,亦停下十余年未支。及至关支,辄称无盐。每千引或给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货抵偿。商恐违限,不得不贵买,以足榜派之数。”。这就是说,按朝廷规定,到万历四十四年时,两淮正额盐只有一半改征折色,其另一半尚须上缴官仓,以供盐商支领。但实际上,盐商到官仓,往往是无盐可支,或只能获得“不堪物货”。商人怕违限,则只好另外购买。
明代两淮,所辖分司有三个,即泰州、淮安、通州;批验所有两个,即仪征、淮安;盐场有三十个,且每场各配有盐课司一个。。袁世振称:“窃谓三十场额课,年年报完。报则有盐,支则无盐,不知此十余年额课之积,毕竟顿于何地乎?盖场官也、总催也、灶户也、吏胥也,尽以场盐鬻之私贩,无一登于廪者。而分司官又与若辈巧为欺蔽。虽有查盘,祗循故事。今所望于盐臣,严督三分司官,查核仓盐。按其十余年来所报完数,从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经商支,已入仓者几何,未上仓几何,务要清核明白,一一设法追完,尽入仓廒,以俟榜派之商,随到随支。其所征人之课,或至充栋,即为平价,卖作商人火盐,既省上仓耗费,又免久堆消折。而价以二钱一引为率,贮司以给轮年支商。如是则价无腾踊,而灶无积骗,此诚甦商要务也。”很显然,袁世振在这里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因按上述所称,两淮应上仓正额盐,以每年37.3万引计,十年则有373万引,如此数量的正额盐,竟被灶户及各官吏胥役所干没,商人无盐可支,则肯定是重大案情,朝廷不可能放过。现既然朝廷未曾追究,则表明其中必有原因。
明后叶的淮盐生产能力,是正额盐的数倍,余盐生产占主要地位。按规定,商人“支买各有定场。于此场支正盐,即于此场买火盐。乃近年以来,群三十场支盐之商,而并聚于富安、安丰、梁垛、何垛、东台五场。场盐虽欲不贵,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场者,岂不以盐为业?而正盐则仅支折价,火盐则委弃莫收。如去岁通州分司所申庙湾一场,东南北三仓,所积盐至七百余堆,已榜派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营求不派,欲不卖之私贩,其可得乎?”
由上述两段史料,可看出一个较大的可能性。即到万历中期以后。虽朝廷规定正额盐一半折色,但实际在灶户、盐商及两淮盐政部门之间,已形成默契,将另一半也实行折色。该做法对灶户(尤其是对条件优越的灶户)而言,并无害处,因他们可藉此以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又对盐政部门而言,因正额盐的开中粮食早已被朝廷收入,现即使无盐支给客商,也并不损害朝廷的利益,只是需要商人愿意即可。至于灶户上缴的正额盐折色货币,则有可能部分偿还给商人,因上述史料中,有将卖盐收入“贮司以给轮年支商”一句,以及“正盐则仅支折价”一句可作启发。现假若未偿还给商人,则便是盐政部门的收入(但非私人干没)。
而在盐商方面,他们对于正额盐的无论部分或全部折色,则都是一种“半推半就”的无可奈何,因他们尚有更多的利益需要权衡。首先,盐产量的增加,可为盐商提供选择的机会。如上述所提富安、梁垛等场,它们较为集中,且交通便利,其中又以梁盐质量最好,在江广口岸卖价最高,安盐则次之,这些都是商人所追求的。另外,尚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到万历时期,不但正额盐需要守候,而且余盐课银也须预纳,且时间长达十年,故扣除守候费用及预纳课银的利息后,商人运销官盐,与清代嘉道时期相似,是无利可图,或获利甚微的。他们须靠夹带盐斤才能获利。如袁世振称:“奸商夹带盛行,单掣稀少。”而这
部分盐货的价格及数量,是全由商灶之间私定;其通行则须盐政部门的默契。故权衡种种因素后,商人只须最终有利可图,其正额盐的有支与无支,或其有偿与无偿,则均可“从长计议”。正是这种官、灶、商三方面的利益权衡,导致万历年间淮盐经营中“政商分离”的第三步变革,是一个逐步演变,甚至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袁世振也只是在论“平场盐之价”时,抨击过这种演变,而在分析盐商实际经营成本时,则并未考虑盐商尚有支盐的可能。
二、淮盐经营已到崩溃的边缘
所谓“疏理”,是指盐政问题成堆,需朝廷派要员到两淮,与盐商一起共谋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取“疏通理顺”之意。而所谓“问题”,则归纳起来,仍是“困守支”挫伤盐商的积极性,使朝廷盐课收入无望。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政也曾进行过一次疏理。这次疏理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便分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内商预纳守候之苦
明万历年间,两淮的行盐格局,虽与隆庆初年一样,为边商开中,内商守支,水商行盐,但其难度则更大。归纳起来,即如上所述,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守支问题上,虽正引已无盐可支,但守候仍是必须。尤其这时余盐课银已实行预纳,时间则长达十年;第二,在购盐问题上,不但余盐需要购买,而且正额盐也需购买。这时,朝廷向两淮派出盐务太监,“借浮课,行大盐”,以朝廷名义向商人借银四百余万两,后演变为余银预征;又增加每引盐的实际重量,即“行大盐”。结果使大量盐引壅滞,商人资本被严重占压。袁世振称:“往因鲁保行大盐,岁课止压两年有半,至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司库空虚,淮商逃散。”而据《明实录》记载,鲁保在万历二十八九时,即在两淮活动,权倾一时。现将袁世振史料中,有关内商预纳守候之苦的记载,略摘录几条:
1“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敝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展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这里需要指出,所谓“囤户”。是袁世振对两淮大盐商的污蔑性称呼,稍后将对该问题有所探讨。
2“今淮上所谓新旧兼行者,旧引断自三十二年是矣,乃新引则断自三十六年。”此即表明,当时正引积压,最长已达12年。即万历四十四年时,尚在行三十二年之正引。
3“及内商苦于套搭。十年之间,纳银三次,而尚不得行盐一次。”。
4“银征于八九年前,盐掣于八九年后,预征之谓也。夫至于八九年后,虽有利息,尽归赔累矣。……年复一年,套上加套,膏血有尽,预借何休?是徒抱积薪之叹也。贫者力难报单,并旧引而不掣;富者勉图掣旧,恨新债之日增。或质引目以纳余银,或罄田庐以实单口。甚有子承父套,弟承兄套,父子兄弟不相保,而皆以命殉者,是长为饮恨之囮也。”
5“何谓在内商则欲行旧引也?其言曰:朝廷预借商银四百余万,今不言借而言征。惟征之一字,可以行法,故执敲朴以鞭笞之。预征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后,惨刑血比,总为岁解。岁解不足,势必责逃亡于见在;横征不已,将复驱见在为逃亡。其所以免脱未能者,惟陈陈旧引,为祖父积累之艰。倘得蚤为销掣,掉臂而去如远坑阱耳。其专欲旧引之亟行者势也。”
(二)边商中盐之苦
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资本已超出西商,而成为两淮盐业中的第一大商业资本。这时两淮盐商的运销任务,也只到各大口岸为止(如汉口、南昌、安庆等地)。但即使这样,一般内商因余银预纳、正引积压和正余二盐并买等缘故,其资本已被严重占压。他们无力再提前购买边商送往两淮的仓钞。边商则因仓钞无售而苦不堪言。户部尚书李汝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今边商贫已彻骨,急已滨死。……顷大同五路,商人刘尚质等,告称粉骨碎身,所济几何?哀求本部,设法通理两淮盐政。山西镇商人赵一鹤等,告称本镇一十八万盐粮,今经四载,尚未完纳。商命殆尽,军需无输,哀求本部疏理盐法,责令两淮新旧均行。宣府镇商人徐恕等,抱其不售仓钞,赴部投告,极称两淮盐法坏极,引目壅积不售,家产赔尽,无路可逃,只得将往淮上所卖不售仓钞寄库,哀缓比追新粮,仍求本部设法疏通,超活蚁命。凡今九边万商,赴部诉告者,无不抢地呼天,拊膺泣血,且谓及今不清,终无望清之日。”
(三)朝廷盐课收入无望
明万历年间,据“山东清吏司案呈国家财赋(约每年银400万两),所称盐法居半(约每年银200万两)”;而在整个盐课收入中,两淮又约占其半。即其中余盐课银60多万两,开中盐粮折银近40万两。但到万历四十四年时,其情况则是:
1因内商已无力再行预纳,致使余盐课银停压近三年,朝廷少收余盐银200多万两。即“两淮盐课,停压两年有半,已少银一百七十余万有奇。今岁又复愆期,时逾秋仲,而上解方至,则下解必更逾越,是将又压半年矣。合三年,则欠二百余万矣。又加云南额解,执留二十余年,少银七十余万。此皆举朝能知之,能言之者。”
2因仓钞在两淮无售,边商也无力再参与新的开中,致使各边开中停压多年,朝廷少收盐粮折银230多万两。即“九边盐粮,因淮盐壅滞,引难售卖,缺额尤多。以停压年份言之,今四十四年,总查完数,则四十三年以前,各镇所中盐粮,皆应全完:永平一镇,盐引银仅四千两,其报完稽考簿如期缴到;宁夏只缴至三十六年,欠八年;延绥虽缴至三十九年,中有三十六七八等年未到,加后四年,共欠七年;固原缴至二十二年,欠十一年(原文为“二十二年”,但估计是“三十二年”之笔误);宣府、辽东俱缴至四十年,欠三年;甘肃、大同、山西神池等堡,俱缴至四十一年,欠二年;蓟州缴至四十二年,欠一年。以各镇额数,扣其欠数,实共欠盐粮银二百三十余万。其所欠虽日压年渐完,实则层累而逋耳”。
此外,自嘉靖以降,各边开中已由原来的自由贸易,演变为强行摊派。万历年间则更为恶化。边地商人或富有之家,一方面逃避开中,另一方面则在上纳时“克减斗头”(又称“告减斗头”,即减少上纳数量)。“十数年来,自各阉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边商赔累,拘囚刑进,其额粮竟不能完。除压年所欠,即有完者,每年告减斗头,四六交纳,其实未经半收,通同该仓,虚出关钞。据各镇所申,仓弊如海,甘死不更,则何有半数人仓也?即有半入,姑以十年计之,已亏边饷三百余万。合压年虚减,十余年来,共损盐粮五百余万。”
这就是说,“总盐课、盐粮,所亏国计,遂至七百余万矣”。若究其原因,则是“阉弁倚借浮课,肆行大盐,遗祸至今”。故李汝华称:“计内帑淮盐,所入不过一百二十万有奇耳,乃令国
计亏至七百余万。目今已后,尚未可知,然则中涓竭泽,其于国家利耶害耶?”。袁世振的描述则是:“塞粟空虚”和“司库空虚,淮商逃散”。至此已可看出,万历四十五年疏理前的两淮盐业,已跌到崩溃的边缘。
三、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
袁世振于万历四十四年奉命疏理两淮盐政。为此,他曾写有《盐法议》十篇(也即《盐法十议》),经奏报皇帝同意后实施。在这十篇《盐法议》中,袁世振以种种理由,否定当时正在实行的“新旧兼行,二八抵验”的行盐办法,以及商人为此而重新提出的其他各类方案,其目的则是要推行自己的方案(即本文所称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袁世振还称,其方案承袭了庞尚鹏的“小盐法”之意。因此,要了解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的本质,还须先了解庞尚鹏的“小盐法”,以及“新旧兼行,二八抵验”的行盐办法是何含义。
(一)庞尚鹏“小盐法”的本意
嘉靖末期,两淮因行工本盐每年35万引,导致引目积压。到隆庆二年时,尚积压约500万引。为此,庞尚鹏曾奉命疏理,并提出速销积引的两项措施:
1扩大每单行盐数额
淮盐分南北两路。原淮南每年行8单,每单7.3万引,小计共58.4万引;淮北每年行4单,每单5万引,小计共20万引。故两淮原每年共行78.4万引。
现淮南每年仍行8单,但每单8.5万引,小计为68万引;淮北每年也仍行4单,但每单5.5万引,小计为22万引。即疏理后两淮每年共行90万引,比原增加11.6万引。
2余盐改行小引
嘉隆之际,正额盐引价很高,盐商行销正额盐均无利可图,他们是靠行销余盐而获利(因这时余盐课额相对较低,且无预纳之苦),故朝廷令此二盐并掣。即每引共计550斤,其中正额盐285斤,余盐265斤。疏理后,每引改为485斤,其中正额盐仍285斤,余盐则200斤(即相当于疏理前每265斤余盐,带销285斤正额盐;疏理后每200斤余盐,带销285斤正额盐)。同样重量的余盐,疏理后可拆解的引数增加,以带销更多的正额盐,从而达到速销积引的目的。这便是庞尚鹏“小盐法”的本意。
前已指出,该时期商人主要靠行销余盐获利。这又相当于余盐改行小引前,每100斤余盐带销107.5斤正额盐;改行小引后,每100斤余盐带销142.5斤正额盐。为不使盐商心理受太大冲击,庞尚鹏对盐商应缴的余盐课银,也作了相应调整。以淮南为例,史料称,改行小引后,“淮南纳余盐银五钱二分五厘”,比改行小引前“减纳余银一钱七分五厘”。由此得,改行小引前,每百斤余盐纳银二钱六分四厘;改行小引后,每百斤余盐纳银二钱六分三厘,略低一点。因疏理的动机是速销积引,减少商人的“困守支”,故上述思路尚可被商人接受。且疏理前,每引重量为550斤,即每年销盐43120万斤(也即550×78.4);疏理后每引重量485斤,每年销盐43650万斤(即485×90),两相比较,疏理后每年销盐重量,无大的增长。
(二)“新旧兼行,二八抵验”的行盐办法
在袁世振疏理之前,两淮是实行“新旧兼行,二八抵验”的行盐办法。袁世振称:“今淮上所谓新旧兼行者,旧引断自(万历)三十二年是矣,乃新引则断自(万历)三十六年,是皆囤户所收之引,而非边商见到之引也。盖自四十三年以前,边中仓勘,多以贱值投之囤户,与边商无涉矣。故今欲肇自四十五年,复祖制行正盐,必以行见引为主。而行见引,必以四十四年所到边钞为正。”在这段文字中,袁世振歪曲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从明朝初年开始,开中盐法一直是按开中年份的先后为序,安排商人行盐。“困守支”便是最好的例证。即使是袁世振后来提出的纲运法,其也是“遵照盐院红字簿,挨资顺序,刊定一册,分为十纲”。故明代绝无当年必以行上年新到-仓钞为正的祖制存在。
例如,在万历四十四年时,若按祖制行盐,则应以中盐顺序,安排守候年份最久(即万历三十二年)的盐引持有者行盐。只是从万历三十二至四十四年之间,有十二年之久,故为照顾边商的利益,再立一条规定。即在万历四十四年,又安排一部分万历三十六年的盐引持有者行盐。上述两个年份的盐引比例,是各占一半。如淮南每年行盐68万引,其中34万引安排给万历三十二年的盐引持有者(此被称为旧引),另34万引则安排给万历三十六年的盐引持有者(此被称为新引)。即“以六十八万引,剖而二之,半行新引,半行旧引”。此外,为防止商人只行旧引,不买新到仓钞,故又增加一条规定,叫“二八抵验”。即“今淮上虽行旧引三十四万,然仍用二八抵验之法,则仍套买边引二十七万有零”。其含义是,凡于万历四十四年,行万历三十二年旧引的商人,须共购买27万引新到边钞以作抵验(34×0.8=27.2),否则不许行盐(新到边钞一般是由大盐商先行购买,然后供自用,或卖给他人)。
上述便是当时正在实施的“新旧兼行,二八抵验”之法。很显然,该法程序烦琐。尤其在同一行盐年份里(如万历四十四年),行新旧之引的商人,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即行新引是一批人,行旧引又是另一批人),再加以各人的行盐数量不同(如各人的经济实力不同),故不便于管理。此外,边钞到达两淮后,因须守候8至12年才能行盐,故其价值必然很低。边商怨声载道。袁世振便是藉此形势,推出其“以行见引为主,附销积引”的疏理方案。即“今欲肇自四十五年,复祖制行正盐,必以行见引为主。而行见引,必以四十四年所到边钞为正”。但如上所述,正是该方案,违背了按中盐顺序行盐的祖制。
(三)袁世振的第一疏理方案
袁世振在其十篇《盐法议》中,曾以不同方式,反复宣示其第一疏理方案。现将该方案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1到万历四十五年时,两淮每年共行盐90万引,分12单。其中,淮南8单,每单8.5万引,小计68万引;淮北4单,每单5.5万引,小计22万引。这与庞尚鹏疏理后的行盐数据相同。
2现对于淮南,将其中的每年52.9024万行新引,即平均每单6.6128万行新引。另每年尚有15.0976万则行旧引,即平均每单1.8872万行旧引;但对这部分旧引,则取庞尚鹏小盐法之意,一分为二,得3.7744万引。也即疏理后,以每单3.7744万旧引,与每单6.6128万新引同行。
3对于淮北,将其中每年17.6156万行新引,即平均每单4.4039万行新引。另尚有4.3844万行旧引,即平均每单1.0961万行旧引;但也对这部分旧引,取庞尚鹏小盐法之意,一分为二,得2.1922万引。即疏理后,以每单2.1922万旧引,与每单4.4039万新引同行。
4对于旧引,疏理前每引重570斤(正余盐一起),若按内商卖给水商的盐价,每引银3.2两计,则相当于水商每两银买盐178斤。现每引加142斤,得712斤,但一分为二,得每引356斤,
卖价则定为银二两(即仍相当于每两银买盐178斤)。为不再增加商人的负担,方案还规定,其“包索、赈济、过坝、挑河诸项,俱止作一引行”。
(四)对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的讨论
尽管袁世振称,其方案承袭了庞尚鹏的“小盐法”之意,但实际上,他与庞尚鹏的疏理理念大不相同,故其效果也不相同。现不妨从两个方面,将袁世振方案与庞尚鹏方案作一对比。
1对比疏理理念
前已指出,“疏理”是取疏通理顺之意。即所谓“疏通”,便是将严重积滞的旧引(又称积引)消化掉,以减少商人资本的积压。这是疏理的两大任务之一。
嘉隆时期,每引盐重550斤。其中正额盐占285斤,余盐占265斤。庞尚鹏所提疏理方案,是将每引重量改为485斤。其中正额盐仍占285斤,余盐则降为200斤。因该时期商人运销正额盐需要守支,但余盐无预纳之苦,即商人主要靠运销余盐而获利,故疏理后,商人欲获得与疏理前同样的利润,则须带销更多的正额盐。而这时所要疏通的积引,也正是壅滞的正额盐引。尤其该方案无运销现中引盐(即运销上一年度才中引盐)的任务。它只要求商人行旧引时,须购买同样多的现中仓钞(详见史料。)。即该方案是通过疏销积引的方式,以逐步减少商人的守支时间。
而袁世振方案,则是以行现中新引为主。当时两淮每年行盐总额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淮南52.9024万,淮北17.6156万)属正额引。这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基数,故袁世振以此作为每年的行销现中新引总额。所剩的19.482万(即淮南15.0976万,淮北4.3844万)才被用于行旧引。这便使疏销旧引的速度大为放慢。其次,他为在帐面上达到速销积引的目的,便将每引重量增加142斤(占原引重570斤的24.9%),以一分为二。这又等于是增加每年的行盐总重量,使疏销积引更为困难。
2对比盐商损失
虽在嘉隆时期,行正引必须守支,但按庞尚鹏疏理方案,其正额盐重仍为每引285斤,与疏理前相比,并未减少。另余盐虽由每引265斤,降为200斤,但庞尚鹏已将余盐课银作相应的调整。即疏理前每百斤余盐,纳课银0.264两;疏理后则为银0.263两,也未增加盐商的负担。故比较而言,疏理给商人造成的困难,主要是每运销100斤余盐,所须带销的正额盐重量,由原来的107.5斤,增加为142.5斤。
现相比而言,袁世振对价格、费用的核算,均是以行现引为主。商人所积旧引,首先将因该方案的实施,而再增加其守候成本。同时,内商以每引570斤卖盐给水商,收银3.2两,是“往时”的价格(即相当于每百斤盐价为银0.5614两,或水商每两银可买盐178斤)。当时正引价每引银0.65两,余盐课银每引0.7两,火盐价每引银0.375两,内商取价每引银3.2两,尚有利可图。但“近年”以来,正引价已为每引银0.85两,余盐课银每引1.45两,火盐则每引银1.5两。在此条件下,内商卖盐价早已为每引银6.0两(每引仍570斤,即相当于每百斤盐价为银1.0526两,或水商每两银可买盐95斤)。所谓盐商旧引,即其正引价和余盐课银,早已按“近年”高价予以支付。在此条件下,袁世振却将疏理后的内商卖盐价格,仍按“往时”标准,定为每引356斤,价银2.0两(即水商每两银仍可买盐178斤),故内商按此疏销旧引,必将大亏无疑。
四、袁世振第二疏理方案(即纲运法)
袁世振在其十篇《盐法议》中,并未提及有个纲运法(此即袁世振第二疏理方案),该法是在其第一疏理方案遭抵制后,才于《纲册凡例》中被提出。且据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的顺序,在十篇《盐法议》与《纲册凡例》之间,还夹有一篇袁世振的《奸囤擅利权揭》。这其中有一定原因,下面予以分析。
(一)第一疏理方案遭到抵制
“新旧兼行,二八抵验”的行盐格局,是因困守支所造成,并对边、内二商都不利。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是为调动边商积极性,但这样要严重损害原持引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的利益。最初他可能以为,只要该方案被推出,必有新的内商产生,这样便可置原持引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于不顾,但情况并非如此。该方案于万历四十五年年初下达扬州后,即遭到抵制。如袁世振于万历四十五年年底到达扬州时,曾写信向户部尚书李汝华报告情况,其中便提及,“部议正月到扬,上解开征,绝不遵部法佥商,仍用套搭”。,“倘职不来,部议竟画饼矣”。
(二)袁世振撰文抨击、恐吓两淮内商
袁世振的第一疏理方案不但遭到抵制,而且有人赴京替盐商说情。当情况传至朝廷后,可能引起袁世振的恼怒。故他曾写《奸囤擅利权揭》,以抨击并恐吓两淮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在该揭中,袁世振将按朝廷规定不得不收购仓钞的大盐商(即持引大户),污蔑为囤户、奸囤。他说:“顷部议行之,两淮内商、边商,皆不远数千里来,举手加额,或上疏,或具呈,惟恐部法不行,惟恐囤户挠阻,则部法岂厉两商者哉?而人从淮上来,即亦有谓部法不可行者,则有为之关说者也。”袁世振在这段文字中,虚拟了一个假的情况。即他认为,在原持引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之外,还有一个“两淮内商”群体的存在,而这个群体是支持其第一疏理方案的,其实并非如此。即当人们发现,袁世振第一疏理方案将严重损害原持引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的利益时,不可能有新的商人响应,故新的内商群体不可能形成。后来袁世振也承认,淮盐经营须依靠原持引内商(尤其是持引大户)。即“每纲去此辈数人(即指持引大户——本文注),余皆疲乏穷商耳”,故须“一概抚而用之”。
袁世振在《奸囤擅利权揭》中,还违背事实,称两淮大盐商每岁攘夺国课银一百数十万两,“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并煞有介事地算一笔帐:“盖国家每岁所取于两淮者,余盐不过六十万,正盐不过三十五万。而囤户每岁所取于两淮者,卖正引之价,淮南六十八万引,每引以八钱五分为率;淮北二十二万引,每引以一两三钱为率,岁卖九十万引,则巧赚国课银八十六万四千两矣。”。
现分析这笔帐,便能看出袁世振的强词夺理。如他称,大盐商每年“巧赚国课银八十六万四千两矣”(即68×0.85+22×1.3),这是按大盐商抛售其全部积引所算。但众所周知,大盐商是两淮内商的主体,他们所收仓钞,是主要供自己使用,只有部分卖给其他盐商。袁世振故意按大盐商抛售全部积引进行计算,并扣以攘夺国课的帽子,这显然不妥。
实际问题在于,按袁世振所供数据,大盐商最初收钞价,为每引银一钱七八分(姑以0.18两计),售钞价则为每引银0.85两,即其价格之差为每引银0.67两(指淮南部分)。但须强调,收钞是发生于十年之前,售钞则发生于十年之后。也即大盐商按每引银0.18两所购仓钞,须积压十年,然后才可按每引银0.85两售出。在此,袁世
振回避一关键的事实,即这十年的利息,恰是被朝廷所占去。
现不妨以本银0.18两为例,分别取年利率为15%和20%,以复利方式(即以某年年底本利银合计数,作为其下一年年初之本银数),计算其九年间的增值情况(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0.18两银经过九年(也即到第十年初),若按年利率15%增值,则为银0.6332两,而若按20%增值,则应为银0.9288两。这表明,上述引价从每引银0.18两,演变为每引银0.85两,完全是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不是“攘夺国课”。其实袁世振也明白,资本必须计算利息。如他称:“银征于八九年前,盐掣于八九年后,预征之谓也。夫至于八九年后,虽有利息,尽归赔累矣。”这其中的“利息”,是指行盐利润;“赔累”则是指资本于被占期间的利息。
(三)第二疏理方案的推出
袁世振因第一疏理方案遭抵制,便于万历四十五年九月再去扬州。而就在去的路上,他经与盐商(尤其是大盐商)接触后,推出其第二疏理方案,即纲运法。据袁世振称:“至九月二十二日入境受事,又以扬郡修葺旧署,封砌未完,不便防范,乃沿途料理盐务,渐次吊查诸卷,及有商人陆续远接,备悉咨询。至天长县住三日,极目蒿思,偶得一纲册之法。”上述文字中的“商人”,应是指抵制其第一方案的人(尤其是大盐商)。现在,这些人远途迎接袁世振,而袁世振则“备悉咨询”(即悉心听取这些人的意见),然后“极目蒿思”,才“偶得一纲册之法”。这便是袁世振抛弃第一疏理方案,并推出第二疏理方案的背景。
袁世振对其抛弃第一方案,出台第二方案,自身多有粉饰,且文字滑稽,现也不妨摘录几句:“自本道入境以来,虚心博访,人人而就问之,节节而细绎之,似犹觉万商情境,尚更有大苦者,哽咽于胸膈之间,而不能吐也。其以一旧引,超掣三新引之故乎。盖部议所以念商者至熟,惟信以超掣为人之所乐趋,只患其少,不知超掣实人之所乐趋,只苦其多耳。比如醇酒十瓮,而令二三人饮之,醉欲死矣;如令数十人饮之,既不苦于甚醉,而又可以畅怀,不亦快乎?”。上述文字中的“万商”,是指原持引内商;“大苦者”则是指持引大户。他们的痛苦是积引太多;其愿望则是尽快销去积引,以盘活资本,然后行新引。袁世振却令他们每行销11日引,须带销3新引。这无疑令他们苦不堪言,怎可能“乐趋”和“患其少”?至于将这种损害商人利益的行为比作请人喝酒,则更文不对题,这只能表明其为人的不实在。
(四)第二方案(即纲运法)与第一方案比较
袁世振曾对纲运法进行过虚伪包装。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见笔者以往拙稿。但与第一疏理方案相比,第二疏理方案还是对盐商作了适当让步。其表现是:
1按第一方案,淮南每年行旧引15.0976万引,第二方案则改为20万引。这便使疏销积引的速度比第一方案为快。
2第二方案统一定每引重455斤;正引价则为每引银0.55两,余盐课银每引0.8两,火盐每引银0.6两,内商卖盐价为每引银2.9两(即相当于每百斤盐价为银0.6374两,或水商每两银可买盐156.9斤)。在此条件下,内商疏销旧引时,因正引价和余盐课银是按疏理前高价支付,故仍难免亏损,但其程度要比第一方案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