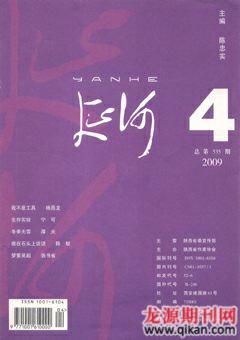粮食祖宗
刘 云
刘云 男,1963年生人,大学中文系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坚持业余创作,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曾在《延河》发表诗歌,出版个人诗集《劳动的歌者》,现为陕西宁陕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与我老家紧挨着的一个村,就是神仙湾了。神仙住着的湾子,多好。从水清水旺的冲河向巴山深处走去,在快要见到莽莽大山的时候,那河边就显出一个大大的湾子来,河从湾子中间划过,河两边一抹平展的镜面便是呈现着水田了,水田不多不少,一千亩。土改时,湾子是有五百号人的,那么人均就有了两亩的好水田。到了如今,人口正好一千,水田亦是有一亩的,在巴山,坡地多,水田少,人均有了一亩,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神仙湾没坡地。坡地是我老家那个村的,那时不叫村,叫大队。从神仙湾再往山上去,没了水田的地方,就有了坡地,坡地多是黄泥地,神仙湾人种着一片片稻子时,我老家的人们便委委屈屈地种着红苕,稻子扬着粉白的细小的花,在清朗的空间一阵阵地清香着,红苕的花呢,发着紫,藏在巴掌大小的苕叶里,引不得蜂蝶的戏访。稻子黄熟了,湾子里天地一色的金黄,而老家坡地的红苕,叶子一层层卷黑着,怎么看怎么不像丰收的样子,湾子里收谷子的打拌桶声,欢快着响彻着整个湾子,过路的干部会说,神仙湾今年又丰收了,就是不说我老家那个村丰收。
其实,我老家是年年丰收的。
爬上神仙湾那面大坡,到了一个狰狞的山岬口,往下一看,好似一口大锅了,那锅沿上,锅帮上,锅底里,就是我老家的村。老家少水田,坡地却肥沃得很,四山的老林子,遮住了北来的霜气,也把好水浸润得老家的庄稼旱涝保收。老家种包谷、洋芋,向着神仙湾的那面黄泥坡地,种红苕。包谷总是似牛角的,洋芋也繁殖得兴旺,就是那叫神仙湾人看不起的红苕罢,也是个赛个地炸开着大大小小的裂子,猛劲儿地胀鼓起肚子。某一年,毛主席在乡下看见了红苕长得可爱,一时高兴,说,红苕很好,我爱吃。便有了全国的大种红苕了。神仙湾的人不敢落后,就将水田起了旱,堆起红苕垄子,比赛着要红苕下蛋。可到底输给我老家那个村,他们不知红苕是喜欢坡地的,且要黄沙地,阳光足,在坡上向阳着晒才有得好收成的。那年,爱到神仙湾沾喜气的干部便没说丰收的事,湾子里的红苕没到苕叶子卷起,苕砣砣都烂在稀泥里了,是叫渍水沤死的。神仙湾人走麦城,只好把红苕藤子割回家去,分给家家户户喂猪。自然,我老家那村红苕又是丰收了,人吃猪也吃,吃不了的,或磨了红苕粉,变着花样做粉条子吃,或切了片子,晒干了堆着过冬。恰恰这年神仙湾就缺了粮,公社里协调着叫我老家的那村给山脚下的神仙湾人借红苕片子吃,来年还谷子。神仙湾人吃惯了水米哩,把个红苕片子吃得肚子结火,满心的委屈,还得感激山上的阶级兄弟救了急。到了来年还谷子,到底转不过劲,找个理由说欠产了,只还了一小半。公社说,算了,都是国家和集体嘛,都有吃的了,还不是左荷包倒到右荷包。我老家的人好说话,笑笑,就真的算了。到底公社觉着过意不去,给我老家的村争取了一批布票,说丰收了,叫大家扯几件衣裳穿,总算没积下什么仇怨。
算来,神仙湾的大出名,还不是丰收之类的事。它的出名是因了神仙湾的倔人,倔人叫马和尚,马和尚一听就是浑名,大名其实正经叫个马和勤。马和尚的出名由来已早。县里的志书上就记着一折子,说土改时国家给大家分了地,不久就办起互助组,马和尚谁的组也不参加,自己单干。到了初级社,马和尚不入社,依然单干,县里的文工团编过一个小戏,叫《单干不如社里好》,说单干的暗地里跟社里比着劲哩,这年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了,社里千里百担一亩苗,到了年底竟丰收了,社员们脸上乐开了花,再看单干的,却只收了二成,最后单干的死缠活缠着要入社,逢人就说还是社里好哇!那戏唱的就是马和尚。戏里说,是人就要合群哩,你不合群,难道不成了个和尚。自此马和勤叫成了马和尚,正经大名却没多少人知晓了。到了高级社,不入就不行了,这是政治上的大事,县委书记说,入,都要入,看谁黄牛黑卵子格外一条筋!便都入了。马和尚也入了。只是年年上告,说地是共产党分给的,牛是我自己拿五石谷子换下的半桩子,起五更睡半夜喂大的,犂呀,风车呀,拌桶呀,晒席呀,都是我请了木匠精工细活地打制的,付了工钱请了酒饭的,凭什么说收就收了?一直告到“四人帮”倒台,再到分田到户时,到底分回了自己早先那片田,只是牛和农具说不清白了,也作不成价,县上的干部说,老马,算你到底是赢了,一口气争了几十年,小经文就不讲了罢,这才罢休。
入了高级社,以后又是人民公社,马和尚不好好出工,经常挨拾掇,雨天队里不上工,动不动就把马和尚叫来,叫他说清白。起先马和尚不吭声,任你怎么斗,却只是眯了眼养神,临了,睁眼道,说够没,说够我回呀!日子久了,马和尚倒烦了,对干部说,你们好大的精神,我是没精神陪你们了!再叫,索性不到场,队上派几个民兵去动粗的,一见马和尚膀大腰圆,力气正没地方使,便都缩了头,到底一个村的人,谁跟谁也没仇怨,渐渐地事情就搁下了。
马和尚不好好上工的理由很简单,说集体干活,牛曳马不曳的,做庄稼就不是这么个做法。干部说,马和尚,你的理由站不住哩,你就是想单干么!马和尚梗了脖项顶了牛,说单干又不犯法!到了公社大集体出劳挣工分,马和尚家的工分总是不够分粮,公社又怕饿死人,年年的返销粮、救济粮倒是优先着安排给马家,渐渐地,背后嫌他的多了起来。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马和尚越喂他越上告,这不是鼓励人往坏里学嘛!
只是马和尚的几个儿女都大了起来。因了他们老子的脾性太坏,便都入不了团,进不了步,村上团支部一帮子也怪得很,说要入团也行,先把你父亲的落后思想改变过来,否则怎么能显示共青团员的先进作用呢。儿女们回家见着他们的老子,话还没理顺,一腔的胆气都从裤裆里跑脱了。老子黑风扫脸,躲还躲不急哩。日子长了,马和尚也听到些闲言碎语,有时半夜就叹气,跟自己女人说,儿女进步是好事,但儿女是儿女,我是我嘛,怎么能往一起扯呢!又说,叫我低头认错,除非他们把我杀了,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也晓得犂到田头自然弯的,但也不是这么弯的!弯也有弯的道理哩!女人说不出大道理,也直是叹气。年年农闲时,马和尚照样到县到省,就是要他的地,要他的牛,要他的犂,要他的拌桶,要他的晒席,要他的风车。
很快到了吃食堂了,开始敞开肚皮吃,大人小娃儿都说共产主义真好哇,渐渐地,粮食见着囤底了,粮食不够吃,没半年,壮劳力都下不得地了,人人都浮肿起来。马和尚也浮肿,常常坐在自家门口青石台阶上,有气无力地望着湾子里的水田坝子,有一声没一声地骂着谁的老子娘,村上干部都不搭理他,任他骂着,也没气力还口。马和尚说,自古神仙湾不饿饭,倒叫你们王八日的捣腾得烟散气断,地是老子娘啊,粮食是祖宗啊,不敬这两样,世道还有不瞎的!下乡的干部听着村上反映,想这还了得,这不反了吗!就要和马和尚理论,见着马和尚,气倒短了,看马和尚两眼的茧火虫光,又想自己也是肚皮贴上了后背梁,啥道理都讲不出来了!马和尚笑道,我晓得你要说啥,你先莫说,我说,你娃儿要是叫我吃上一顿饱饭,你操我娘老子都行,只是你娃儿也饿耙了,说不得硬气话了,你看你们都造了些啥子孽呵!这年秋末,马和尚直接就上省了,等到县上将他接回遣送回来,竟面颜好了许多,原来省里县里对他却照顾,每天两顿杠子馍,一碗白菜豆腐汤,吃得马和尚一肚子的反动劲儿翻不上嗓子眼儿,到底给劝慰着耙了气了。回来几天不出门,一入冬,马和尚找着队上干部,说,老是这样儿的,也不是一个事,一千口哇,弄不好就出了人命了!便相商出一件事,因了这事,马和尚上了我老家那村的山里,做出惊天的事来。
神仙湾是没坡地的,也没山林。山林都在我老家那村的四山里。马和尚叫队上干部跟我老家的队干部商量着,借下一片老林子,办起个神仙湾的药材场,专种黄连。答应每年卖下钱来,二八分成,或由神仙湾付给三千斤大米给我老家的社员过年。这事在那些年不新鲜,比如山下的大队,每年会跟高山队借了土地繁殖包谷种、洋芋种,解决山下队种子退化问题。只是种药材倒是头一回。好在两家队里都同意了,也没跟公社里报。马和尚一个人冬里就上了山了。
那药材场多少年后,我回老家时,听着马和尚的事,上去看过一回。只是场子已经毁没了,种过的地又叫蒿草长满了,隐约中林子边上碎刺灌丛子里,还有千脚落地窝棚的样子在那里显示着,可以想见马和尚当年生活的迹象。不知马和尚是怎么相上这个大场面的,那是一个高山深处的草甸子,一百多亩尽被蒿草覆盖的好地,四周是山林,象是原始的样子,从没人来动过。马和尚一个人背了米面、锅碗、砍刀、锄头,当然,还有火种,进了草甸子。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盖起了他的窝棚的,他的第一顿在深山里的饭食是怎么到嘴的,第一场我老家的大雪把上山的毛毛路盖得严实的那些日子,他是怎么守着他的窝棚里的火塘,听着山里的野物们的嚎叫的,他又是怎么砍开林下的杂树棵子,把那肥沃的林间的浮土翻松,整治好黄连棚子,在春天种上黄连的种子的,从此,马和尚一年都没下山,他的小子每月给他背一回米面油盐上山,爷儿俩是怎样相对而语的,这一切都没人能说清!只是这年秋季,黄连下山时候,神仙湾的壮劳力上山背运黄连时,才知道马和尚就是凭着自己一双手,种了一面山的黄连,在那片百多亩的草甸子里,开出了五十多亩地,全部种上了包谷!这一年,神仙湾的药材场黄连收了上万斤,包谷收了一万五千斤!
你如果当时站在药材场的草甸子里,看到包谷丰收的样子,心中肯定会象山风刮过一般,你不能平静,这已经不能用奇迹来形容,一个人,一个年年为了他的土地到县到省,希望要回他的权利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山里汉子,一个连正经名字都被大家忘掉了的人,甚至,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他了,反正,这片老林子,在他的脚下,在他的锄头下,种出来叫人泪花花的精贵的东西啊!反正,我知道这一年,全县超交公购粮,留下的人均口粮不足二百斤,我还知道,第二年春天还未过完,全县的土地大面积撂荒,近一半的人口出外逃荒,我知道县里的头头脑脑因超额完成公购粮受到专区、省上表彰,也因为人民的逃荒受到撤职处分。这些都是县志上记载的。
不说近万斤黄连卖了多少钱,只说一万斤包谷,在这个冬季给了神仙湾人多少温暖,尽管神仙湾的第一场新雪还未彻底落下时,这温暖的梦就破灭了。县里派来了工作组,神仙湾作为瞒报产量的典型,被报到了专区,分到户的包谷被限期收回集体,然后罚交了公粮,一些胆子大的,把马和尚种下的包谷藏在山里,当然马和尚家是颗粒不交的,那几天,他搬个大靠背椅坐在自家大门口,见干部来收粮,他就破口大骂,骂干部,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指桑骂槐地叫干部又气又笑,你气吧,他骂的是国民党,你笑吧,分明又是在骂社会主义。最终,神仙湾大队的干部连锅端掉,我老家那个大队的干部也背了处分。也是这年冬天,马和尚再次踏上了他的到县到省路,只是没有过去的运气好,没有杠子馍、白菜豆腐汤给他吃了,只有一天二两米汤喝着度命了,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关押。
在我的记忆里,正式知道马和尚这个人,是1978年的事了。那时,马和尚的小儿子马超志和我同班,刚刚上完小学五年级,正准备升入初中,但他是班里三个唯一没有升入初中的一个,因了现行反革命的老子,另两个是地主子女,在同学们的议论中,我知道了马和尚。从此我的这位马姓同学再也没有走出大山,尽管多年后,他成了成千上万走南闯北打工农民的一员。
正式见到马和尚,当然是在神仙湾的那水田茫茫、乡野静寂、鸡犬偶尔相闻、让人会忘掉今夕是何年的氛围中。我那时做着县文化馆的创作员,准备写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新变化的戏剧。我在村支书的指点下,见到了在我心中谜一样的马和尚。他老了。因为已进初夏,他身上仍然穿着厚厚的棉袄,双手拢在袖筒子里,他倚在他家土墙院子的门框上,接我进门。我说,马叔,你老精神蛮好嘛!他说,操心还好。我又说,我和马超志是同学哩!他哦了一声。此后我们的谈话很困难,对于我的问话,他总是摇头,偶尔叹一口气。马家的老婆婆在灶房里给我们张罗着做晚饭,也许是柴草太湿,灶房的浓烟一直涌到堂屋里,呛得我一阵阵咳嗽。马和尚突然就吼了起来,冲着灶房那头骂道:你是想撵客走吗!你做了一辈子饭,连火都不会烧了吗!我连忙陪笑说,没事没事,我也是农村呆过,习惯了!马和尚摇摇头,说,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顿饭,我们是喝了酒的。酒是我带来孝敬他老人家的。西凤,红包装的,在那时应该是县上领导才常喝的。马和尚的酒量并不大,大约不到二两,便坚决不喝了。我借着酒上脸单刀直入地问,马叔,是什么力量,让你几十年不停地上告,非得要回土改时分得的土地呢?直到这顿饭吃完,直到我很失望地起身向他告辞,他也没回答我。那时我非常理解他,一个农民,因了那个苦难重重的年代,在监牢里坐了十几年,尽管后来平反了,也按当时生产队的工分值补了钱,但十年足以把一个精气十足的人毁灭几个来回!当马和尚送我,走过很长一段田埂,我说你回去吧,就送到这里吧,他才犹豫了很久似的,向我说:“老叔说了,你莫笑话呵,我这人可能就是一根筋,现在说起来,也没了意思,往日里想要的,有了,有了又怎么样呢?我几十年,就是看不惯大集体胡糟弄地,地是娘老子,粮食是祖宗,啥时候这个理都不过时。只是,现在,谁还爱种个地呢,争了一辈子的气,还是叫自己给泄了!还说有意思吧?!”
神仙湾,这大片的水田坝子,和我一样都出不来气了。我知道,水田还是过去的好水田,可种它的人却越来越老了。我知道,汹涌的民工潮,涌进了城市,涌进了灰色或彩色的梦想,哪一天,那被城市象垃圾一般倾倒出城的,那被土地的深情的目光牵着,终于回来了的,有马和尚的,不,马和勤老人的儿女们吗?!再过去若干年,他们会在神仙湾的水田坝子前,对我说,地是娘老子,粮食是祖宗,你别辱没了它吗?!
责任编辑 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