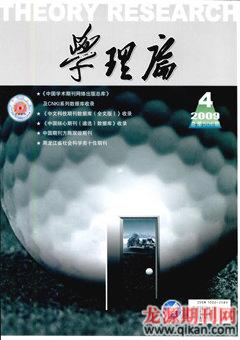传媒时代的民族问题
储 殷 李培广
摘要: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向民主治国的转型,传统社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面临着重新的诠释。在单质性民族国家逐渐消解的全球化过程中,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这种现代甚至是前现代的概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如何重构以及重构为何种意义的符号,往往取决于国家、社会以及传媒的共谋,民族问题的提出往往同时具有国家战略、消费需要以及塑造消费需要的三重背景。
关键词:民族;后现代;消费社会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4—59—02
一、作为想象的民族的消解与重构
民族一词源于拉丁语的nasci,意即“出生”,在政治上,民族是自视为同属于一个自然的政治共同体的人群。尽管从人种学、人类学上寻求本民族意义几乎是所有民族的共同诉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民族都是由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因素塑成的主观与客观的混合体。集体性的记忆总是无法离开想象而获得其连续性,集体成员也正是在想象中获得了对于抽象观念的经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此意义上将民族定义为人造之物,即想象的共同体[1]。
民族的实质在于一种心理——政治的建构,它不仅是民族共同行动的起因,也是这种共同行动的结果。民族意识正是在共同行动中得以塑造,民族意识也正是在民族问题的提出中获得如滚雪球一般的递增效应。任何民族问题都是一种集体性的行动,它要求一种超越于个人理性之上的价值诉求,非如此则无法摆脱奥尔森语中的由搭便车而带来的集体行动的困境[2] (p38-40)。民族运动的核心乃是让运动中的个人仅仅作为民族的一分子而行动。
其一、民族运动内部,现实的多元利益聚合取代了单一的民族利益诉求。当抽象的利益无法满足动员的需要时,对于民族利益的世俗诠释就成为争取受众的必需途径,民族问题只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而被这个符号遮蔽的实质确是参与者各自不同的动机。诸如新纳粹的欧洲当代极端主义派别不同于传统的种族主义者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藉由排外所表达的是对于缺乏就业等经济问题的愤怒。
其二、民族运动过程中,职业性的民族问题制造者取代了民族主义者。由于当代民族主义运动,从内核上而言缺失了民族国家时代早期的那种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不疑,因此它迫切地需要一种危机状态,唯有在危机状态中社会的分裂与对抗才可以强化通过我们对敌人这种识别模式。
对于藏独这个当代民族分裂势力而言,其在文化上是难以识别的,在历史上是难以理清的,在逻辑上是难以自证的。所谓的“本土文明、民族记忆”由于本身就属于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因此显得含糊且混乱,从而无法成为一个建构性的、自足的观念。“我们”的概念是空泛的,“他们”的概念是真实的,对于他者的反对由此成为实现自我的唯一方式。以敌我关系为本质内涵的施密特式的政治特性构成了当代民族分裂运动中徘徊不去的幽灵。民族分裂主义者将尽其可能去回避同一制度框架内的对话与互动,而力图去制造一种紧急状态。原因在于,一旦是对话而不是对抗,一旦“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模糊不清,“民族分裂运动”将失去自我的内在根据而不复存在。当代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是制造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因为唯有制造出“死结”,舌头才会让位于牙齿。
随着同质性民族国家的消解,多元话语共存的后现代来临,作为族群神话的民族主义已经被严重消解,当代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消费时代的符号,它成为了一种偶发的时尚,提供的是多余精力和激情的消费,以及普通人对于平凡生活的反抗,对于存在意义的追求。在大多数时刻,它只是作为一种暗喻存在于观念世界的深处,这种暗喻将社会过程中失败者的被剥夺感符号化为了某种受压迫的民族意识,从而将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重构为民族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民族问题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它既是对一系列难以言表的失败情绪的概括,也是对诸多现实利益诉求的遮蔽。
二、作为观念与信念的民族问题
当代民族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它蕴含着的内在冲突,而在于它对于外在世界的视觉冲击。从巴黎街头狂躁的藏独分子,到加沙地带挥舞枪支的巴勒斯坦极端派别,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民族问题在许多时候成为一场表演,它要求戏剧化的张力、冲突与不可解决的悲剧性结果。它意味着民族运动优先考虑的可能却是本民族之外的电视观众的视觉需要。传播技术的发展、消费时代的来临,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传媒节目把囚禁于平庸生活而渴望刺激的大众的需要集中在一起,并予以强化,从而使得大众在平面中获得多维度的体验。这种体验的核心是抗拒平凡,因此电视节目的重要功能就是发现并制造焦虑[3] (p23)。大众通过对于窗口中外在悲惨世界的体验,而获得“我们是安全的”这一内在的自我确认。国际新闻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焦虑与安全的奇妙混合物。CNN的24小时滚动模式创造出一种日常性的亲切与安全感,而打断这种日常模式的突发事件报道则提供一种新奇的视觉消费。突发新闻是让人上瘾的,世界越混乱它就越容易让人上瘾。在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人觉得老套的后冷战的当代,有什么比民族问题更容易触动人们对于当代多元文化冲突的敏感呢?
当藏独分子的暴力活动被西方媒体赋予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时,一场街头的骚乱就脱离了其具体的情境而上升为存在的政治,在媒体的视野中,骚乱的真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生产出的“民族问题”这一值得消费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细节被意向所遮蔽,相反细节本身直接决定着意向的强弱程度,因此细节越暴力,民族问题的存在就越清晰。和风细雨的理性讨论只能在新闻里得到蜻蜓点水的报道,唯有歇斯底里的敌意、恐吓与暴力才可能让观众和演员同时满意。人们在透过平面的窗口,消费着外界的混乱与狂暴。
当作品完成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存在了。藏独分子所蓄意图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思路。西方世界的惯常思路倾向于把体制外精英的集体行动视为某种民意的表达,却无意甚至刻意地忽略了,民意常常不是政治过程的起点,而是政治过程的产物。体制外的精英表演不仅通过“民族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传播中获得权力的增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念的生产,这些体制外的疏离者可以获得一种话语的权力,正如瑟尔指出“用一种语言说话就是从事于一种由规则制约的行为”[4],“民族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如同某种构成性规则的提出,构成性规则实际上就是创造游戏,游戏通过规则而被创造,被构成[5] (p153)。体制外精英正是通过构造这样一种民族问题的语境从而为争取其利益获得正当性,而谈判一旦在民族问题架构下进行,实际上等于确认了所谓“民族问题”的存在。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当代的民族问题通过媒体镜像而构成自我生活的一个部分,这种移情并非无原则的滥情,而是有意识的矫情,对于外部世界的西方式诠释往往浸透着直截了当的国家利益。同样的这些国家,可以长时间地对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保持冷漠,却对拉萨街头的一群暴徒深表关注。如乔姆斯基所言这种文化议题体现了双重性格,对于国际事务而言,它是足以引起谴责、制裁甚至干预的大事,而对于国内事务而言,它只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趣事,它的真实目的是让民众关注窗外的故事,而忽视身边利益攸关的大事[6] (p38-41)。虽然西方国家在国际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上表现出一贯的武断与粗暴,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却常常是混乱的,尤其对于民族问题的反应仍然充满了权宜之计的矫揉造作。不仅是媒体倾向于提供那些人们想看的事实与评论,甚至官僚机构、情报机构也倾向于编造,目的是迎合上级,将那些上级爱听的内容上报[6] (p271)。尽管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少数体制外的蛊惑者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获取权力,但是西方的成见决定了它仍然倾向于用民族问题模式来重构事实。“民族”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发源于西方世俗国家成型过程中的一种信念,且这种信念常常不过是一种成见。当代民族冲突中最为惨烈的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大屠杀,其实不过是比利时人根据牛群和土地而创造出来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7] (p92)。一切的成见都并非中立,它浸透着意识形态,它是对判断者自尊心的保护,是其投射在世界上的自身意识与价值观念[8] (p72)。
三、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和谐民族观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的民族问题自建国以来一直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兼容并蓄的东方式思维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不同民族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与对话。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大家庭提供了明确而具体的方向,这种以整体和谐为出发点的实践哲学,相对于以对抗为出发点的西方民族观念更有利于解决当代全球民族问题。其原因在于,和谐理念的话语结构表现为富有弹性的容纳性结构而非西方式的排斥性结构。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国家超越了西方传统语境中局限于单一民族的国家概念,中国并非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具有“天下”、“世界”的普遍意义。东方的世界大同的理念也超越了西方狭隘的种族、宗教的派系概念。中国社会一直具有一种开放的、普适的、世界主义的心态,它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也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整合与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伴随着对于长期以来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深刻反思,和谐社会的民族理念已经开始成为解决当代全球民族问题的重要思路。
参考文献:
[1][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38-40.
[3][英]罗杰-希尔夫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
[4]Searle,Speech Acts:An Ea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5][美]斯蒂文-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3.
[6][美]乔姆斯基,巴萨米安.宣传与公共意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1-41.
[7][英]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2.
[8][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72.
(责任编辑/王丽君)